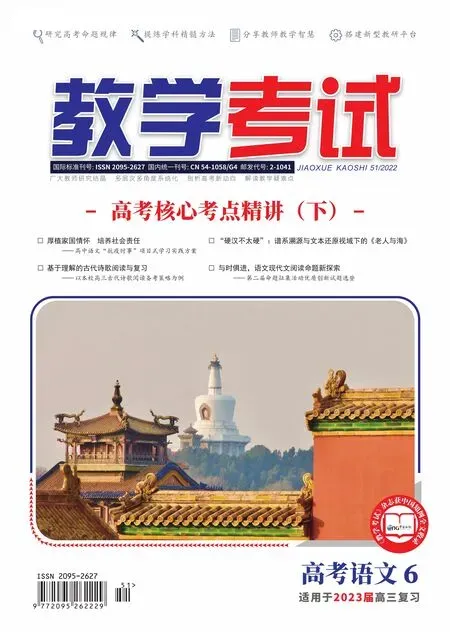“硬汉不太硬”:谱系溯源与文本还原视域下的《老人与海》
四川 梅振铎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以“外国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进行主题组元,旨在落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设置的“初步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的课程目标。单元学习任务群设计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基于“主题组元”,运用“文本细读”去领略、还原西方文化的渊薮。然而,如果这些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出现偏差,或者囿于成见,不仅会影响对西方文化精华的理解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对单元学习任务群的设计产生延宕。有鉴于此,笔者以《老人与海》作为阐释蓝本,尝试为单元学习任务群的设计提供一个透过“文化溯源”与“文本还原”去领略西方异质文化的窗口。
截至目前,国内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大多局限在“硬汉的抗争美学”“人的灵魂与英雄的尊严”“尚力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失败的强者与人生抉择”等方面,即便出现新的争论,也很少超出上述议题的范畴。这些解读的原点,往往离不开海明威在《午后之死》所提及的“冰山原则”。笔者认为,“冰山原则”作为海明威“极简主义”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固然是打开《老人与海》的一把密匙,但切入文本不同的“审美假定”,会使论者对“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以及“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解读。因此,笔者做一个大胆的“阐释假定”:《老人与海》或许隐藏着尚未被众多论者关注到的微观意旨——“硬汉”也许是被悬浮在“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不太硬”才是潜藏在“冰山”之下的“形象内核”,“硬汉不太硬”抑或是“冰山原则”背后隐喻的一种艺术辩证法。
一、“硬汉”的谱系溯源:“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
圣地亚哥的“硬汉”形象滥觞于“海明威式英雄”的塑造,是文本悬浮于“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老人“打不败的精神”潜藏着人在“自然绝对力量”面前的激越抗争,老人超拔的勇气和强力的意志是读者常常能触摸到的“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故而成为悲剧英雄最好的哲学注脚。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既定“审美事实”的层面,那么就难以触碰到老人这位终极生存者背后浓重的西方文化渊薮。卡洛斯·贝克指出,在文本的世界里,真正把海明威与“硬汉”嵌套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英雄的神话谱系”。弥漫在《老人与海》字里行间的神话原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推开重读圣地亚哥的另一扇窗。
圣地亚哥的“硬汉”原型,指向古希腊文化的神灵与天空。老人作为一个长期被艰难与不幸裹挟的老渔夫,因遭受衰老和命运的捉弄,连续八十四天连一条鱼也没捕到。所以在周遭世界里,他的能力成了问题,生存成了问题,职业成了问题,甚至连自我的价值和尊严也成了问题。当他历尽艰辛捕获大马林鱼后,这场冒险似乎配得上老人付出的尊严和代价。事实上,老人这场暂时胜利冒险的审美原型恰好见诸《荷马史诗》的《奥德修纪》。诗人荷马把奥德修斯海上十年的历险,以时空倒置的方式放在他到家前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来描述。奥德修斯凭借个体的终极生存意念,在茫茫大海中与未知的命运进行不间断的抗争:战胜圆目巨人、智斗塞壬女妖、闯关卡律布狄斯……在原型视角的烛照下,奥德修斯历经终极力量的重重考验和圣地亚哥克服自身极限捕获硕大无比的马林鱼,是一种叙事艺术上的“异质同构”——它们共同支撑起“人与命运”“人与自然”的抗争母题;无论是“奥德修斯式”的历险环境,还是“圣地亚哥式”的斗争方式,都把“个体超越现实的桎梏”上升到苦难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硬汉”原型的神话图腾,寄寓在圣地亚哥试图用小船把大马林鱼从苍茫的大海上拉回港的“受难历程”中。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鱼大战”:攻击老人的鲨鱼数量越来越多,抢夺大马林鱼的鲨鱼种类越来越凶残,攻击老人所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而老人打击鲨鱼的作战工具越来越少——他一次又一次被残酷的攻击打出命运的常轨,最终在自然的极限困境面前失去了自己捍卫尊严的战利品“大马林鱼”。实际上,这种证明“强大的阻挠”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冲突原型,源于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所推的无休止的滚石。西西弗斯因触犯了众神而被惩罚不断重复、永无休止地做同一件事:把巨石推上山顶,但每当巨石将要到山顶时就会脱落滚下。这种既荒诞无效又孤独无望的劳作,被哲学家加缪视为最严厉却最美妙的惩罚,因为西西弗斯在绝望中发现了新的意义——他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坚毅力量,像“战斗的舞蹈”一样优美。当西西弗斯不再因为荒谬而抱怨,他就成了“神话时代的圣地亚哥”。只不过圣地亚哥面对的“诸神”变成了大海与鲨鱼群,他同样无法避免无休止的搏斗,受到难以名状的非人折磨。因此,当圣地亚哥用努力抗争去捍卫自我尊严时,他就比“西西弗斯”更强大,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中寻找存在的价值。
“硬汉”原型的谱系溯源,更脱离不了基督教的自然宗教图景。在西班牙语的言语系统中,“圣地亚哥”指涉“救主”和“受难者”。一方面,基督教所宣扬的耶稣受难环境跟老人所处的苦难环境高度吻合,老人苦行僧般的生命历程几乎再现了耶稣受难的痛苦经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圣地亚哥本人并不信仰宗教,但是当他的肉身被苦难压得异常沉重且超越自身极限的时候,他却以圣徒彼得的名义,用虔诚的宗教仪式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获得坚持下去的力量。另一方面,圣地亚哥在捕获大马林鱼时,充满了溢美之词,甚至特意指出它的眼睛“像宗教队伍中圣徒塑像的眼睛”。有鉴于此,老人出海打渔俨然成为一场“朝圣”的精神之旅:鲨鱼的攻击就成了“受难者”的必须,老人的煎熬就好比向“拯救者”的赎罪。因此,海明威对圣地亚哥形象的建构鲜明地体现了两面性——“受难者圣地亚哥”是对“拯救者耶稣”的一种精神皈依,“硬汉圣地亚哥”是对“受难者耶稣”的价值投影。实际上,老人的宗教原型已经囊括一种源于崇高的悲剧美,即有上帝形象的圣地亚哥能够承受并超越一切现世痛苦里的孤独、失败甚至死亡,且永远也不会衰败。
基于上述对《老人与海》“硬汉”形象的文化谱系溯源,不难看出老人“硬汉神话原型”潜藏的“本相”:宗教式“孤勇者”的苦难生存哲学。这种哲学氤氲的西方文化内核,正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所言,指向“老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凸显“人作为有神性的存在,拥有超越苦难的永恒精神”。
二、“不太硬”的文本还原:“冰山”之下的形象内核
宗教式“孤勇者圣地亚哥”身上所寄寓的苦难生存哲学,固然可以解释“硬汉”显露于西方文化“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但是在固有阐释的视域之内,苦难生存哲学的另一面往往容易被忽略,即老人作为弱小的个体在无限重复的苦难面前同样“畏葸不前”:怀揣极端怀疑的本能恐惧,不愿直面绝对困境的退缩,不断陷入否定自我的消极,无法掌握命运的深层焦虑……这些人性的本能,显然不是“硬汉”的“硬”可以完全解释的。
圣地亚哥的“不太硬”,始见于他作为“孑立的个体”在绝对困境面前的犹豫退缩。人本能的心理体验、精神境况最能反映内在自我在现实面前的纯粹状态。面对大马林鱼被凶残贪婪的鲨鱼不断蚕食的窘况,圣地亚哥一度陷入“梦的呓语”中:
真是好景不长啊,他想。他盯着那条紧逼而来的鲨鱼,顺便朝那条大鱼望了一眼。这简直像是做梦一样,他想。
好景不长啊,他想。我现在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希望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而是独个儿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它们准把这鱼咬掉了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上好的肉,”他大声说,“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希望我压根儿没有钓它上来。”
圣地亚哥的意识流不断陷进“一场梦”的反复迷惘中。此时,他的自我独白透露出其隐秘的心理位格:不愿直面外在的残酷,借助梦来有意回避现实。因为“梦”作为潜意识最直接的表征,它暗示着老人跟“普通人的性情”并无二致——在绝对强力的压迫下,他本能地退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实之外。此时的老人尝试“自己跟自己”对话,通过反复激励自我,试图把自己从怯懦中拉回来,以缓解他对战利品不断丧失、外在世界难以把握的深深焦虑。这就表明,老人作为终极生存者的“硬”,并不是一种“天性的必然”,反而更像一种“挺住的选择”。他并没有特别的办法完全超越主体的自我弱点,也没有办法在外在环境的极限进逼下完全坦然面对艰难和不幸。
圣地亚哥的“不太硬”,彰显于他释放内心深处孤独压抑时“摇摆式的自我否定”。老人在捕获到大马林鱼时,内心充满了把自己作为万物尺度的激情。但当鲨鱼群一直纠缠自己、折磨自己时,他开始将自己放在“怀疑的天平上”,他的自我由“最初的坚定”滑向“反复的摇摆”:
“别想啦,老家伙,”他大声说,“顺着这条航线走吧,事到临头再对付吧。”不过还是得琢磨琢磨,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儿可干了。这个,还有棒球。……不抱希望才愚蠢呢,他想。还有,我把这当成了一桩罪过。别去想什么罪过了,他想。眼下不说罪过,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对这个一无所知。……“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他大声说。
当老人开始重新追问这次出海捕鱼的必要性之后,他就不断陷于“想太多”和“别想啦”的自我矛盾中。老人的内心不再坚实,虽然他不断安慰自己要担当,但担当的合理性却被隐隐的罪过心理冲刷,因而在保卫大马林鱼和痛击鲨鱼群两个极端中不断摇摆。老人变成了自己的“怀疑论者”:反复质问自我、否定自我、重估自我,心中坚定的价值尺度开始动摇。可见,“失望者”和“希望者”这种“二律背反”的角色已经深入到老人的意识深处。这个“不太硬”的老人,恰恰才是“海明威式的英雄审美”隐秘却动人的地方。这样的圣地亚哥才是一个活泼泼的人,才是一个“既见得天地、又见得众生”的人。因此,老人身上的坚韧超拔,更多的是他在不间断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找回自我的结果。
圣地亚哥的“不太硬”,还集释于他放下优雅风度对鱼“躬亲自省”的“应激独白”里。老人在捕获到大马林鱼时,毫不掩饰自己对它的爱,甚至把它上升到力量美学和意志美学的高度;当大马林鱼被鲨鱼咬住时,他将其看成“自己受到袭击一般”,甚至希望自己没有钓到它。可见大马林鱼不仅让老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成就感,还直接维护了他作为渔夫的尊严,甚至在大马林鱼遭受群鲨的围攻时,他脱口而出:
“鱼啊,我本来就不该出海到这么远的地方,”他说,“对你对我都不好。鱼啊,真抱歉。”
“你原来是一整条。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我把咱们俩都毁了。”
这些“应激独白”反映出圣地亚哥既有无法掌控大马林鱼前途与命运的矛盾与懊悔,也有对自己出海太远的反省与批判——或许由于自己无节制与非理性的索取,遭到了来自于大海群鲨、自然严厉的报复。凭借大马林鱼,他本可缓解经济和生存的压力,但现在一切都可能归零。他与大马林鱼必须同时面对被追击、被包围的困窘,自觉联结成“命运共同体”,以至他开始忏悔自己为什么要捕杀大马林鱼。可见,老人不但“不硬”,甚至还觉得杀大马林鱼和鲨鱼都是自己的罪过:
我根本就不懂什么罪过,也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相信。也许杀了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是的,尽管是为了养活自己,让好多人有鱼吃。不过这样说来,干什么都是一样罪过。别再想什么罪过了。
在圣地亚哥的潜意识里,杀戮本身有罪。只要被摧毁的都是崇高、有活力的生命,那么这种耻感就伴生于老人的世界观里。这种对位的思考,修改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优先尺度,甚至消弭了罪恶有形的边界:鱼和人各为生存,在自然的法则面前不得不走向对立、甚至成为生存的敌人。老人对作为敌人的“鱼”,非但没有半点“硬气”,更为重要的是他承认了自己的有限——必须通过消灭敌对客体(鱼)的肉身才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面对这一情状,他的内心写满了无可奈何,那份与“鱼”惺惺相惜的“柔情”在无意识间肆意喷涌。
不难看出,圣地亚哥这个“硬汉”“不太硬”。只是老人在与自然世界的对抗中,悟出“挺住意味着一切”,从而完成了自我救赎,成为自己的英雄。
三、“硬汉不太硬”:“冰山”背后隐喻的艺术辩证法
经过谱系溯源以及文本还原,圣地亚哥也许是海明威艺术世界里最富隐喻性的艺术形象。“冰山”之上的老人,是祛除西方文化荫蔽的宗教式“孤勇者”;“冰山”之下的老人,是兼具人性本能弱点的“普通人”。或许,这个“硬汉不太硬”是海明威创作中最为隐秘却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辩证关系,为打开《老人与海》新的“审美之维”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硬汉”作为“孤勇式英雄”的审美形象,揭示了海明威艺术世界里“崇高美”的深刻性。圣地亚哥虽遭受失败,但绝不屈从于命运,甚至淡然面对自己的一无所获,对于失败没有一丝一毫的感伤。他用生命、灵魂、信仰的力量重新点燃了自己,成为自己的英雄,铸就了一种决不妥协的“坚韧之美”。恰恰是这种“不幸”而“错位的美”,最终成就了显露在海明威艺术“冰山”之上的崇高与庄严。当然,这种源于古希腊伟大而静穆的美学传统,一直是西方艺术审美的主旋律:《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不屈从于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毅然决然去拯救玛丝洛娃堕落的灵魂而获得自我良知的救赎,最终使两人的灵魂“复活”;《百年孤独》里因为丽贝卡的到来,失眠症、失忆症袭击了马孔多全镇的居民,但奥雷里亚诺不屈从于现实的枷锁,最后闯出对抗失忆的生存之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小小年纪就在谋生之路上不断被歧视、被虐待,但他也没有被不幸裹挟和打倒,最终因抗争而获得成长……而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只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海”的“渔船”之上,向崇高的美学传统致敬。
“不太硬”作为“普通人突围”的审美脚注,隐含着海明威艺术国度里“柔性美”的通兑性。圣地亚哥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内心也有恐惧、沮丧、担忧和后悔;他深陷自我否定的泥淖,需要反复提醒自己摒弃消极、充满希望;他充满矛盾、时而谦卑,承认自己作为人的有限,却仍敬畏自然其他生命的伟力。海明威并没有刻意拔高老人的生命,只是把鲜活的生活根基与生命色调融入到老人充满写实主义的“独白系列”中,从而开拓出老人熔铸普通人“柔性美”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的本真源于“真实”,然而只有“真实”符合普遍人性的规律和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时,艺术形象才具有“典型性”,才能引发相应的审美共通感。中西艺术之维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水浒传》里打虎的武松,并非天生就是英雄,他喝醉后独自上山过景阳冈,是为了不被店家嘲笑,打虎近乎一种保存自己的本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同样不是主动的秩序反抗者,他得道成仙后一直处于受欺骗、受歧视的状态,大闹天宫只是他对现存秩序表达不满的反应;《红楼梦》里“宝玉挨打”,贾政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所谓的“封建家长做派”,既要看到他因宝玉勾搭忠顺亲王的戏子琪官,间接导致丫鬟金钏投井的怒火攻心,更要看到他面对大厦将倾的家族却独力难支的绝望与痛苦,这或许才是人之常情……类比圣地亚哥身上隐隐存在的“柔性美”,从侧面揭开了“硬汉守望者”海明威的另一副艺术面貌。
“硬汉不太硬”,是《老人与海》这座艺术“冰山”背后艺术辩证法的统一。小说所呈现的“冰山风格”,既有“硬汉”圣地亚哥的生命历险与体验,也有“常人”圣地亚哥的本能书写与重构。正如孙绍振先生对“海明威式艺术”总结的那样,浮在表面的是人物平静的动作和对话,而深邃的精神沉淀在叙述以下。
——运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