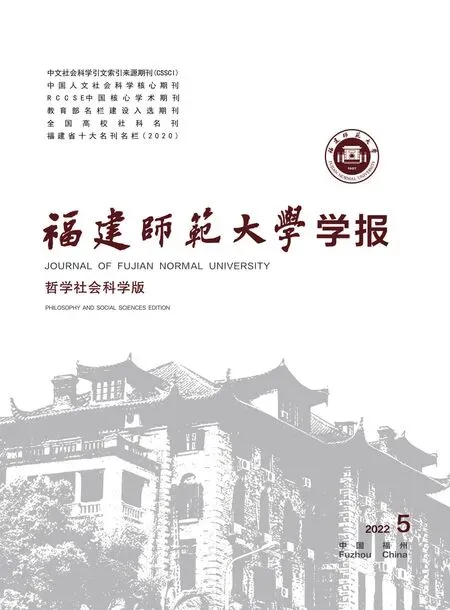物质性与实践性:基于界面分析的手机主屏幕管理研究
张 磊,孙 晗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智能手机主屏幕界面。当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智能手机来到用户手中,会迅速变为“私人订制”的产物。几乎每个人都会下载自己所需的应用程序并对之进行独特的分组排列,并随着使用日期的增加而以不同的频率更改主屏幕。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且持续发生,却较少出现在媒介研究的主要学术图景之中。究其原因,多半是媒介研究更关注内容、符号再现和效果,而忽略了媒介的物质性以及媒介实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立足于物质性和实践性的交汇点,手机主屏幕界面(interface)正是这种新技术逻辑的鲜明展现。手机主屏幕的物质性构成该如何理解?它蕴含着什么样的技术逻辑?在技术设计形成的基础上,用户对手机主屏幕管理的媒介实践,隐含着哪些值得探寻的深意?
一、文献综述
(一)手机主屏幕的应用型研究
手机主屏幕及其管理活动的研究主要处于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这一学术主题之下。研究者既有学界人士,也有来自业界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研究的核心是用户界面设计(user interface design),计算机工程专家对此尤其关注,这使得相关研究的应用性显得格外突出。研究分成设计和使用两端。一端关注手机主屏幕的工业设计,包括手机主屏幕的主题页面、应用程序图标、交互手势等具体设计。(1)Chun-Ching Chen,“User Recognition and Preference of App Icon Stylization Design on the Smartpho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5,pp.9-15; Norrie Lauren,Roderick Murray-Smith,“Investigating UI Displacements in an Adaptive Mobile Homescre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Vol.8,No.3,2016,pp.1-17.另一端则注重对用户手机主屏幕的使用体验进行观察和理解,从而反馈于手机主屏幕设计。后者更关注用户使用行为的表象,包括用户操作手机主屏幕时的视觉体验和情感体验、用户与手机主屏幕页面相关的认知模式和空间记忆等,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使用模式和使用规律(2)Chad C.Tossell,et al,“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martphone Personalisation:Measurement and User Variability,”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31,Iss.10,2012,pp.995-1010; Siu-Tsen Shen,“People and Their Smartphones-mapping Mobile Interaction in the Modern Connected World,” Engineering Computations,Vol.33,Iss.6,2016,pp.1642-1658; Anna K.Trapp,Carolin Wienrich,“App Icon Similarity and Its Impact on Visual Search Efficiency on Mobile Touch Devices,” Cognitive Research: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Vol.3,No.1,2018,pp.1-21.,呈现出理解手机主屏幕管理的多样视角。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理论色彩较弱,但提供了关于手机主屏幕管理的两个基础性认识。
第一,用户的手机主屏幕管理活动有两项具体操作值得关注,即“选择壁纸”和“排列整理图标”。研究发现,大多数手机用户将人物肖像设置为壁纸,且相较之下青少年和女性用户群体更偏爱肖像。用户还会担心页面视觉不协调(visual incongruity)而采取措施来避免肖像的人脸被遮挡(例如移动图标或小组件)。(3)Young-Hoon OH,Da-Young JU,“Look at My Face:A New Home Screen User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sign,User Experience,and Usability,2017,pp.146-163.德国学者马提亚斯·布莫尔(Matthias Böhmer)与杰诺特·鲍尔(Gernot Bauer)研究了用户在城市不同地理位置和生活情境中变换手机应用程序图标位置的行为,(4)Matthias Böhmer,Gernot Bauer,“Exploiting the Icon Arrangement on Mobile Devices as Information Source for Context-awareness,”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Mobile Devices and Services, 2010,pp.7-10.通过分析用户排列图标的原则及厂商手机相关设计背后的隐含深意,提炼出用户管理应用程序图标的五项原则:使用频率原则(usage-based)、接近性原则(relatedness-based)、可用性原则(usability-based)、美观原则(aesthetic-based)和外部原则(external concepts),并指出这些原则并不完全互斥,用户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二至三个原则。(5)Matthias Böhmer,Antonio Krüger,“A Study on Icon Arrangement by Smartphone User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3,pp.2137-2146.
第二,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设计发展飞快,手机主屏幕的样貌日新月异,用户的实践活动也更加千变万化。此类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容易忽略用户实践的丰富性。设计者为手机注入技术基因,而用户在多种目的、不同情境的操作实践中对手机主屏幕进行创造性的媒介组合实践,让手机主屏幕的管理延伸出了更复杂和更丰富的可能,这亟待我们深入探寻。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和可视化分析,主要是对用户同质化行为的归纳总结,试图从大量数据中抽象出所谓的用户使用模型和规律。在研究目的上,现有研究偏重应用色彩,力图为手机厂商的主屏幕和应用程序设计提供服务。笔者则试图探讨用户对手机主屏幕的创造性管理,旨在发现“规范行为”以外的意外性,进一步逃离“界面设计”和“用户反馈”之间的机械论循环。这就要求对“界面”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度理解。
(二)作为界面的手机主屏幕与“技术剧本”
界面被视为处于人机之间的一种“滤膜”(membrance),它既区隔又联系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6)Mark Poster,The Second Media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20.它将庞杂晦暗的技术系统遮蔽了起来,将复杂的数据运算和流转以图标等符号方式进行可视化。界面是人操作技术系统的入口,是机器功能“视觉化”的产物,其背后是一个“技术功能”的世界,而不仅是一个“意义”的世界。(7)祁林:《界面革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181-198页。这形成了一个互动过程,“界面将机器的数据、数据流和数据结构展现给人类感官系统,同时为人们的输入与互动建立框架,并把用户的指令翻译并返还给机器”。(8)Søren Pold,“Interface Realisms:The Interface as Aesthetic Form,” Postmodern Culture,Vol.15,No.2,2005,p.4.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则将界面理解为形塑用户和机器之间交流的软件,认为界面就像译者一样,介于两者之间,使得双方互相理解。(9)Steven Johnson,Interface Culture: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San Francisco:Harper San Francisco,1997,p.14.换言之,界面操纵的关系是语义学层面的,它体现为意义和表达,而非物质性的力量。当然,界面通常以液晶显示屏为物质载体,以键盘或触摸式屏幕为操作平台。(10)祁林:《界面革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181-198页。界面的物质性基础不应被忽视。
这种界面的物质基础在不断转换。从显示屏到触摸屏,从CRD到LCD、LED、OLED,从球面到平面甚至折叠,从单点触控到多点触控,如前所说,有关手机主屏幕的基础性认识之一就是其快速的变化迭代。手机主屏幕基础形态的改变即是生产者对手机主屏幕“技术剧本”的改写,它是技术愿景在社会语境中的叙事性陈述。界面设计者通过技术剧本为用户设计好了一系列标准行为和使用情境,并将技术知识嵌入其中,从而引导用户实践,规定了受众应当如何去使用和体会特定的技术物品。(11)梁君健、陈凯宁:《自我的技术:理想用户的技术剧本与手机厂商的技术意识形态》,《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3期,第75-91页。然而技术剧本的设定并不能完全框定用户的使用行为。用户对手机主屏幕进行能动性再造,使它更适用于自身,随后再上演日常性的手机使用。人与手机主屏幕,或者说人与界面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催生出丰富多彩的媒介实践。这种关系以及媒介实践也引发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12)徐亚萍:《运动图像的操作化: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第55-75页;黄华:《身体和远程存在: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9期,第46-51页;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23-132页。
“人-界面-机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如果还陷在界面工程学和人机交互设计的窠臼之中,只强调界面的功能性价值,关注设计的效率成果以及用户体验的满意度,是远远不够的。人不能仅仅被称之为“用户”,所扮演的也不仅是机械反馈循环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刺激因素。人不可以被化简为统一行动者的用户或消费者,界面也不仅是视觉所见的二维的、光滑的平面实物,也不仅是如技术黑箱一般不可见的程序语言和指令系统,甚至不仅是虚拟和现实时空之间的边界。我们应拓宽自身的想象视野来理解界面,走向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化意涵的界面思考。界面克服了媒介研究中硬件/软件、物理/虚拟、物质/语言这些二元论(dualism)概念,它介于这些概念之上,又将它们相融。
(三)作为复合空间的手机主屏幕
杰弗瑞·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指出:“计算机不愿被纳入习惯性的概念框架。”(13)Geoffrey Winthrop-Young,“Hardware/Software/Wetware,”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186.智能手机作为计算机的变形,也是如此。通常,媒介研究者不仅关注智能手机作为一个整体性媒介终端在社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关注编码和各种应用程序的内容与效用。简言之,前者关注硬件(hardware),后者关注软件(software),而围绕智能手机的具身性行为常常被忽略。温斯洛普-扬使用硬件、软件和湿件(wetware)这个三重合一的术语组合来理解计算机。当中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术语“湿件”,指的是与硬件、软件互动,并与计算相关的人的因素。(14)Geoffrey Winthrop-Young,“Hardware/Software/Wetware,”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186-198.通过将数字技术的硬件和软件相连接,人类被化约为技术体系中的环节之一;反过来,通过人的介入,又使数字技术得以实现并在复杂的情境中活化。人“盘活”了硬件与软件。因为个人特性和具身化操作各有不同,数字技术的外在表象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画面。
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我们将手机主屏幕视作一种复合空间(hybird space)。阿德里亚娜·德·苏扎·席尔瓦(Adriana de Souza e Silva)指出,计算机形成的是一种静止界面(static interface),然而手机形成的是一种移动界面(mobile interface),它具有移动性和便携性,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模糊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边界,整合创造了新的复合空间。人在使用手机时并不会将之划分成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也不会有“进入”虚拟空间的感觉,这与坐在固定屏幕前操作计算机是不一样的。(15)Adriana de Souza e Silva,“From Cyber to Hybrid: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Vol.9,No.3,2006,pp.261-278.因此,手机的屏幕看上去是一个二维平面,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同延性(coextension)的复合空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推进德·苏扎·席尔瓦的论断。首先,手机主屏幕的玻璃平面下具有纵深性,敞开了一个虚拟空间,用户就像对待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那样进行放置、排列、组合与美化。其次,这一空间是数字化和技术化的。它建立在硬件的物质实体基础之上,实现着控制硬件功能的软件指令,为使用者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与人之间进行着具身互动,这使它与真实空间区别开来。再次,手机主屏幕的空间居于人的指掌之间,它的便携性和移动性使它成为一个随身的空间。最后,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说,手机主屏幕的管理使用融合在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情境范围内。总之,在手机主屏幕的二维表面之下,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
笔者从智能手机用户对主屏幕进行管理的微观实践入手,把主屏幕这一界面视为复合空间,把它的设计理解为“技术剧本”,从而探寻这一媒介实践中更为多变的界面空间、更丰富的人机互动、更深切的具身感知,进而探索人与技术之间在现象学存在论上的互动关系。笔者试图回答两组问题。第一,用户面对着什么样的手机主屏幕“技术剧本”?第二,用户需要理解并且参与到这一“技术剧本”当中来上演自己的日常生活,对复合空间进行操作,这一媒介实践是如何发生的?当用户在管理和重新设置手机主屏幕时,又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化身份、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纳入其中的?
二、研究方法
手机主屏幕管理既涉及界面的物质性,又涉及用户的实践性,这两个属性交织在复合空间之中。笔者主要采用物本分析(objectual analysis)和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两种方法进行探究。
从物质性层面来说,作为界面的手机屏幕几乎没有现成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它需要一种综合式的研究设计。智能手机因iOS、安卓和鸿蒙等操作系统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理念、技术基础和外在框架,其中蕴含着“技术剧本”,并借助于屏幕的材质及技术而实现,包括玻璃、塑料、金属涂层、触摸点、控制器、线缆、基座,有液晶显示屏(LCD)、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等不同显示屏类型,也有电容式、电阻式等不同触摸技术。为了理解这种复杂的界面物质性,笔者搜集了当前市场上主流智能手机所使用的屏幕的设计原理和物理构成资料,苹果、安卓和鸿蒙系统的官方技术剧本(包括手机厂商官网的广告介绍和系统更新日志),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物本分析来理解手机主屏幕设计及与之相关的媒介实践活动。
所谓的物本分析法,强调从外观/相和功能/灵这两个方面入手(16)张磊:《拟人、非人与后人类:论人工智能媒介物与人类的相遇》,《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0年第6期,第6页。,对媒介物开展一种基于物性的分析。物本分析法源自海德格尔对“物”的现象学解剖,受到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的影响,又与之相异。物质话语分析力图发现“物质的话语效果与话语的物质效果间的相互建构”(17)Cynthia Hardy,Robyn Thomas,“Discourse in a Material World,”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52,No.5,2015,p.682.转引自袁艳:《“慢”从何来?——数字时代的手帐及其再中介化》,《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第24页。,其指向的更多是对技术符号的分析,而非物质依存状况。实际上,媒介的物质性恰恰不是以符号方式来展现的。手机主屏幕上不仅有“能指/所指”这一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基础的物质性空间排列组合。物本分析法更注重物质构成带来的基础性影响,采用文本细读式的眼光加以审视,力图为理解作为界面的手机主屏幕奠定基础认识。
用户使用的实践性和屏幕的物质性一样复杂。本项研究在数字民族志的思路下,开展参与式的观察和深度访谈。笔者对线上社区豆瓣、微博、知乎及小红书用户所分享的手机主屏幕管理相关内容进行了搜集和观察,其中重点关注豆瓣小组“我的桌面”(18)豆瓣网“我的桌面”小组,2020年10月30日,https:∥www.douban.com/group/ymm0001/,2022年8月29日。。该小组现有成员11万多,小组成员分享自己的手机主屏幕及相关管理经验。笔者重点对22位手机用户进行了线下或线上深度访谈,访谈问题围绕他们的主屏幕日常管理行为展开,当中还结合他们在线上社区所分享的手机主屏幕管理内容设置了具体的针对性问题,同时还收集了来自这22位手机用户的100余份手机主屏幕截屏和录屏文件展开分析(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列表
本·莱特(Ben Light)等人在提出手机应用程序的“漫游法”(Walkthrough,一译走查法)时说:“分析一个应用程序需要关注其嵌入的社会文化表征,就像其技术特征或数据输出一样,后者也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19)Ben Light,Jean Burgess,Stefanie Duguay,“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3,2018,p.885.对手机主屏幕的研究也一样。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也要考虑技术工具的物质性。两者结合,能够为具体的研究带来充分的思考。
三、研究发现
(一)理解屏幕:手机主屏幕的物质特性
屏幕不仅是一组光学设备(optical devices),还是一组具备物质实体形态的界面,是一个用户根据技术剧本而上演数字日常实践的舞台。屏幕具备实时交互功能,硬件设计奠定了软件运行的基础,也触发了人机互动的丰富状况。
屏幕位居媒介的发展历史之中。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提出了一种屏幕谱系学,将屏幕划分为经典屏幕、动态屏幕和实时屏幕三类。(20)Lev 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1.经典屏幕(classical screen)以绘画为代表,是一个矩形的平面,供人们从正面观看。它存在于人类身体所处的日常空间之中,也是进入再现空间的窗口。动态屏幕(dynamic screen)以电影银幕为代表,显示历时性的图像。实时屏幕(screen of real time)以计算机屏幕为代表,它显示的图像可以持续地进行实时更新。屏幕的特性是叠加的,而手机屏幕不仅同时具备了这三类屏幕的功能特性,还增加了互动的性质。当然,它的物质形态也与其他三类屏幕迥异。智能手机时代,手机屏幕在物质形态上具有三个特性。
第一,手机屏幕是一个长大于宽的竖屏,占据手机的主体部分。1983年最早出现的便携式电话是直立式的,只有能显示一行数字的LED屏幕。随着手机更新换代,屏幕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面积,可以说,手机形态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手机屏幕比例不断扩大的过程。早期手机的屏幕比例多为4∶3或3∶2,以水平向的“横屏”为主。它们多半只承担显示功能,无法进行触摸互动。从横屏变为竖屏的关键节点是苹果公司iPhone的推出。(21)事实上,世界上第一款配备电容式触摸屏的手机并非iPhone,而是LG公司的KE850。它于2006年12月12日首次发布,不到一个月后,苹果推出了iPhone且获得了巨大成功。伴随物理键盘的消失,电容式触摸屏开始兴起。iPhone否决了占用屏幕空间的物理键盘,主张“用软件来替代硬件”,开始采用灵活而适应性强的触摸屏键盘。自此之后,这种设计逻辑贯穿了智能手机的发展史。许多物理硬件被剔除在手机的技术剧本之外。手机的Home键、耳机插孔、储存卡槽慢慢消失,摄像头也开始隐形,厂商们陆续推出升降摄像头和屏下摄像头。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不断普及,未来或许连手机充电接口也会消失。一切都将隐匿在屏幕之下。
第二,手机屏幕是以玻璃为基础材质的。现代电影理论有三个基础性隐喻,即画框、窗户和镜子。(22)Vivian Sobchack,The Address of the Eye:A Phenomenology of Film Experi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并非巧合的是,它们都免不了要使用具有光学透明性却具有能实现物质区隔的玻璃。手机屏幕也同样使用了玻璃材质。手机屏幕颇似画框,这为用户镶嵌进肖像或其他图片奠定了基础;但与画框不同的是,手机屏幕里内嵌了一个具有同延性的三维世界。从这个角度讲,它又像是面向无限新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手机屏幕还成为映射自我的一面镜子。它显现了用户的自身需求,是个体私人化的复合空间,能够隔绝屏外、自我沉浸的庇护所(shelter)。但是,手机屏幕并不完全符合玻璃的透明本性。透过玻璃,我们本应能看到屏下的手机构造,如传感器模块的触控点、电路板元件、芯片和电池等。然而,以玻璃为材质的手机屏幕遮掩了技术世界。手机在发展过程中,化硬件为软件,去掉了外在接口等硬件设计,变得越来越纤薄。用户原先可自行更换电池和储存卡,现在变成用户无法自行拆解的一体机,成为一个封闭且隐秘的小型扁平黑箱。“技术黑箱”的概念被手机具象化了。
第三,手机屏幕提供了与人体交互的界面。随着屏幕触摸传感器从电阻式转向电容式,多点触控(multi-touch)这一软件理念得以实现。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导电性,使得手机专为人的手指所掌控,而非电阻屏时代可被任何材料操控。基于这一理念的技术剧本取消了作为物理中介的按键和电子笔等,屏幕从系统显示器升级为操作界面,以极佳的灵敏度支持手指控制屏幕的丰富手势,包括滑动(swipe)、轻按(tap)、挤压(pinch)和反向挤压(reverse pinch or unpinch)。多点触控突破了电阻式触摸屏时期的单点触控,拓宽了人与手机屏幕的具身互动,且这种互动越发灵活和生动,人机互动更贴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例如,多点触控中的反向挤压就是手机在用户操作之后给予的反馈。人体的热力和导电性经过技术转译,引发界面操控的变化,硬件、软件、湿件就在物质性层面上建立了可通约性。而这一技术原理,也为湿件的概念意涵提供了鲜明注脚。
基于以上三个特性,手机主屏幕形成了复合空间,也形成了“技术剧本”的舞台。这类技术剧本规定了用户的“手势”,引导其具身操演。固然,不同品牌厂商形成了不同的理念和技术剧本,但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手机软件系统设计以美学风格的“苹果化”、功能设计的“安卓化”趋势走向了统一。苹果公司的iOS系统通过各种手势设计,为主屏幕管理提供了基本方式。
手机主屏幕的技术结构是不稳定的、离散的、分布式的,更是具备多个层级的,并通过手势设计,形成了三种方式——切换、延伸、嵌入——来实现三维空间的建构。“切换”指的是不同页面和模式的更替。“延伸”指的是同一层级的横向拓展。例如,用户可自行设定主屏幕页面的数量,来不断拓宽页面空间。“嵌入”指的是不同层级的垂直拓展。例如,用户将应用程序归类进文件夹,或移动至“App资源库”。许多主屏幕功能本身也嵌入式地隐藏在页面中,从主屏幕页面右上角向下轻扫,用户即可打开控制中心,可以快速访问包括手机模式、无线局域网、蓝牙等重要功能。手机主屏幕的三维空间在“延伸”和“嵌入”中实现同延,在“切换”中实现移动运转。
(二)封面装修:用户对手机壁纸的设置
手机主屏幕是一个复合空间,现今人们对手机主屏幕的管理不再局限于布莫尔等人所关注的二维页面上的图标排列与整理(23)Matthias Böhmer,Antonio Krüger,“A Study on Icon Arrangement by Smartphone User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13,pp.2137-2146.,而是体现为更复杂与更多变的空间设计。在“我的桌面”豆瓣小组中,小组成员分享自己经验时常常用到“装修”这个动词。人们把手机主屏幕与居住的家庭空间相类比,通过多层次的实践活动,使手机成为自己个性化的私人媒介物。
我们每日起床第一眼和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图像,往往是手机主屏幕的锁屏壁纸。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将手机壁纸视为最接近自己的媒介,并试图通过壁纸来改变自己的外在表情。(24)Young-Hoon OH,Da-Young JU,“Look at My Face:A New Home Screen User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sign,User Experience,and Usability, 2017,pp.146-163.访谈对象张美美将壁纸作为一种积极暗示的图像化,选择了一张在她看来十分辽阔的景象作为锁屏壁纸。壁纸中央有一个人驾着马车上坡,周围是裸露、宽阔的草坪,再后面则是层层叠叠的房屋。
我(很久)没有换过锁屏壁纸了。我记得这是有一次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换的,就感觉它(壁纸)很开阔,带给我很多想象的空间。它特别像我高中时期,或者是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自己所处的那种期待状态。你随时看到这张图,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就是有非常广阔的东西可以去想,这是这幅图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一点。(25)访谈对象:张美美。
人们在面对手机主屏幕时,即便深知这是一个厚度有限的扁盒子,也明白自己所见无非是一幅二维图像,却仍在有意无意地选择具有纵深感和延伸感的壁纸来打造这一复合空间,去拓宽自身感知和想象的边界。如张美美对应用程序文件夹的命名方式也非常别致,第一排用四个月相表情符号(emoji)来命名,第二排分别命名为“Everything”“Will”“Be”“Ok”,连成一句“一切都会好的”。(如图1所示)每一个单词在几何排列中遥相呼应的同时,共同所组成的这句话也与张美美的锁屏壁纸相呼应,成为她积极暗示自己的方式。作为嵌入日常生活并贯穿各种情境场景的界面,手机主屏幕很多时候超越了实用的技术功能,成为一个自我表达和对话的空间,一面映照自我的镜子。用户们使用图片、文字和表情符号,变换颜色、字体和位置,通过多重的组合和排列,书写着一首首赛博装置诗。

图1 张美美的文件夹命名
常作为锁屏壁纸的还有人物肖像。(26)Young-Hoon OH,Da-Young JU,“Look at My Face:A New Home Screen User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sign,User Experience,and Usability, 2017,pp.146-163.这与手机屏幕的竖屏特性有关,也模拟了画框隐喻。早期计算机有水平和垂直两种主要视图形式,且名称与两种绘画类型一模一样。水平形式被称为“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垂直形式则被称为“肖像模式”(portrait mode)。(27)Lev 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MA:MIT Press,2001,p.95.计算机壁纸常采用横屏的景观模式,而手机壁纸常采用垂直矩形的肖像模式。很多用户将家人、恋人和偶像的肖像作为锁屏壁纸。轻轻点按一下手机屏幕,思念的人即会出现。锁屏页面成为一副相框,其作用就如同过去老怀表指针后的人像,或者出门远行时钱包里夹着的一张照片。手机不是人体的延伸,也不是延伸的“人体”,而是人体的“器官”。(28)黄旦:《“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第23页。那些附着情感的壁纸,和人一道在空间中移动,形成一种陪伴。除了用户自定义和系统默认的静态壁纸外,安卓手机还会提供随机壁纸功能,即每次打开锁屏屏幕时会显示出不一样的图片和配文。有用户就会重复解锁、锁屏、再解锁这一连串动作,通过看更新的壁纸来打发时间。
相比锁屏壁纸,主屏幕壁纸的图像景物更为简洁,使得应用程序图标更为清晰可见,以避免出现视觉不协调。(29)Young-Hoon OH,Da-Young JU,“Look at My Face:A New Home Screen User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sign,User Experience,and Usability, 2017,pp.146-163.同时,应用程序图标和文件夹的排列也可能因壁纸的不同展现出新的几何样貌。小陈是《创造营2021》选手井汲大翔的粉丝,她把井汲大翔的照片作为自己手机主屏幕的壁纸,并将应用程序的图标和文件夹围绕人像排列,以防挡住人脸。(如图2所示)
这个壁纸比较不固定,我经常会换。这次选井汲大翔是因为追选秀追的他,也给他花了钱。他太可爱了,看他就像看儿子一样,所以就选择把他放在桌面,想要每天都看到他,选了一个直接怼脸的正面照……图标和文件夹的位置一般我都不会太动,但如果换壁纸的时候文件夹挡住人脸了,我就要把文件夹和图标移开。(30)访谈对象:小陈。
除了将偶像设置为壁纸之外,也有像豆瓣用户“金岛嘤”这样的粉丝,不仅围绕着人像壁纸进行图标和文件夹排列,还将带有偶像照片的小工具纳入其中,并在这些偶像元素的组合考量中,避免空间前后的视线遮挡,以实现复合空间内错落有致的层次堆叠。(如图3所示)

图2 小陈的手机主屏幕页面 图3 金岛嘤的手机主屏幕页面 图4 大老师的手机主屏幕页面
访谈对象大老师十分热衷于“装修”自己的手机主屏幕,几乎每两天就要更换一次壁纸,但有两个元素是不会更换的,那就是对结婚纪念日进行计数的Days Matter和显示结婚照的小工具。(如图4所示)相比频繁更换壁纸,大老师并不挪动这些有着纪念意义的板块。不仅如此,她丈夫的手机主屏幕,原本属于“理工直男”的实用主义风格,也在她的代为管理下匹配上了这些与整体风格有些格格不入的“花哨”小工具。在两个不同的手机终端上,大老师用同样的主屏幕布局设置使得她和丈夫二人处于共在空间之中。手机主屏幕的复合空间特性再次得以凸显,它既承认物理空间中相对距离的遥远,又表现出虚拟空间中的毗邻。(31)Adriana de Souza e Silva,“From Cyber to Hybrid: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Vol.9,No.3,2006,pp.261-278.
无论是选择“睹物思人”的壁纸,还是排列文件夹名称书写的赛博装置诗,又或者是通过主屏幕的相同布局来建立联系,用户们的实践可谓丰富多彩,甚至显得浪费了许多时间和位置来做“无用”之事。手机主屏幕脱离了界面是“功能”而非“表征”的既定框架。(32)祁林:《界面革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187页。事实上,界面是可以包含非功能性内容的,对界面的讨论也不能只停留在“界面是否友好”的应用性设计标准之上。从物质性、符号或美学角度来理解界面,是界面文化分析的纲领性主题。(33)[英]尼古拉斯·盖恩、[英]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
(三)内部的排列组合:用户对应用程序的创造性管理
基于手机厂商撰写的“技术剧本”,用户对个体手机主屏幕进行再造。这种再造并不拘泥于技术剧本的固定逻辑,而是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使用频率是最常见的原则,但它不指向真实的使用频率,而是指向对使用频率的期待和想象。布莫尔等人认为,用户会根据自身真实使用应用程序的频次对图标进行排列,将使用最多的应用程序图标放置在第一个主屏幕页面,使用最少的应用程序图标则放置在最后一个页面。(34)Matthias Böhmer,Antonio Krüger,“A Study on Icon Arrangement by Smartphone User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13,pp.2137-2146.然而,用户对自身使用时间和频次分配的认知是模糊的。手机屏幕是具有同延性的复合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手机所运作的任何程序和页面在时空上没有边界。并且,这一复合空间没有中间(in between),一切页面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与抵达是平滑自如、“单击即可”(one tap away)的状态。(35)Adriana de Souza e Silva,“From Cyber to Hybrid: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Vol.9,No.3,2006,pp.261-278.“人们拿着手机,常常处于一种疆域无限且心神涣散的场景,虽然有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但我们不是在一个充满各种歧路的花园中有目的、有计划地散步,而是突发奇想、三心二意地玩一个跳房子的游戏,这个游戏是由许多落点、起跳点以及各种陷阱构成的。”(36)Johanna Drucker,“Humanities Approach to Interface Theory,” Culture Machine,Vol.12,2011,pp.7-8.复合空间的这种特性使得人们常常迷失在原本作为工具的手机里,使用手机常用“玩”或“刷”来形容,手的功能在大脑与眼睛的中枢操作之外凸显出来。“手本身所具有的认知和讲述能力,在数字移动媒介的条件下被彰显和开发。”(37)徐亚萍:《运动图像的操作化: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第55-75页。这突破了视觉中心主义,也提醒我们在所谓理性判断之外的身体潜能。应用图标管理的使用频率原则也因此被瓦解,“常用”的理性判断是暂时的,“随意”的无意识涣散行为弥漫在实际的手机屏幕管理及使用行为之中。
作为无意识行为的反面,也有用户试图通过主屏幕管理这一媒介实践来打破手机使用的病理性习惯。访谈对象小严就力图将自己的手机打造成工作机和学习机,而非游戏机;力图不被手机所操控,而是借手机实现自我管理。作为一名备战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大三学生,为了减少使用娱乐社交应用程序、进入高效率的学习状态,小严将自己的每日任务、扇贝单词等学习应用程序图标突出排列在第一个主屏幕页面,将微博、豆瓣等社交应用程序隐藏在了主屏幕末页的文件夹里,甚至直接删除了抖音、王者荣耀等娱乐应用程序。在学习时间里,小严还会将休闲娱乐的主屏幕末页隐藏起来。一般来说,一旦用户确定了手机主屏幕的总体布局,就不会轻易变动。甚至在更换新手机的状态下,用户对手机主屏幕的管理往往也会延续上一部手机的媒介习惯,以满足自身交互偏好,维持跨平台的一致性和私人化管理。(38)Jonna Häkkilä,Craig Chatfield,“Personal Customisation of Mobile Phones:A Case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4th Nordic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Changing Roles,2006,pp.14-18.在形成主屏幕的空间记忆之后,用户适应新的手机主屏幕布局需要时间成本。而小严恰恰就是利用反空间记忆,时常更换应用程序所在位置,变动自己的手机主屏幕布局,来使自己的手机主屏幕陌生化,以达到应用程序的期待使用频率,实现理想的手机使用状态。
你经常点开微博、豆瓣之类的娱乐应用程序,原因就是它在你很熟悉的地方。你无聊的时候下意识就打开手机点开它们了,然后就会花很长时间去玩。我不想浪费这么多时间在那儿,所以我就把各种各样应用程序混杂在一起,让自己对它们的位置不那么熟悉,就不会经常点开了。(39)访谈对象:小严。
布莫尔等人将用户划分为新手用户和专家用户,并指出新手用户往往依据手机系统所推荐的归纳方式来管理和命名应用程序文件夹,这就是外部原则。(40)Matthias Böhmer,Antonio Krüger,“A Study on Icon Arrangement by Smartphone User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13,pp.2137-2146.其实,用户对手机主屏幕还有更为消极的管理办法。有些用户任由应用程序图标根据下载顺序自动排列,一页排满后就继续生成新的页面,其余设置则依据手机系统的默认模式不予更改。如访谈对象Soap连基本的主屏幕管理功能都不加理睬,不使用文件夹归纳应用程序图标,而是任由这些图标散落在主屏幕页面上。对这些用户来说,厂商技术剧本的设计再丰富也是无关紧要的。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在比较传统画框和计算机屏幕视窗时预言:“基本上,画框原有的秩序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叠加或平铺的秩序。”(41)Norman Bryson,“Summer 1999 at TATE,” 2015,http:∥artasiamerica.org/documents/6307,August 10,2022.手机主屏幕的文件夹、APP资源库等分类设计试图形成清晰的逐级收纳,深入垂直空间。然而,如Soap一样的用户的手机主屏幕空间试图反抗这种垂直、纵深、叠加的规则,而是形成平铺和延展的平面。
可能因为我是“平铺型人格”,我喜欢把所有东西摊在一起横向对比,会感觉比较清晰,但也会被人说很杂乱。这个世界大部分时候是为“堆叠型人格”设计的。(42)访谈对象:Soap。
无论是使用频率原则,还是外部原则,在用户的实际管理行为中都受到挑战。布莫尔等人总结的五项原则看似清晰合理,却难以解释复杂万端的用户行为。实际上,唯一可能的原则就是“情境化”的原则。手机屏幕的复合空间与用户的地理空间、社会位置、流动性有机融合起来,形成虚实交织的“情境”。访谈对象安娜将大众点评、亿通行、携程旅行、去哪儿、滴滴打车和爱彼迎等应用程序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并将这个文件夹命名为“dududu”。
“dududu”就是汽车的声音,意思就是我要出门了,这些应用程序都是我出门在外所需要用的。(43)访谈对象:安娜。
访谈对象老王也将海岛奇兵游戏等娱乐应用程序与携程旅行等旅游应用程序归类到一个文件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应用程序都是外出路途上的应用,或者有实用功能,或者用于消遣。另一位访谈对象陈磊是一名编剧,外出时常用“京东读书”等应用程序,为了能够方便进行单手操作阅读电子书,就将这些程序排列在了“程序坞”这一单手操纵最容易接近的主屏幕区域。
正如德·苏扎·席尔瓦指出,作为移动界面,手机主屏幕的复合空间植根于移动性与通信之间的勾连,并通过同步发展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社会网络来实现。(44)Adriana de Souza e Silva,“From Cyber to Hybrid: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Vol.9,No.3,2006,pp.261-278.手机的空间不是独立且割裂的,而是伴随着人的行动在城市或乡间不停移动,主屏幕的使用因此融合在人们所处的空间环境和诸多生活情境之中。如果手机应用图标管理有原则,那么它只能是情境化原则。
(四)走向屏外:手机主屏幕管理与社会文化身份
既然手机屏幕管理是情境化的,那么,社会个体的身份与关系也必然会介入相关的实践之中。在调查中,有两类人群引发了笔者的关注,一类是老年群体,另一类是视觉障碍群体。这也导向了有关手机屏幕与人类感官之间关系的讨论。
在手机用户中,老年人多半属于所谓的新手用户,无论是手机使用程度还是媒介素养,抑或是建立界面心智模型的能力,均不及年轻用户群体。(45)Martina Ziefle,Susanne Bay,“Mental Models of a Cellular Phone Menu.Comparing Older and Younger Novice Us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2004,pp.25-37.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视觉能力也相对受限。手机厂商因此推出所谓的“老年机”,它的屏幕及管理也具有独特性。老年人的专用手机多半是市面上屏幕尺寸最大的型号,在主屏幕管理方面,主要提供的是应用程序排列整理等基础功能,其余多为默认设置。主屏幕页面往往简洁大方,较少使用文件夹,图标和字体大小也被调成最大显示模式,力求视觉效果上的清晰可见、操作上的简单直接。
此外,老年人的手机可能会由子女来进行辅助管理。以在北京工作的老张给自己在山东的父母买新手机为例:
我没有直接寄到父母那里,而是先寄到我自己家,我装好APP,设置好桌面,再寄给他们。我先问了他们现在用哪些APP,然后下载相应的,并且多下载了一些同类的,以及我估计他们会需要的。我把字体设置成“巨无霸”,没有把应用程序分组放进文件夹,而是直接分类罗列在屏幕上……我估计他们最常用的APP是4个,微信、电话、短信、相机,所以把这4个放在最底下的常用程序坞。(46)访谈对象:老张。
对于视觉能力受限的老年人来说,通过 “放大显示”“粗体文本”等功能的设置,问题相对易于解决。但是,对于视觉障碍人群来说,情况就更复杂了。智能手机厂商普遍设置了“读屏”“语音控制”等功能,为盲人提供服务。iOS等手机系统还为色盲人群提供了“色彩校正”功能,包括为红色盲人群配备了“红/绿滤镜”,为绿色盲人群配备了“绿/红滤镜”,为蓝色盲人群配备了“蓝/黄滤镜”。一位小红书用户有色弱的视觉障碍,手机主屏幕在过去四年里一直使用的是“黑白简约风”,在发现了手机色彩校正功能后,他立马将手机主屏幕主题更换成了彩色。
原来微信是绿色的,TIM是蓝色的?!原来淘宝居然是橙色的?!原来真实世界的颜色这么明显。我把色弱校正模式开开关关好多次,来比对前后看到的颜色。(47)小红书用户页面。2021年10月30日,http:∥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17d27ac00000000102a4b4?source=question,2022年9月1日。
此外,部分并无视觉障碍的用户也巧妙使用色彩滤镜为自己服务。访谈对象小葫为了减少使用抖音、小红书等娱乐应用程序,就打开了手机系统灰度的色彩滤镜,让自己的手机失去色彩,变成完全的黑白色,她将这种方式称为自己的“防沉迷”系统。另外,还有用户为了追求“墨水屏”的阅读效果,在浏览电子书时打开黑白色彩滤镜。
无论是视觉能力受限的老年人,还是存在视觉障碍的盲人或色弱者,抑或是巧用色彩滤镜的健全人,都提醒我们视觉在手机屏幕管理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屏幕设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视觉中心主义。那么,其他人类感官呢?以手指触控动作为主要交互方式的手机屏幕,必然涉及触觉问题。
触觉也可能存在肢体障碍。屏幕厂商也为有手部颤抖、灵巧度或精细动作控制方面困扰的用户群体开放了多点触控响应方式的调节路径,以识别更快或更慢的触控,以及忽略多次触控。更重要的是,多点触控在考虑到不同生理特性的身体时,也在形塑人整体的生理姿态。原本拿着笔时右手五指的共同行动,变成了无名指或大拇指的单独运作。即便回到书本和纸页面前,我们还会陷入翻书页不自觉戳戳纸张右下角时的恍惚,又或者想要连点两下,放大书本上的某一图片。这种错乱感提醒我们,界面的技术剧本在迎合着人的身体,而界面的动态本质也在重塑着具身行为。这套建构行为把我们的身体和感性装置与一种迅速变化的模式联系在一起,这一切被整合到一种复杂的经验中去。(48)Johanna Drucker,“Humanities Approach to Interface Theory,” Culture Machine,Vol.12,2011,p.15.这种新的感官体验也深深渗透进了手机主屏幕的管理。
人持手机时是单手还是双手操作,使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对应着手机主屏幕管理的差异。一般用户主要以右手单手操作手机,并习惯用大拇指进行点按。屏幕位置不同,手指触摸、点按的难度也有所不同。随着手机屏幕尺寸越来越大,单手操作难度陡增,顶端的应用程序基本处于触控盲区,相较之下,屏幕的下半部分是容易触及的,并且惯用手方向部分的可触及范围更大。因此,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或是在移动状态下单手操作的应用程序,往往被置于程序坞(主屏幕最下方)。人与界面之间的交互,还存在“解放双手”的情况。随着自动语音识别技术(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的发展,人机交往逐渐实现超时空人际交流的回归。如何启动一款应用程序也会影响其图标在主屏幕页面中的位置。访谈对象老王就将依赖语音唤起的应用程序,直接放于靠后的页面或页面的边缘位置。
除了百度地图,我基本上把导航软件都放第二页面了。车载应用基本上都是用“小爱同学”唤起,所以我就不会把它放在主页面上。一般如果要导航,就直接喊语音助手,它就会出现了。(49)访谈对象:老王。
传统媒介的感官流程多半是一种“眼睛观看—大脑理解—手动操作”的机械流程。(50)祁林:《界面革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181-198页。在管理屏幕时,人置身在界面这一复合空间中,会调用和发展更复杂的感官经验。与此同时,五官感觉、身体的移动性、人的能力和行动能力也被放大和重塑。(51)喻发胜、张王月:《沉浸式传播:感官共振、形象还原与在场参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96-103页。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感官体验也得以显现。
四、结语
手机主屏幕究竟是什么?从外表形态上看,它是形状长大于宽、以玻璃为基础材质、封闭且隐秘的扁盒子;从硬件设计上看,它配有电容式触摸传感器,能与人之间产生灵活的交互;从操作逻辑上看,它以“切换”“延伸”“嵌入”的方式,实现了二维平面之下的复合空间建构,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具身操演的舞台和技术剧本。
对形形色色的用户来说,手机主屏幕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和人体一道在空间移动,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贯穿着用户的日常生活,手机主屏幕成为用户进行自我表达和情感寄托的数字画框、实现理想自我的数字镜子、走向广阔社会关系的数字窗户。从手机壁纸的更换,到应用图标的排列,“情境化”是最突出也是最可靠的实践原则。老年人和视障群体有自己的主屏幕管理方式,而无论是生理受限者还是健全人,也都随着主屏幕的使用延伸出新的感官经验。即便基于同一个技术剧本,通过手机主屏幕管理这一媒介实践,用户也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数字日常生活。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曾经指出软件之下的专制主义(52)Friedrich Kittler,“There is No Software,” Ctheory,1995,pp.10-18.,这种专制主义恰恰被媒介硬件和具身实践所瓦解。手机主屏幕管理只是当代数字媒介技术得以展开的一个切面,它使我们得以窥见媒介技术世界的纠缠状况。“界面”,既依赖物质性基础,也依赖软件设计,还依赖人的具身行为,它是虚实空间的中介,照亮了人与技术相互关联的另一个面向。软件、硬件、湿件相互连接,在社会情境中生成为整体性的媒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