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噪声防治的法治解构与完善路径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韦冉,郑淑裕
(1.山东警察学院经济犯罪侦查系,山东 济南 250200)(2.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250200)
海洋环境噪声是指在海洋中由水听器接收到的除自噪声以外的一切噪声,依其来源的不同可分为生物噪声、地震噪声及人为噪声等种类。[1]其中基于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海洋人为噪声包括船舶航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海洋油气钻井平台在开采活动中产生的噪音以及军舰操演中声纳的应用等。[2]在法律实务中对于海洋噪声是否应受规制的观点不一,主要由于其危害并非如传统环境污染公害一般会对人类的身心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既往研究者对海洋声学的关注通常落脚于其在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探测潜艇的方法,研究仅关注于抑制噪声对声纳系统的干扰[3],而忽视了声波对海洋哺乳动物生存所产生的影响。在海洋环境中,生物受能见度及气味辨识度的限制,主要依赖声音这类介质进行沟通、觅食以及求偶,因而对其感知也更为敏锐。但随着人类对海洋探索规划的进一步展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噪声干扰也在进一步增加,暴露在高强度噪声之下的海洋生物,其听觉灵敏度会逐步减弱,当声级进一步升高,不仅会造成生物永久性的声损伤,[4]还会使其迁徙或死亡。基于海洋生物发声行为的特异性,除海洋哺乳动物受到人为噪声的直接影响外(1)Ben White’s Yucatan Diary. https://aw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documents/ml-benwhiteyucatandiary-092711.pdf,海洋爬行动物以及无脊椎动物(2)Vermeij MJ, Marhaver KL, Huijbers CM, Nagelkerken I, Simpson SD. Coral larvae move toward reef sounds. PLoS One. 2010 May 14;5(5):e10660.Alderks PW, Sisneros JA (2011) Ontogeny of auditory saccular sensitivity in the plainfin midshipman fish, Porichthys notatus. J Comp Physiol A 197:387-398也可能因对高强度噪声的感知而在生理、行为及适应性方面发生转变,这最终将波及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及整体平衡,危及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保护。
在已有的国际法律框架下,尽管尚无解决海洋人为噪声问题的专门性公约,但仍可依有关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性条约对海洋噪声污染进行治理,且目前区域性的国际法律文本已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相关措施与解决办法,部分发达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国内立法进程与国际法在水下噪声规制领域的转化。反观我国为噪声污染规制而出台的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噪声的定义仅限于对他人生活、工作、学习所造成的干扰,而航道区域等水下环境产生的船舶噪声对其间生活的鱼类等生物造成何种干扰,尚无国内法给予关注。[5]当前以南海为代表的海域环境正承受着多元化的人为噪声侵扰,相应区域内生物搁浅数量正日益增长(3)参见我国沿海群发性鲸类搁浅,人为水体噪音或是最大诱因[N].新京报,2022-01-22.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1-22/doc-ikyamrmz6833953.shtml.145头鲸鱼搁浅,环境噪声污染已经超乎你的想象[EB/OL].https://www.hzjzy.com/hangy/270.html.,妨害着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尽管目前联合国并未将海洋噪声污染列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但已有海洋区域合作协定对此问题进行探索,因而笔者试图从现有问题出发,综合考察该议题下国际造法的进展及相关国家实践,提出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既有模式下,我国对海洋噪声的规制及实践方案,以期在海洋人为噪声治理领域有所总结,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现行海洋噪声污染的法律规制进展及实践
海洋噪声作为一种非传统威胁,认定其对生物及所处环境产生损害的过程是复杂且有争议的。倘若依据管理风险的传统方法:“只有在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确定损害”的情况下,才有理由采取保护环境的行动(4)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Decision (United States v. Canada). 35 AJIL (1941). 648-736, at 716.,那么在等待结论性证据的同时,海洋生态可能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害。有鉴于此,学术界及相关国际机构对生物多样性可能受水下噪声影响的程度开展了广泛调查,这一过程也得到了来自国际层面的关注,一些国际和区域机构也通过会议决议的形式,对水下噪声管理的必要性进行了确证。
(一)海洋噪声污染治理的国际法规制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作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达成的一项国际协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设定旨在为海洋及其资源的利用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法律制度,因而也被称为“海洋宪章”。尽管在广泛性与影响力上无出其右,但碍于制定时间的久远,难以避免其内容存在滞后性:在公约中无直接涉及人为水下噪声的相关内容。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并“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5)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及第194条第1款。,现有证据已能够证明军用声纳的应用与鲸鱼搁浅的发生存在直接联系(6)Navy sonar and cetaceans: Just how much does the gun need to smoke before we act?[EB/OL].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5326X08002221.,这足以满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有害影响”(deleterious effect requirement)的定义。联合国大会也通过非正式协商会议(UNICPOLOS)提议对海洋噪声污染进行防治,依此而形成的相关协定与决议(7)Statement by OceanCa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Noise Coalition[EB/OL].http://oceannoise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OceanCare-IONC-Statement-ICP-19-11-06-2018-final.对缔约国减少人为海洋噪声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2.《生物多样性公约》
作为第一项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全球性协议,其保护生物资源的初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接纳。序言中强调,“一些人类活动正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减少”,纵观全球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始终未进入主流视野,且下降的趋势也未得到根本性遏制,究其原因在于从科学共识到政治协议达成的漫长过程,限制了环境治理活动的开展,对生物的保护囿于“能力与意愿”,[6]致使诸如“人为海洋噪声”的规制踟蹰不前。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在2014年的第 XII/23号决定(8)Intergovernmental Decisions and Academic Bibliography relating to Marine Species and Anthropogenic Underwater Noise[EB/OL].https://www.ocean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Intergovernmental-Decisions-and-Academic-Bibliography-relating-to-Marine.敦促缔约方采取诸如:绘制声音时空分布图、对噪声活动可能造成的重大不良影响进行评估监测等行动,但实际推动落实的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鉴于鲸鱼及海豚等易受到人为海洋噪声威胁的生物已成为全球公认的濒危物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国应主动参与海洋噪声管理规范的制定。
3.《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其目标在于通过订立具体的国际协定,在政府间开展针对迁徙与洄游物种的跨国界保护行动。《公约》第3条第4款第3项指明:缔约国应当“在可行和适当的范围内,预防、减少或控制正在危及或有可能进一步危及该物种的各种因素”。除“外来物种”可能对生物的生存繁殖带来威胁外,人为海洋噪声的产生及强度的增加也可能是生物栖息地衰退的重要影响因素(9)ADVERSE IMPACTS OF ANTHROPOGENIC NOISE ON CETACEANS AND OTHER MIGRATORY SPECIES[EB/OL].https://www.cms.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ms_cop12_res.12.14_marine-noise_e.,各国有必要也有义务对海洋噪声的治理采取行动。在2017年第十二次会员国大会中也重申了对近海风力发电厂及航运噪声开展国际协调研究的必要性,希望能最大限度的降低航运噪声对海洋生物群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中国还未加入此项公约,但对政府间协调开展迁徙物种保护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认可,在积极参与中华白海豚及迁徙候鸟的跨界保护中,积累了跨国界物种保护和管理的经验,[7]有望为未来海洋生物的保护提供大国智慧。
(二)各国有关海洋噪声污染的治理实践
1.欧盟国家
欧盟国家间受地理位置特殊性影响,海洋活动的范围常越出周边区域,这使得在积极利用海洋产业和能源谋求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也更能领会丰富且脆弱的海洋对经济、气候及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先后通过决议和战略,推动欧盟对“两洋”和“四海”(10)“两洋”和”四海“分别指大西洋和北冰洋,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生态环境养护,以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针对海洋噪声,欧洲议会于2004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8]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完成对海洋哺乳动物、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累积环境影响的全球评估之前,暂停在管辖水域内部署高强度声纳”。2008年,欧盟在“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的基础上颁布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保证于2020年实现海洋资源及生态系统的良好状态,其中首次明确将人为水下噪声纳入污染定义,强制其成员申明并确保“水下噪声将保持在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
出于各海区的特性及能够便于协调区域内各国开展海洋哺乳动物的保护活动,欧盟制定了相关区域合作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保护波罗的海、东北大西洋、爱尔兰和北海小鲸类的协定》(简称ASCOBANS)及《关于保护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鲸类动物的协定》(简称ACCOBAMS)。ASCOBANS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对人为水下噪声进行规制的国际法律文本,从第三次缔约国会议开始,陆续提出使用预防性方法解决海洋噪声,呼吁在区域层面与其他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开展合作,从国家层面引入审批程序以加强对人为活动的干预。(11)Resolution No.9:Managing Cumulative Anthropogenic Impact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EB/OL]. https://www.ascobans.org/en/document/managing-cumulative-anthropogenic-impacts-marine-environment-0.ACCOBAMS在2004年通过的第3.10号决议中承认人为海洋噪声是一种危险的污染物,并请各缔约方对水下噪声活动实施缓解和监测措施、在海洋哺乳动物活动的关键区域周围设置缓冲区(12)RESOLUTION 3.10 GUIDELINES TO ADDRESS THE IMPACT OF ANTHROPOGENIC NOISE ON MARINE MAMMALS IN THE ACCOBAMS AREA[EB/OL].https://www.accobam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ACCOBAMS_MOP3_Res.3.10.。提议优先进行高质量研究的同时,绘制并确定海洋哺乳动物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计量范围,即“人为水下噪声地图”,这便于各国了解海洋噪声的生成现状及其对鲸类的影响,使采取的规制措施更具可操作性。
2.美国
人为噪声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一直都是美国最高级别的科学研究主题。1995年的海洋气候声学测温实验促使公众开始关注海洋噪声污染,其后在《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中为声音水平设定阈值,以防止海洋哺乳动物受到“伤害”或“行为骚扰”。[9]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在1999年发布的白皮书中对海洋人为噪声的增加提出了监管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新的海洋生物保护区、将噪声污染标准纳入国际协定并制定有关噪声污染监管的区域协定。[10]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作为管理美国海洋资源及栖息地的组织,其领导下的国际海事组织于2014年在小组内批准了船舶减少噪声的自愿原则,以激励建造和改造船只、降低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其2016年所发布的海洋噪声战略路线图(13)Ocean Noise Strategy Roadmap[EB/OL].https://cetsound.noaa.gov/Assets/cetsound/documents/Roadmap/ONS_Roadmap_Final_Complete.被认为是了解和评估噪声对海洋生物的慢性影响,用以指导未来海洋活动的重要参考。
海洋噪声战略路线图绘制的重点本是对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慢性噪音(chronic anthropogenic noise)进行评估,但夏威夷地区军事主动声纳训练演习的噪声测绘,使军用雷达的使用进入了噪声规制的范围。[11]国际捕鲸委员会及美国海军声纳专家都一致认为,低频声纳的使用是导致鲸类大规模搁浅的最重要因素。2016年7月,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裁定美国海军违反《海洋哺乳动物法》,这一判决推翻了温特案所确立的国家安全至上的利益选择。温特案裁判的历程也体现出美国社会在环境利益与其他社会利益间的平衡与抉择(14)海军演习是美国过去三十年海洋哺乳动物搁浅诉讼的主题,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就海军执行安全任务与海洋生物福利的保护产生分歧(以温特案为代表)。NRDC v. Evans, 364 F. Supp. 2d 1083 (N.D. Cal. 2003), appeal dismissed, NRDC v. Gutierrez, 457.F.3d 904 (9th Cir. 2006).,在无法永久禁止海军使用低频主动声纳进行训练和测试的情况下,法院仅限制其不得在海洋生物特别丰富的地区使用,其后美国海军自行豁免其在“环太平洋”演习中声纳的使用,使军事活动的开展,在“国防必要时”可免受《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的约束(15)。但即使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区域已被证实属于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栖息地(16)Van Parijs, S. M., Curtice, C., & Ferguson, M. C. (Eds.). (2015). Bi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s for cetaceans within U.S. waters. Aquatic Mammals (Special Issue), 41(1). 128 pp.,NOAA仍未采取相关限制或缓解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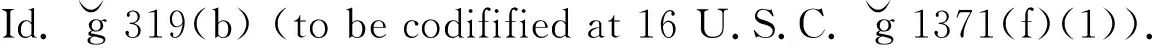
3.加拿大
加拿大对其管辖水域海洋噪声的管理,既不同于欧盟具有《海洋战略框架》可综合指导海洋生物保护;也不具有如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的法律框架,能对海洋哺乳动物给予特别关注。加拿大对海洋噪声的关注基于海洋哺乳动物种群能否满足可持续消费利用的需要。相较于美国仅将声学作为重要而非主要威胁的组成元素,加拿大通过2010年联邦法院的一项裁决(17)Federal Court, 2010. David Suzuki Foundation v. Minister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2010 FC 1233. Affirmed, 2012 FCA 40.,迫使联邦政府在海洋哺乳动物的行动计划中承诺:对关键栖息地声学成分进行保护,将水下噪声列为至少两种濒危鲸鱼物种关键栖息地的威胁要素。[12]
此外,加拿大对海洋哺乳动物的保护散见于《渔业法》、《国家海洋保护区法》及《濒危物种法》等法律中,由《海洋法》为海洋战略及生态系统保护提供指导,授权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但目前仍未商讨出一个总体性的针对海洋噪声的管理和缓解办法。[13]同时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商业渔业,而依照加拿大《海洋哺乳动物条例》,禁止扰乱海洋哺乳动物的前提是未处于捕鱼状态,这使得《渔业法》中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免受海洋噪声影响依旧停留在理论层面(18)Canada Marine Mammal Regulations(Section 7)[EB/OL].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sor-93-56/FullText.html.。《濒危物种法》作为保护濒危海洋哺乳动物的有力工具,一旦物种经由加拿大濒危野生动物状况委员会(COSEWIC)评估列为濒危或受威胁物种,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DFO)就必须为其确定并设立关键栖息地。DFO已为极易受到干扰、容易产生搁浅或觅食中断等不利影响的鲸类建立海洋保护区域,并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等易产生噪声的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限制。对于区域性或海岸范围内的水下噪声,加拿大计划开展海洋空间规划,促使具有监管权的机构间进行综合而广泛的协商,对于能源管道或航道是否对鲸类栖息产生影响确立科学评估与监管审批的双重标准。[14]
二、海洋噪声污染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理念变革
(一)海洋噪声污染治理的局限
1.国际海洋法律体系的碎片化
近代国际海洋法的一大特点在于将海洋分区划块治理,这既是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也是海洋大国争夺规则话语权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创设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海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属性,人为的海域划分也使海洋在地理空间层面呈现出严重的条块化状态。海域、区域的不同使海洋法制度的设置存在差异,海洋法律体系也明显呈现出碎片化特点。[15]具体到海洋噪声污染的规制,迄今并无专门调整该问题的开放性条约,且目前所推行的若干区域性或是国家间的尝试,也糅杂着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基于海洋资源有限性与海洋生态脆弱性的共同认知势必会推动在海洋事物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国,操纵国际规则以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为争夺海洋规则话语权而提出的理念、主张与制度构想并不能使各方主体对海洋资源保护建立共识,国际社会在海洋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实质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
2.国际海洋法律规则供需失序
各国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殊性,使现代国际法在发展普遍性规范的同时,基于区域共同利益而制定的协议规范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6]相继产生的一系列区域或次区域法律文件,成为了比国际法更为发达的法律形式。在海洋噪声治理中,出于对国家及区域性组织的依赖,区域性海洋规则多符合本国利益或适宜区域发展,往往导致区域性制度林立而缺乏应对全球性海洋危机的国际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仅限于针对环境保护作出普遍性原则规定,对于可否将海洋噪声归结为跨界污染的一种形式,[17]仍未得到国际条约的肯定;其能否对海洋噪声进行强制性约束措辞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约的约束力。对规范的模糊化处理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各国对海洋噪声危害的认知并不如微塑料污染或气候、难民问题深入;二是各国对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养护的关切不同,这也使全球性规则的制定阻力重重。而主张“尽量”谋求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合作,“鼓励、建议”各国调整并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以兼顾生态保护(19)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第1款第3项。的倡导性表述,使各缔约国更易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有利于本国的理解而否认缔约国在海洋噪声污染治理方面的义务。
3.海洋噪声规制实践中“搭便车”现象凸显
依据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作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作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享受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海洋资源属于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因受益主体的广泛且不特定,往往使应当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各国都试图追求最小的付出、甚至不付出财力和精力便可获取利益的共享。以南海周边国家对国际环境公约的加入为例,菲律宾是域内唯一签字缔约《迁徙物种公约》的国家,签署《印度洋、东南亚海龟及其栖息地的谅解备忘录》的周边国家也只增加了印尼与越南。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长期存在岛礁主权、海域划界、资源开发等争端,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各国对环境问题往往多从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难以建立集体认同、形成环境利益共同观。[19]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事务中“一与多”关系的存在,给各国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与空间,公约加入的自主选择性使各国往往难以形成对海洋环境治理的动力。相关国际机构的设立多为规范性而非操作性,仅履行沟通、协调及促进义务,难以真正发挥对南海海洋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职责。目前海洋噪声的治理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间、以围绕自身需求所实施的个别行为为主。对于公海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人为噪声,目前既无一个超国家集团进行管理,国家的行动又不能直接获得实在收益。因一方或几个相关方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责任,就很可能出现只由另外一方或几个相关方独自承担治理负担的局面,进而导致这一方或几个相关方也无力承担或不乐于承担责任,最终导致整个责任共担机制的崩溃。[19]就海洋这个大集团的困境而言,目前行之有效的方式仍是回到以区域为单位的小集团,以区域合作的形式开展海洋的保护与治理,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调动积极性;还能相互形成对照,便于监管以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
(二)“公海自由原则”迈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变革
1.传统海洋治理理念之弊端
在全球海洋治理及海洋噪声规制中问题的产生,可回溯至既往海洋利用理念的变化。格劳秀斯于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奠定了如今国际法与海洋法的基础,也使海洋自由思想成为海洋利用的理论依据,人类不仅要求对海洋本身享有公平航行、贸易的权利,对于海洋中的丰富资源也主张开放共享。随着对自然资源及海洋渔业资源探索能力的显著提升,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但鲜少能够对海洋资源的保护投以关注。“公海捕鱼自由”的国际法规则,使公海渔业资源正面临养护危机。格劳秀斯过去所主张的海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实际上已违背了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20],对海洋利用的观念,应当由海洋自由转变为海洋治理。
为避免海洋资源在全球海洋公域的应用与治理中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罔顾海洋承载力,致使“公地悲剧”的发生,海洋治理采取了产权化的治理范式以应对资源危机。[21]其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首创的“专属经济区”制度,不仅为海洋“公地”制定了细化规则,也使沿海国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行为更加理性、也更有内在动力承担养护义务。但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不仅限于人类的过度捕捞,更为主要且直接的威胁在于海洋环境污染(20)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五个主要威胁分别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海洋污染、生态环境改变、外来物种入侵、全球气候变化。。对于海洋噪声这类危害形式特殊,危害行为难以追溯,危害结果发生也更为隐秘且难以预料的污染物的治理,不能对海洋进行简单划界而应依海洋生态系统特性对责任进行明确细化,这不单单是主权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义务,更需国际及区域组织间的合作。为解决内部对海洋资源与权益的竞争,也迫切需要对国际实践及区域活动给予理论支撑。“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能有效克服上述弊端,其承继于国际法既往发展的成果,作为政治理念,其精神内涵也体现了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环境法原则,具有高度的法律性。[22]
2.“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噪声治理中的目标定位
更新海洋治理理念,实现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当今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传统海权国家依靠其海军优势及霸权地位,强行推行单方规则与秩序,这不仅使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也使海洋资源平等利用、海洋经济共同繁荣沦为空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政治斗争与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其为世界海洋所确立的法律秩序也不可能全面且准确,面对国际海洋法域以国家主权为导向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以共同体为导向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冲突,[23]海洋治理理念亟需变革。
海洋噪声污染、非法捕捞、海水酸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使海洋生态愈发恶劣,海洋是联通的海洋,是全人类的海洋,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整体性越突出,就越无法在面临海洋风险时独善其身,因而海洋噪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国建立合作、共迎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最具“中国智慧”的方案,不仅强调人类与海洋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倡导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24],也强调各国针对全球海洋秩序应重建对话与沟通平台、制定危机应对方案以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噪声的产生为例,行驶于公海的船舶,罔顾海洋生物保护而追逐短期效益,以邻为壑的现象常常出现。为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忽视他国环境需求,也终将因利益纠葛而陷入无休止的对立情绪之中。
因而海洋噪声的治理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使海洋回归其“共有物”的属性,对于海洋人为噪声的治理,应加强合作,以各国之合力共同应对,以对话协商代替武力争端,坚持开发包容,坚持共利合作,坚持与时俱进地参与海洋实务。[25]海洋的整体性与海洋活动的国际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的繁荣发展也不能仰赖于哪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应共同参与海洋资源的开发分配与海洋纠纷的化解。
3.“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治理中的价值彰显
海洋噪声规制的特殊性在于噪声源的可移动性以及传播所造成的跨界污染,在国家管辖范围内产生的噪声若无国内立法规范,则会产生国家主权间的冲突;若主动涉足国家管辖范围外噪声的治理,则又与公海自由原则相矛盾。[26]“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制度体系的核心要务是制定和确立各国普遍认同和愿意遵循的治理规则”[27],因此海洋噪声的控制除科学技术的指导外,还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兼顾利益分配与资源保护,指导海洋综合事务的管理。区域性条约对国际公约中的原则性内容,依地区特性进行细化以实现其可操作性,通过区域合作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有利于海洋安全环境的构建。海洋安全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综合性概念,不仅包括环境与气候变化之下人类生存危机的化解;也包括国际海洋秩序层面基于海洋权益之争的应对。相较于采取海洋执法或海洋外交的方式消除特定威胁,海洋战略的长期性要求建立并维护周边海域的安全、稳定,实现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这不仅要求海上各国的发展要兼顾近海优势与远海保障,还需推动构建区域及全球海洋安全秩序。“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树立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海洋安全观,是中国在共同维护海洋和平、共筑海洋新秩序、共促海洋繁荣发展的方案与智慧的提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关乎海洋治理的内容都带有着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预见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海洋争端的可能性,因而倡议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实现权、责、能的一体平衡,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对海洋的发展利用进行积极协商,与涉海非政府组织开展官方合作,推动构建海洋治理主体间相互尊重、和平稳定的发展道路。面对海洋噪声及海洋塑料等海洋污染问题与生态失衡所暴露出的海洋治理滞后性与有限性的现状,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应坚持技术合作、利益共享,以区域、国家及全球性为基础开展多层次海洋治理行动,以互利共赢的态度,实现人海和谐发展目标、共同探索海洋合作治理的新秩序。
三、海洋噪声防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构建
目前海洋噪声对海洋生物健康及海洋生态平衡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生物界、法学界等领域的重视,这不单是一个学科的任务,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事关海洋利用与发展的重大课题,其解决不单依赖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能力,更仰仗各国的有效参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保护海洋环境,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无法避开海洋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气候问题。
(一)国际层面: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完善
为解决目前海洋生态保护与噪声污染防治以“软法”为主要规制形式,造成国际社会无有力约束机制、逃避责任、困于利益纠葛的问题。海洋噪声的减控不仅需引进强制性的实施机制,以公约的广泛参与性昭示海洋噪声规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以后果的强制性保障各国切实履行海洋保护义务。更需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形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全球治理观,通过建立国际社会成员间的合作、信赖关系,弥补了国际法律秩序毁易守难的结构性特点[28],在协商共治的氛围下缔结更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还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非完全等同于全球共治。[29]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其序言中确定,应“本着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倡导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成果共享。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更注重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任何国家,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海洋命运共同体所建构的“共治共享”正在逐步打破专属经济区制度所构建的“专属专管”,在拓展海洋研究主体与维度的同时,使海洋的发展更好的致力于海洋秩序的可持久性、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海洋权益的可合理性享有[30],使海洋噪声等复杂问题得到全面的控制与解决。
(二)区域层面:建构基于海域特性的区域治理机制
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构建受到环境问题的跨国家性影响,面临机制冲突、合作不足等问题,相较于各洲间政治利益考量、意识形态对立、履约能力不同等现实原因,国家间的治理合作意愿更为强烈,区域化的组织或安排更易凝聚国家间的价值与期望,实现在海洋治理问题上的共识[31],区域海洋沿岸国也能更为平稳持续地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事业。
1.构建区域性海洋声学保护区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范围广阔且物种丰富,但因受捕鱼、航行、海底采矿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海洋环境及生态养护中所需处理的事务也更为复杂。参照区域海洋项目在地中海及东北大西洋范围内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进展,区域性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能够为海洋噪声治理提供思路借鉴。目前世界范围内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其目标在于对大型海洋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这与海洋噪声管制所欲实现保护的对象一致,因而海洋声学保护区的建立存在现实的建设标准。其最大的挑战在于海域主权归属的争议,以南海保护区的设立为例,为保护横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管辖权的生态系统,一般是建立跨界海洋保护区以满足管理需要,但实践中南海地区的复杂局势,使得任何对合作行动的支持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国家声索请求的间接承认。[32]
因此对这类争议地区声学保护区的设立应首先发挥区域性组织的协调功效,定期召开会议以协商人为噪声减控的行动计划与绩效指标,可考虑各成员国履约能力的不同,设定有针对性且具有一定强制力的议定书或制度性合作模式,以保证内容的有效实施;应允许邻近沿海国在海洋噪声的管理过程中享有特殊地位,在提案、磋商等方面具有优先权,适当顾及沿海国的合法权益。协助并督促声学保护区周边国家完成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监测,实现区域层面的信息共享与声学标准测定。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合作被认为是践行和推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方式[33],中国也需发挥自身域内大国的引领作用,在海洋噪声问题的管理中主动发声,适时推进争议海域海洋保护区建设。
2.防治海洋噪声污染的前期信息交流机制
环境问题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引起环境现象发生的科学认知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全面准确,面对可能危害海洋生物的巨大风险,国际环境法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即构建海洋噪声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从源头控制噪声的产生。
海洋环境信息平台的建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海洋生态安全信息数据库,库内应包含各监测站点信息,统一海洋噪声信息获取的频率、评估流程及公布形式。各国应对管辖范围内重点船只及海洋勘探活动进行登记,以加强区域组织对环境治理、安全预警及生态修复方面信息的掌控。二是建设海洋生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各国应参与搭建信息沟通协作平台,参与海洋重大事件的信息监测与事件处理。对管辖海域内海洋环境及生物状况定期进行汇报和交流,以大数据的方式对区域环境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同时与国际接轨,实现国家间的信息交流与成果共享。三是强化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与管辖能力,监管机构应对汇报时限及程序作出标准化统一,对各国船只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超过监管标准的活动作出处罚;针对瞒报、漏报、错报的行为,应设定惩罚措施,以国际公报的形式刊发相关噪声排放情况。海洋环境的治理始终与海洋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为打破各利益主体间隔阂,实现环境保护成效的长期性,关键还在于加强各国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同,使各国建立对海洋环境治理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3.防止海洋噪声损害扩大的后期协调机制
事前预防尽管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风险的发生,但在探讨多元共治理论时,应将事前预防与事后协调相结合,建构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海洋噪声污染管理模式。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各国除以提供科技及资金的方式履行环境保护协作义务外,还可通过创设低息融资,使企业参与环境治理,这既能为生态保护行动吸纳资金,企业也可通过融资参与海洋保护进而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34]当各区域组织及联合国机构都参与融资,将势必改善各国经济实力发展不平衡、环境保护能力各异的现状,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多元主体协作。
对于海洋噪声跨界所产生的污染致损,可通过设立环境基金以提高各国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能力。首先需对赔偿对象进行科学分析,对于保护区内濒危海洋物种的死亡,可由保护区所属国向肇事国索取赔偿;而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保护区内海洋物种的死亡,肇事国应向区域内专设用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基金会进行赔偿;对于海洋噪声跨界所造成的公海生物资源损害,应由基金会代为垫付,由肇事国及其区域组织实际赔偿。对于海洋噪声已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可由各国通过技术与资金的相互扶持进行治理,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需要,落实“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将发达国家的援助义务进行细致化、明确化甚至见诸具体条文之上。这就需要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协调机制,这一协调机制能确保各国对区域框架公约内的内容与义务有效实施,也能加深沟通与信任,对治理进展及未来治理方略进行讨论与规划,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所设想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良性发展。
(三)国家层面:完善海洋噪声治理的预防机制
我国自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在海洋、大气、固体废物及动植物保护领域都设置了专门的法律法规,环境立法可谓是空前繁荣。但对于海洋噪声的防治,《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其是否属于海洋污染并未明确界定(21)《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4条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军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中,对于经上级批准的军事演习等因特殊任务产生的环境噪声不受规定约束(22)《军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环境噪声是指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在训练、实验、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生活等活动中产生的影响周围环境的声音,经上级批准的军事演习、打靶训练、飞行和执行其他特殊任务的除外。”。乃至专门规制噪声污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噪声污染的定义以及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制定都是从人类利己的角度出发,环境品质的好坏并未将水下生物所受影响纳入考量。因而我国的立法完善在借鉴《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等国际法相关规定的同时,也可考虑同步制定适于海洋的声环境质量标准、着手海洋噪声时空分布图的绘制,细化操作标准及行为准则,以满足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整体需要。
1.制定满足海洋噪声管理需要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依照噪声污染源可将海洋人为噪声大致分为频繁且可控的船舶水下噪声以及需要国际间协调缓解的军事噪声污染。而控制噪声源是控制船舶噪声污染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35]船体作为噪声生成的最主要来源,应在船体设计与船型构造阶段改进技术,优化材料以阻断噪声的产生与传播,但目前船舶的设计尚未考虑水生生物安全,缺乏专为限制船舶水下噪声而设定的标准。现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制定目的仅考虑“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对噪声污染问题的规制未融入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价值观念。
按目前构想,声环境质量标准的调整对象可大致分为两类:按船舶类型或是按区域的不同特性制定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具体而言,民用船舶依用途往往可以分为客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类型,按载重或动力装置的不同又可进一步细分,这就使同一类型的船舶在不同船速(23)对于同一艘船,船舶行驶速度越大,船舶辐射噪声声压级则越大。参见邸凌杰.长江上游航道散装货船水下噪声声源特性分析及生态防控措施[J].珠江水运,2021(12):28-31.或状态下其噪声的生成呈现动态波动状态。在单一噪声源的情况下(不考虑声波的叠加效果),由于噪声不具有累积性,船舶达标排放噪声的确能保证相应声环境的达标,但不同鱼类对同一噪声源所产生的影响和伤害也存在差异,无法确定合法的噪声排放是否会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的后果。若简单对航行中的每一类船舶设置固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值,不仅难于监测,整条航线中不同区域内海洋生物的保护要求也各有不同,因此以船舶类型划定声环境质量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可在出厂前按船舶类型设置噪声达标区间,对于建造完成或投入使用的未达标船只可通过强制加装消声器或隔声装置以降低船体噪声的产生。如若将声波的叠加效应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在多个噪声源同时排放环境噪声的情况下,即使每一个船只都满足噪声排放标准,也有可能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因此建议以海洋环境保护区为基础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在中心区域对航行船只的数量及频率进行限制,以区域生物特性为计量标准,设置动态的监管方案。
2.军事声纳使用的限制与监管
海洋军事和经济安全是海洋生态安全保护的动力和出发点,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但以维护地区和平、航行自由等名义开展的军事演习不仅会加剧海洋争端的升温,其军事活动产生的海洋噪声对海洋生物也将造成巨大影响。以南海地区为例,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保护海洋环境及生物是缔约国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当前国际社会对军事演习及其声纳使用所造成的生物损害却缺乏规制的直接法律依据。
中国政府在军事声纳的监管中,对外应强化东盟各国对海洋噪声污染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过程中,坚决反对美国等国在南海地区部署军事声纳探测装置及未经许可的军事活动。同时,在国内立法中对军事声纳的使用逐步增加限制,先阶段性暂停在主要鲸类及海洋保护区周围海域范围内部署高强度声纳,对军事演习的周边海域环境进行先期评估,同时开展战场生态要素调查及军事生态学研究,预测军事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敏感生境及物种的影响和变化,制定相应的维护、回避和修复计划。[36]为实现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还需加强海洋环境监管部门职能的履行。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中,海洋环境监管部门承担两种角色,一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权的主管机关,二是代表国家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主体。[37]海洋环境监管部门首先需要积极行使其行政职权,在行政层面对海洋噪声污染进行前期的监管与控制,避免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此外需充分发挥行政权力在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中的重要作用,通知并督促被诉主体纠正噪声污染行为、避免行政程序向司法程序的转移。
3.海洋噪声时空分布图的绘制及利用
海洋噪声时空分布图的绘制有赖于前期对海洋生物物种组成、分布特征及受胁状态的探明,目前南海地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已初步建立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致力于揭示齿鲸动物声呐系统相关的发声、听觉机制及噪声影响。接下来需要对重点种群的密度、分布及生境选择作出可视化报告,结合科学研究中心、监管机构与国际组织等提供的数据,首先评估制定人为噪声对重点区域海洋哺乳动物听力影响的技术指南,对急性噪声风险制定有效的管理方案,避免与海洋生物栖息地产生时空重叠。
海洋噪声时空分布图绘制的主要目的是最大化的减少人为噪声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故而需设立协调组织,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整理记录收集的环境声级基线,按照强度规划航道与科研勘探活动。既能在海域、部门及机构内部实现信息共享、监督合作,满足跨机构行动的噪声管理需求;也能实现有限资源对优先管理事项的倾斜、实现战略的科学性。在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海域生物的研究正逐步与国际接轨,国家也应在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地方政府及企业的义务、执行及监督等模块提出精细化要求,在海洋政策安排与法律制定中通过税收或利益分配等机制鼓励对海洋技术的研发。[38]海洋噪声治理仅是我国在深海战略及生物保护过程中的先期性议题,未来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都需要中国深度参与到国际立法的探讨与研究之中。
四、结语
就目前海洋保护的发展而言,尽管海洋噪声对生物的危害进一步显现,但作为一个全球性议题,仍面临专门性国际公约的缺位、区域性合作的不足以及国内立法的亟待完善。为实现海洋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及各方利益主体应围绕海洋噪声治理及生物保护开展国际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坚持全球性协定谈判与区域性制度发展并进,在协商共治的氛围下缔结具有制约、监督作用的国际规则,推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海洋噪声污染防治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上形成共识。
由于海洋噪声议题所涉主体的多元复杂以及概念的前沿性,国际立法仅能提供宏观而非实操性的建议,若仅依赖国际海洋秩序的革新,不仅无法涵盖区域内部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缔约过程还会因利益博弈而裹足不前。因而海洋噪声问题的解决更需发挥区域性海洋机制的作用。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共同探索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信息交流平台,补阙并完善海洋噪声致害的赔付制度,以跨界海洋噪声保护区的设立满足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下具有地区特性的海洋噪声污染治理方案。反观国内海洋噪声的治理,首要目标是完善海洋噪声的测绘与数据信息的梳理与整合,在治理的初期,可对重点海域、对濒危海洋生物产生突出影响的噪声问题增加控制与减缓的措施性规定,设置符合现有技术条件且不至过于严格、难以实现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