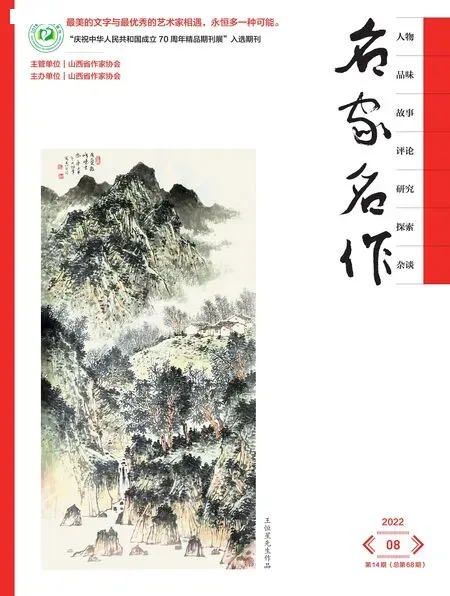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对人格修炼的启示
吴俊化
中国传统绘画有几千年的传承,纵观历史长河,巨匠辈出,名作大观,丰碑林立,画论丰富,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东方文明特征。因此,要把握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精神中的美学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精神中的美学内涵
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洋画最本质的区别集中在观念、造型、构图、意境等诸多方面,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才彰显了其深厚的美学内涵。
(一)中西方绘画差异
西方的艺术重在写实,多用直观的方式来表达情感,科学脉络贯穿其中。而中国的艺术则相反,中国的艺术注重意象表达,其根基是中国的古代哲学,更贴近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科学是两个范畴,艺术家与科学家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在艺术家的眼里看到的是情感、是感性,而在科学家的眼里则是客观理性。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中国的艺术,它们之间在最初有一点是相通的,是艺术家在用一种质朴天真的心灵去追寻潜藏在大千世界的各种美,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有差异而已。欧洲的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是两个不同的高峰,这两个高峰只能远远相望,要想融合,只有走到山谷才能见面。
(二)中国传统绘画以线塑形
中华民族对线条向来情有独钟,中国传统绘画如此,中国的雕塑、建筑亦如此,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的本质就是非常注重流动的线条。中国传统绘画把形体化为飞动的线条,着重于线条的流动,因此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带有舞蹈的意味。中国传统绘画注重线条,配合线条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毛笔、墨。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有极大的表现力,因此“笔墨”两个字不但代表绘画和书法的工具,而且代表了一种艺术境界。中国历代画家就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创立了各种用笔的方法:方笔、圆笔、中锋、侧锋、藏锋、出锋、疾锋等;创立了铁线描、柳叶描、琴弦描、橄榄描等“十八描”。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讲究节奏、疏密、浓淡、干湿等,因此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具有建筑的形式美、舞蹈的姿态美、音乐的节奏美,其核心要素不是机械写实,而在创作出一种意象,以至于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对中国画中的线条也羡慕不已,竟然用线条画起了油画。
线条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脊梁,南齐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六论法》中就有“骨法用笔”的精辟论述。线条能外取物体的骨相神态,内表画家的人格心灵,具有一种铮铮骨气之美、荡气回肠之美。
(三)笔墨美
中国传统绘画除线条美以外,还有由于宣纸、毛笔、墨的不可把握性所呈现的笔墨美。中国传统绘画有工具材料的难以把握性,但中国人知难而上,持之以恒,坚持时间长了这种难处变成了一种乐趣,最后不仅可以很顺手地运用其可把握性,而且还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不可把握性,为中国传统绘画增加了一些意外的趣味与玄妙,从而也使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拥有了神韵。宋代时期梁楷首创了泼墨大写意人物画,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代的徐渭又把大写意花鸟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至此,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创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四)构图美
西洋画三维空间的构图讲究的是科学。中国传统绘画构图讲究散点透视,更具主观性、灵活性和创意性。
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美还表现在留白上。如果说西洋画习惯于把所有的空白都涂满才算是画面的完整,那么中国传统绘画则恰恰是把“黑”与“白”作为构图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绘画有即是无、无恰是有,笔墨和线条只是造型的需要,本身也被赋予了意义。中国传统绘画灵活巧妙地运用“有”与“无”的关系,具有东方的美学色彩。

扇面《秋色无边》 吴俊化/作

《霜禽欲下先偷眼》 吴俊化/作
二、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精神彰显的意境美
诗中的情诗人通过文字表述,而画中的情要观者用眼睛和心灵去感悟。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与我国悠久的文化沉淀息息相关,是我国儒道、禅宗思想的一种视觉形态,是“情”与“景”的结晶。
(一)“道”的境界
我们都读过《庖丁解牛》名篇,庖丁解牛之娴熟,是因为胸中有全牛,掌握其筋骨要害之处,此为“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是整个人生、历史、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这种哲理性的思考去感受和提炼,去表现和创作,乃是对“道”的观照,旨趣是以畅神和精神自由为最高境界,这正是中国历代画家所追求的一种意境。
“道”的境界在山水画中表现尤为突出。北宋的全景山水;南宋的诗意般特写山水;元代以“有我之境”山水超尘脱俗;到现代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带动着中国山水向现代形态转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禅”的境界
“禅”的内涵讲的是一个“空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世上本来什么也没有,芸芸众生还争什么呢?“空性”看似无用,实为大用。正因为它看似无用,人们常常忘却了它的存在与作用。艺术与“空性”恰如人与空气,常常忘却的正是息息相关的,现代科学可以把一个物体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元素,但“空性”仍是不可知的一个奥秘。正如我们可以运用科学手段轻而易举地分析出一个苹果有多少元素构成,但若把组成苹果的所有元素都找出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并不能组成苹果。看来组成苹果除了各种元素外,应该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这“一点什么”,它无处不在,却难以捉摸。这“一点什么”便是本质,便是博大,便是玄妙。
就艺术而言,有了这“一点什么”,就是活的生命;缺少这“一点什么”,便是垃圾一堆。历代中国画家就是在苦苦寻找这“一点什么”,尤其是花鸟画家,他们不愿意在一个单层面上再现自然,而是在一个深层的境界里创构,从直观形象的描绘到活跃生命的传达,一直是最高灵境的表现。历来文人爱画梅兰竹菊,他们所传达的不是单一的形,而是一种生命,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水墨画在用毛笔接触宣纸的刹那间,就充满了禅意。因此,在历代名家作品中,我们不难感悟到他们对“禅”的追求,同时也使我们面对他们“超旷空灵”的画面为之动情。
(三)儒家境界
儒家思想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其作为入世之说,渗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尤其渗透在人物画中。正因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美术史上最先成熟的是人物画。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在唐代以前,绘画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说教。宋代以后出现了“风俗画”“历史画”,其内容大都也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有关,甚至与当时的民族斗争有一定的联系。元代人物画衰落,其原因就是由于蒙古贵族统治,一大批士大夫画家对人生抱一种冷淡的态度,因此都“疏于人事”,避开接触社会并以山水花鸟寄情达意反映社会。由此可见,人物画与历史政治背景紧密相连,特别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物画明显地流露着儒学境界。
从儒学的本质意义上讲,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画作品同样洋溢着儒雅风采,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矿工》、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方增先的《藏民图》、无不体现着儒学中人文关怀的色彩,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内涵。
三、笔墨精神的美学价值与人格品质的相互映照
绘画美总是与人格美不可分离,笔墨精神总是与人格品质紧密相连。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形式美、意境美都是由画家创构的,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精神的外在和内涵的体现。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就是客体和主体的交融,画家所表现的既是物象的品格,又是自己的渊源博见和人格力量,是一种人生感、历史感的宣泄。
(一)笔墨精神与人文修养
所谓画如其人,就包括了画家的全部生命状态,画家的笔墨精神充分地体现了画家的人格修养。石涛认为,画家在观照天地万物开展审美思维时,将体验到的天地的生机、山水的活力、花鸟鱼虫的灵气与画家自有的生命力活动有机联系起来,进而可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巧妙地融精神内涵于画面形象之中。石涛的这个美学体系,是对“天人合一”的继承,不仅适合山水画的创作,而且可以运用到人物画、花鸟画创作中。
吴昌硕以气作画,气韵灵动;黄宾虹焦墨点染,气势浑厚;潘天寿追求张力,大气磅礴等等。历代名家懂得运用传统道德人格来修身养性,十分重视对自己人格品德的锤炼,在画中通过道德人格的自我表现,对社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这是中国传统绘画最有价值的美学遗产。
(二)当今笔墨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单一形态转向多元形态。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转变,对人格的追逐也各不相同。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以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为潮流的社会环境,导致艺术作品的命运由市场来决定。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品难以被重视,从而产生不了大的影响力,致使其往通俗易懂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绘画同样也受到影响,一些画家受金钱的诱惑,把艺术作为挣钱的工具,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这与我国的旧文人相比,所缺少的乃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中国画家必须增强文化自信,树立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传统绘画中最精华的部分,锤炼自身人格修养,从而为时代创作出更多的精品。
(三)弘扬笔墨精神任重道远
越来越趋向大众化是当代中国传统绘画发展的一个特点,目前已表现出“重制作轻写意”“重表面轻内涵”的趋势,应当引起美术界的高度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提倡文化艺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文化大复兴的必然。时代呼唤精品力作,呼唤创新艺术作品。每一个艺术家都需要做出努力,应该以传承与创新笔墨精神为己任,抵制和铲除各种文化腐败,让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精神内涵缺失的现状得到改观。
中国传统绘画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我们应为拥有这份珍贵的遗产而感到自豪。这份遗产不但给专业画家提供了一个参照源,而且也是美育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