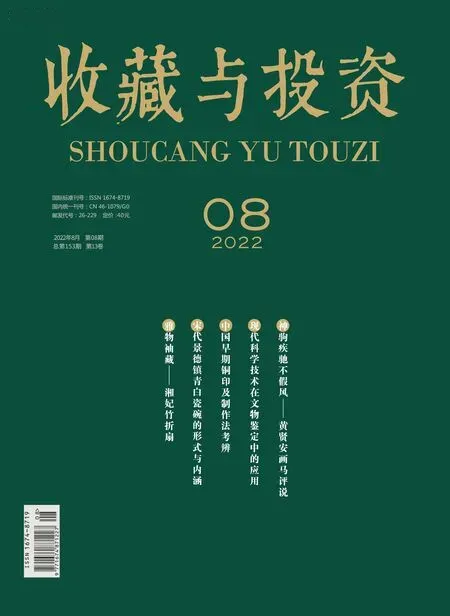“花”开瓷上:西夏牡丹纹瓷器的美学意蕴
应 琦(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疑即当地所产。”
黑城正是当时西夏所属的军事重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均发掘出了大量西夏瓷,由此揭开了西夏瓷的神秘面纱。
我国出土的西夏瓷装饰纹样种类繁多,造型多变,在西夏瓷众多植物装饰纹样中,牡丹花主题的纹样居多。西夏牡丹纹瓷器受宋代的写实主义风格影响很深,且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党项族特有的风格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使西夏牡丹纹瓷器不再只是一件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器物,而是逐渐发展为充满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
一、赏形:“圆润曲妙”的艺术造型
民族文化是民族审美观念形成的基础,而审美观念又会反作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陶瓷在整体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五大名窑代表着宋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就陶瓷造型而言,宋代陶瓷中多为实用之器,如定窑中碗、盘、杯等生活器具种类较多而瓶、壶较少。宋瓷造型整体上简洁大方,清新流畅,追求内在的美感。器物造型与时代审美一致,宋瓷造型优雅大方,线条飘逸流畅,与宋代自然、含蓄、质朴的审美观正相吻合。曾经盛产西夏瓷的灵武窑正是在宋代磁州窑系、宋代定窑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西夏瓷器的艺术风格中既能体现党项族的特色又带有中原汉文化的意味,大夏王朝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也在西夏瓷器的艺术造型中有所展现。
(一)形之“圆润”
宁夏灵武磁窑的褐釉剔花牡丹纹双耳扁壶外形圆润,高35厘米,口径9.5厘米,腹径31厘米,厚19厘米,扁壶的肩颈部和接近壶底的部分分别有一对穿耳,对称存在,腹部正反面也有一对对称的圈足,小口、斜唇。这种圈足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游牧民族在使用时卧放。造型从整体上看像一只乌龟,扁壶首尾衔接自然,线条流畅,腹部整体轮廓弧度饱满,气脉贯通,连贯和谐。党项民族生活在长期战乱的时代,在艰难的游牧生活中,往往能够从这些圆润造型的器物上得到一丝心灵的慰藉。西夏牡丹纹扁壶大多圆口、圆颈、前后扁圆腹、肩部对称圆形双耳、圆形圈足,整体均衡的器物造型在视觉上使人感到平稳圆满,进而在心理上获得安定感和稳定感,体现了西夏人民的“求全意识”,是人民对于圆满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祈愿。
(二)形之“曲妙”

图1 褐釉剔花牡丹纹双耳扁壶

图2 西夏牡丹花梅瓶
曲线作为最能表达人类情感的线型,在陶瓷造型设计中也曾广泛运用。黑釉剔刻牡丹花梅瓶是西夏瓷器中体现“弧线”美的代表性器物。梅瓶作为瓷器的一种器型,是从陶制和青铜的盛水器中获得灵感而设计出来的。明朝张谦德《瓶花谱》道:“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时尚窑器。”西夏牡丹花梅瓶整体造型极具弧线型美感,小口、束颈、宽肩、深腹修长、直圈足,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瓶口的造型似一只外翻的蘑菇,由长颈鼓腹形成曲折流畅的瓶身,给人端庄典雅之感。与中原地区所生产的梅瓶不同,西夏的梅瓶有其独特的造型装饰手法,即“蘑菇口”,在外翻的蘑菇口下沿水平方向切削,口与颈的差别较大,这也是梅瓶“仅能容一支梅花”的特色。西夏梅瓶的“曲”,展现的不仅是一种美感,更是一种美学情趣,体现出西夏人民对自然的崇敬和敬仰。
二、品美:“自然至美”的审美意蕴
西夏牡丹纹瓷器受到后世的欣赏和称赞,还因为它美在“自然”。自然美是人类以最纯粹、本真的眼光欣赏自然,从而产生的具有根源性的一种审美感受。西夏牡丹纹瓷器的自然美首先在其“形态美”,单枝或缠绕的大朵牡丹花在瓷器上肆意绽放,牡丹花瓣和花蕊隐约可见,向人们展现牡丹花的高贵典雅;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寓意美”,自古时起牡丹在人们心中就是象征着富贵、圆满的大吉之物。西夏牡丹纹瓷器上的纹饰图案是一幅和谐、美好的图景,牡丹花大朵盛开,或一枝独秀,或绕枝交缠。制瓷工匠在创作中不夹杂任何功利欲念之心,仅纯粹地再现出大自然牡丹盛开时的真实图景。这种将自身完全置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自由的创作状态,更能凸显出人对自然的喜爱,以及西夏人民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一)自然之物“形态美”
西夏瓷器上的牡丹花纹饰形状圆润饱满,勾勒牡丹花的工笔线条苍劲有力,花瓣分布具有规律的对称性。单看牡丹花花瓣,有单瓣和复瓣之分;按牡丹枝叶,又有折枝、缠枝、串枝的区别。随着窑工年复一年的加工、提炼,西夏瓷上的牡丹花图案逐渐形成了别致的造型风格:“凸”字形的花瓣顶端;“?”型的花瓣筋脉;花蕊多以圆圈表示。
折枝牡丹纹,即刻在瓷器上的图案并非整株的牡丹花,而是对部分花枝进行图案化创作,枝干形式灵活,可曲可直,是最常出现在西夏瓷器上的一种牡丹花纹饰。鄂尔多斯出土的黑褐釉剔划牡丹纹罐,就是其中的典型器物。这只大罐,罐口呈圆状趋近喇叭状,罐颈短,罐身微微鼓起,上腹部所施釉为褐釉,同下腹部露胎的部分之间形成一道明显的弧度交界线。罐身主体部分剔刻两组牡丹花纹,正上方和正下方刻两道弦纹,整个图案都在开光内剔刻装饰花纹。如单看此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一只弯曲的枝干上生出一朵娇艳欲滴的牡丹花,正面可见五瓣肥大的牡丹花花瓣,花瓣两边各有一组对称的枝叶,枝叶摇晃衬托得牡丹花纹整体比较豪迈、质朴,符合游牧民族偏粗犷的审美习惯。此外,西夏瓷上的串枝牡丹和缠枝牡丹图案也各有其独特的节奏和韵律感,使牡丹纹瓷器显现出生机勃勃的氛围,更显西夏窑工技艺娴熟。
(二)自然之物“寓意美”
牡丹纹样在西夏深得人心,与海水纹、鹿纹等象征美好寓意纹样的组合在西夏遗存中也均有发现。鹿是党项一族极为喜爱的动物,因此西夏人民常将鹿纹与牡丹纹结合,以表达对富贵、平安生活的向往之情。褐釉剔刻跃鹿牡丹纹扁壶上可见一只活力四射的小鹿,口中衔有牡丹,立姿回首,朝气蓬勃。牡丹与鹿组合的图案纹样或是受到了汉地瑞鹿识仙草的影响,在汉地鹿被视作守护仙草的神兽,除此之外,“鹿”同“禄”,当禄与福、寿结合在一起时,“福、禄、寿”便成为人们表达祝福的一种美好祝词。至宋代时,鹿已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神兽,象征吉祥。党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动荡不安、战乱频发的西北荒地,对性格温顺、其肉可食、皮能制衣、角可入药的鹿需求量一直很高,甚至体型较大的鹿还可以作为交通工具拉车载人,捕捉猎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项能够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活动。故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党项族将鹿与牡丹花组合的图案装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瓷器上,意为富贵和谐。
三、释意:“观物取象”的美学内涵
从美学的角度看,西夏牡丹纹瓷器的出现,是制作者“观物取象”的结果。通过“观物”而取万物之兆象,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思维方式,影响了艺术创作的许多方面,也对作为独特艺术的陶瓷造型有深层次影响。观物取象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时也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物”为审美过程的开端,而不是从心开始。艺术创作的原型与对象应是包罗万象的大自然和社会实象。西夏牡丹纹瓷器上所选区的牡丹花纹样,就是西夏人民“观物取象”创造的纹样,瓷器上的牡丹纹饰一般是选取牡丹花最富有特征的局部加以构形而成。牡丹纹作为西夏瓷纹样的母题,由母题又不断生发演变出新的纹饰图案。“一种对创作母题不断重复的表达兴趣,是对自然人化的不断认可,即自然物象经过人化‘自娱’处理后转成个体心象,传递出人的生命信息与情态类型”。可以说,牡丹纹样高频出现在西夏瓷器上的现象,体现了西夏人民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游牧民族对美和赏心悦目效果的追求。
其次,“观物”并非照搬“物”,绝非人们常理解的对物特征或属性进行简单的“模仿”或“复制”,观物的最终目的实际是创作者能够通过捕捉客体形象,形成观者心中之“象”。最初制作瓷器时,多采取直接观物模仿的方式,图形样式单一。后来在制瓷工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制瓷者以观成象,再设计组合使之排列成为完整、对称的图案。西夏牡丹纹瓷器在纹饰的选材上,一是富有艺术性、充满韵味的牡丹花图案,或一枝独秀,摇曳生姿,有的又两两相对,遥遥相望;二则选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案,寄托西夏人民对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之情。
四、结语

图3 黑褐釉剔划牡丹纹罐

图4 褐釉剔刻跃鹿牡丹纹扁壶
受中原瓷器影响而诞生的西夏牡丹纹瓷器,最基本的意蕴在于形式美。造型之美并非一成不变,或圆润或曲妙的造型恰恰体现出美的多变性。陶瓷非“动”物,人们通过观赏静立在一处的陶瓷就可以获得美的愉悦感,因此,牡丹纹瓷器形式美美在视觉上;意象美以自然之物牡丹之“象”寄托“富贵、吉祥”之意,存心于物,凝神于形,寓意于象,意象两者所代表的审美主体的主观情感及客观的审美意象在牡丹纹瓷器上得到了充分释放。西夏牡丹纹瓷器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类移情的产物,值得反复品味。
——以石家庄市博物馆馆藏隋代青釉扁壶为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