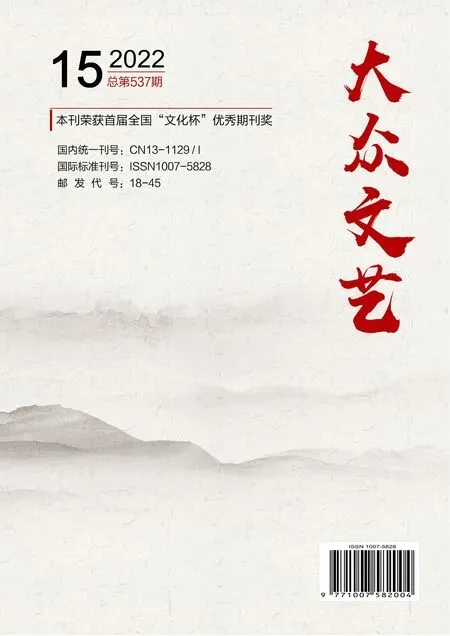浅析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
李稚茗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晚清时期,王朝糜烂、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全国各地仁人志士慷慨悲歌,掀起各类救亡图存的爱国行为。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风靡西方的“人种学说”中找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重要性,并掀起了种族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主要分两大派:一派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支持君主立宪,维护清朝统治;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国民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推翻满人统治。
1905年至1907年间,支持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鼓吹国民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别创立起了不同阵营的报刊,展开了时长两年的拉锯式民主论战。其中,《新民丛报》《中国新报》等由改良派创办的刊物是支持立宪观点的主阵地,而《民报》等由革命派创办的机关报则是支持共和观点的言论机关。
《新民丛报》是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先生在日本横滨创办的重要刊物,创刊于1902年。梁启超以该报作为主要阵地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中国新报》亦是改良派的重要言论机关报,由立宪派杨度于1907年1月20日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该报曾联合梁启超创办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的《民报》展开持续时间两年多的大论战,认为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主张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家。
《民报》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机关报,创刊于1905年11月。该报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与舆论阵地。孙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观点的广泛传播壮大了推翻清政府统治、主张民主革命的声势,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立宪派与民主派关于种族革命的主张
在这场长达两年的民主论战中,种族革命始终是双方争论的重点之一。
种族革命即民族革命,该词出自孙中山所著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清朝以少数人压制我多数汉人,故种族革命以起。”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秉持的种族革命观点便是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内容。强调以“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他认为国家需要承担保障民族安全的责任,“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仍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故曰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他认为,要保障汉民族的切身利益,就必要推翻异族的统治,建立汉民族为统治核心的政权,主张民族兴亡是一个政治国家的责任。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的前提是拥有政治国家。
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却不认可“民族主义”的观点,“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他认可清王朝对中国统治的合理性,认为满人入主中原是“易主”而非“亡国”,因为清代先祖在入主中原以前,所生活的区域亦在明朝版图内,因此他批判革命派狭义的民族主义并极大的反对三民主义,反对种族革命。
二、立宪派与民主派对种族革命有不同主张的原因
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报》报名取《大学》篇中"新民"之意。其实在创刊初期,梁启超在报中力倡民族主义,他通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激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与落后,抨击清政府屈辱卖国的卑鄙行径。
但梁启超言论与态度的大转变源于1903年。
1903年初,在美国保皇派的邀请下,梁启超对在美华人的政治状况进行系统的观察。他发现,华人尽管在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下,依旧无法融入美国的政治社会中,这让他对一般中国国民实行共和自治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梁启超表示:“华人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华人尚且‘无高尚之目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深深地刻进了民族基因里,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自己身份由听命中央的百姓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共和政体的“放纵”只会使得毫无自治能力和政治意识的人民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
因此梁启超便放弃了原本的想法,并明确声明:“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于是他在《新民丛报》中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并在其中写道:“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䣊不能为讳者也。”于是他开始在自己的主阵地《新民丛报》中,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主张,反对革命派的各项思想。立宪派想要实现封建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过渡,必定是要一定程度上“维护”清朝的统治,因此梁启超对种族革命的态度是坚决抵制的。
孙中山对种族革命的态度则是一直以来均保持一致。“种族革命”一词本就由孙中山所创,他在《社会主义的分析》里写道:“清朝以少数人压制我多数汉人,故种族革命以起。”孙中山所倡导的种族革命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思想观念。由于孙中山提倡的是革命,而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较弱,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去号召人民,因此他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在群众中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因此对于孙中山而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基于策略和情境考虑的思想利器。自清朝建立以来,“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民间从未停止过呐喊,中国传统的“贱夷狄”思想在汉族儒生心中仍根深蒂固。而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让人民苦不堪言,饱受压迫和欺凌,逐渐对清政府丧失信任与信心。且当时的人民民智未开,极易受到煽动和洗脑,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复仇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心底里的诉求,故人们对此趋之若鹜。梁启超对此思想的评价是:“(它)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
那事实上,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真的这么认可“满汉一家”吗,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又真的这么抵触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吗?其实不是的。
梁启超最初在《新民丛报》上力倡民族主义,反对清朝统治,说明他底子里还是汉族儒生的思想,以汉为尊。但后来梁启超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思路其实十分清楚,他希望用改良主义来增加国家的权力,即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并发展综合国力,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竞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对传统民族观念的突破,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基调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他还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他认为,区别汉民族和国内其他民族是小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则是团结国内各族抗击国外诸族。梁启超衡量国内形势,认为革命不适宜中国国情,且中国受到外国侵略严重,此时应各族团结合力抵御外敌而不是内斗,是以反对种族革命。
对于孙中山而言,孙中山最初提出的民族主义有着强烈的狭隘大汉主义倾向,但也是时势所迫。当时清政府正在筹备“预备立宪”,清朝贵族试图用“民主改革”的旗号来愚弄汉人,以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政治寿命和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在此情境下,孙中山急需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和知识,于是便以汉人根深蒂固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作为突破口。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憎恶满族人,虽然他自身的民族观相对较狭隘,但后期,他便将民族主义改成“五族共和”。所以对于孙中山来讲,民族主义和鼓吹种族革命只不过是他达成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因时而变,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状况。但话说回来,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孙中山所确立的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三、革命派和立宪派针对种族革命进行民主论战对后世的影响
1905年至1907年这场长达两年的民主论战无疑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从后世的结果来看,革命派无疑是胜利的一方,他们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成功实现了“反满”革命的胜利。
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为何会输?其实在最开始,呼吁君主立宪制的声音是很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都对未来报以极大的憧憬和希望,毕竟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若是中国能仿照明治维新,实现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的话,对中国的发展亦是极其有益的,但庚子国难之后,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团体在清末新政改革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皇族内阁的建立,证实了革命派的远见,也彻底摧毁了汉人精英的忠诚。
在此次新政改革中,以慈禧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希望借由立宪安抚民意,打击孙中山,延续清朝的统治,满洲亲贵将这场改革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出核心集团的机会,而汉人士绅则是想着通过立宪扩大汉人在议会和内阁中的比例,加大他们的话语权。表面上,满人汉人都希望立宪,但他们的诉求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满人把立宪当作反汉的工具,汉人则把立宪当作摆脱满人专政的机会。最终,高品级的汉族官员被边缘化,满洲亲贵被大量提拔,还建立起了一个以满族人为主,满族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皇族内阁。这种蛮横愈发使汉人意识到所谓立宪只是满人的立宪,获得权力的也仅是满洲亲贵,汉人依然被放逐在权力体系之外。这种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立宪改革,逼迫最后对清朝抱有希望的维新派产生了反意。
维新派产生了反意,便注定了立宪派落败的结局。孙中山鼓吹的种族革命为什么会胜利?因为他抓住了当时汉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愤怒的汉族士绅便群起响应。清朝的灭亡,实际上彰显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困境。
种族革命的民主论战也影响了后世对于清朝国家性质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初,海内外对于清朝国家性质的分析或多或少的带有政治色彩,并会有意无意地将“清朝”和“中国”割裂开来,萧一山的《清史大纲》将推翻清朝统治称为推翻异民族的统治,认为是“民族革命”的第一时期。即使到钱穆将其1952年演讲集结而成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仍将清朝与元朝一起称为“异族政权”。但这种充满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看法却容易被外国分裂势力所利用。比如日本以“满蒙征服论”为代表的观点,为未来日本侵华进行掩饰,为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做思想铺垫。
中国学界很快发现了外国学者带有政治目的“学术侵略”,也开始了反击。譬如曾在古史辨运动中提出疑古纲领,其中包括对 “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的顾颉刚先生也转变了立场。在此之前,他对“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们心中的“向来统一”只是因为用秦汉以后的眼光去定义秦汉以前的疆土而穿绳的历史谬论。但此时,他将自己的论点由原来的中国并非一统,变成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合法性。
在这一大背景下,就连一直强调学术独立的傅斯年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1935年12月15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局部侵华的背景下,傅斯年以团结中华各族为目的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他在文中强调,自从春秋战国,中国各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使得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历史学家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清初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科学探讨,基本确定了清朝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共性,稳定了抗日战争前后的民族思想论战,也为以后国内对清朝的基本认识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清史”由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兴起,这是一种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学术思潮,在国际与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并在2015年上半年集中爆发。跟以往的研究清史的学派相比,“新清史”的学者们反对“汉族中心论”,坚持区分清朝与从前汉族所统治的王朝,更加强调满族因素在清朝统治中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清朝的政治自成一种特殊的风格和统治模式,并表示满洲人入关后虽有一定程度的汉化,但自始至终并未失去自身的族群认同,以至于满汉分殊的现象持续存在至清末,而满汉分殊的存在也恰好可以解释十九与二十世纪“反满”言论的成因。
虽然新清史的核心还是在于满汉争议,但此时的我们,对清朝的认识已经从偏激的民族主义回归到史学研究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