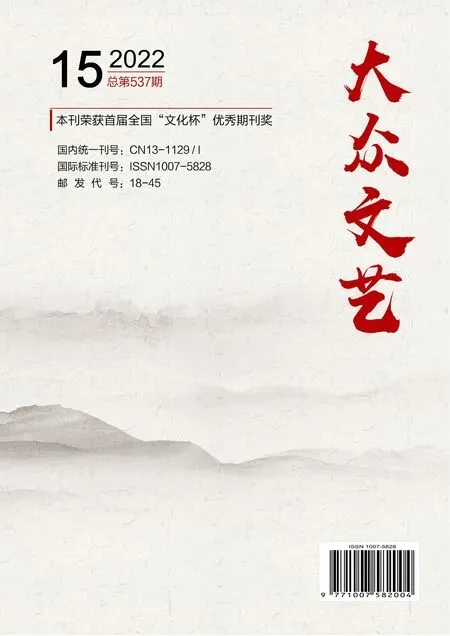向内的表演:论洛夫诗歌中的戏剧表演性
夏 沁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洛夫的诗歌中存在声音与听觉等组构形成的戏剧表演意味,这种表演不是处于表象的外在特征,而是一种内向性的“自我”表演:现代诗歌呈现给人的只是文字,其“表演性”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的。尽管不是显性的,但是它同样会给读者预留出一个表演的空间,带给读者视觉与听觉上的审美感受。因为这种“诗歌表演”与读者的主观性有很大关联,所以较之于戏剧艺术直观的外向型表演,现代诗歌所体现出的表演性更具有延展性。形象与抽象的聚合,想象与现实的统一,增强了洛夫诗歌的审美体验。
一、戏剧表演性的听觉呈现
洛夫的诗歌中描绘声音的内容很多。“啄木鸟 空空/回声 洞洞”、“伸手抓起/竟是一把鸟声”,这是自然之声;“枪声/吐出芥末的味道”、“昨夜/船上的酒嗝/居然合折押韵/有点咀嚼唐诗的味道”、“妻对着一棵松树/号啕大哭”,这是人为之声;“‘千年后我瘦成一声凄厉的呼唤时/你将在何处?’/我仍在山中”,这是人物进行对话的声音。诗人将声音代入诗作,这些负载在文字上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诗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诗歌中,声音描写出现的位置各不相同,它们的作用也有差别。其中一类常常出现于诗歌的开头或结尾处,一首诗歌就如同一幕舞台剧,它的开头和结尾分别暗含着幕起与幕落的过程。于诗歌的结尾,“演员”“道具”全部退场,只剩下黑暗中的一两声回响。声音不像视觉化的事物只能是非有即无,它有延长时间的功效,给沉浸在诗歌中读者提供了逐步“退出”诗歌的时间。在不显戛然与突兀的情况下,也给了读者体会诗歌余韵的机会。如《死亡的修辞学》:“枪声/吐出芥末的味道/我的头壳炸裂在树中/即结成石榴……”《闲情》:“檐下嘀嗒之声/我完全听不懂这三月的/难言之隐”首句就将声音——“枪声”“檐下嘀嗒之声”呈现出来。
洛夫的《致时间》以“滴嗒”开头,且将“滴嗒”声独立为一行。排列在声音前面的省略号表示这个声音自之前就已经在响着了;而分行的存在又使这一声音得以延长,它在下一个分句之前,给读者留下了一段空白。截至此处,“演员”“道具”都还未登场,作为观众的读者所能听到的只是“滴嗒”……在视觉缺席的时间里,听觉作为高度活跃的主角,在感知声音的同时,也在调动着读者的想象。继续读下去,倘若诗歌的内容与预估相似,那么读者由听觉感受所激发的“前理解”就会随着诗歌的进展而延宕开去,进而加深对诗歌语意和氛围的感受;倘若内容与预估不同,那么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诗歌所呈现出内容就会不断地对读者的前理解加以修正。这种互动式的阅读体验,同样可以加强读者与诗歌之间的张力。法国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认为,戏剧写作应该追求一种“声音戏剧”的效果,淡化演员的“表演”用舞台上的背景音乐、演员的对话让戏剧发展,恢复读者的自由。诗歌以声音描写开头,就是将“重要的位置”交给作为观众的读者。开头声音的模糊性和神秘性能够极大地调动读者的联想与想象,让读者先在脑海中演绎出一则“先导剧”,通过对声音的感知构建出心中的诗歌。
对话是诗歌中出现的另一种声音。洛夫的《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共两段,第二段以对话的形式呈现。除了“我”与蟋蟀的一说一答外,再无其他文本。而在戏剧表演中,对话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手段。剧作家杜拉斯就十分推崇对话式的写作,她试图淡化表演的其他内容,着重突出对话,用对话推动情节的发展,其戏剧作品《萨瓦纳湾》,不交代幕起幕落、不对场景布置做冗长的陈述、不引入过多人物、对人物动作的交代也少之又少。作者将全剧唯一的焦点集中在对话上,用含混且具有跳跃性的对话连缀出“爱与死亡”的主题。《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和《萨瓦纳湾》异曲同工,它展现出与戏剧表演类似的对话手法。诗歌第一段就如同戏剧剧本开头的舞台说明,交代了背景与事件:于秋夜的衡阳宾馆与一只蟋蟀相识。而后,“演出”开始。“我”与“蟋蟀”展开一系列对话,表现出一位游子的苍茫伶仃之感。将人与蟋蟀的对话作为全诗的重心,不夹杂多余的矫饰,更见精炼与新奇。并且,对话是最能显示说话者情感的表达方式。诗人在由他构建而成舞台上为读者进行表演,他的情感倾向直接转化为诗歌对话体文本的标点,并为读者所接收。感叹号、问号、破折号,在略带诙谐戏谑的氛围中,表达出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与苦涩的无奈感。由此,诗歌要传递的故事与情感不再是被诗人“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诗歌中跳跃性的对话语言,被人物“说”出来的。读者也不再是通过视觉来消化诗歌文本,而是通过捕捉诗歌中的对话,靠自己的听觉想象来编织出诗人想要通过对话传达给观众的内容。经过听觉想象的加工,读者作为舞台下的观众,等同于亲耳听到了正在进行的对话,他们成了对话的倾听者与见证者。如此,便拉近了读者与文本及诗人间的距离。
二、戏剧表演性的视觉呈现
在诗歌的主体部分,用视觉化方式呈现的意象与色彩仍占据大量比重。以洛夫《白色墓园》为例,纸面就是诗人的舞台,他在纸张上填上色彩、摆上意象,安排“戏剧”上演。诗人在后记中写道:“抵达墓园时,只见漫山遍植十字架,泛眼一片白色,印象极为深刻,故本诗乃采用此特殊形式,以表达当时的强烈感受。”这是一篇视觉效果极强的诗歌,诗人将所见所感全都化为诗句中视觉化的意象与色彩,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色墓园》的视觉呈现可分为两层:一是纸面上的视觉;二是想象中的视觉。纸面上的视觉,它最先闯入读者的眼帘,形成读者对诗歌的第一印象,诗人对诗歌文字加以排列、布局,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在进一步的阅读中,读者开始对诗歌的内容形成自己的理解,他们捕捉到诗歌中存在的意象与色彩,形成想象中的舞台。同时,最初对诗歌形式的感受又会影响到诗歌的整体意境,进而影响到读者“想象舞台”的建构。
诗歌将白色孤立为一列,又将主体内容作为另一列置于纸面的右边。用洛夫的话说,即:“两节上下(白的)二字的安排,不仅具有绘画性,同时也是语法,与诗本身为一体,可与上下诗行连读。”这样巧妙的布局安排,将纸面分为两个部分,给读者带来一种几何化的阅读感受。这样的诗作,不仅需要被“读”,更需要被“看”。读者需要在阅读的同时,体会诗歌呈现出的视觉艺术。此诗一连运用四十个“白的”,白色在反复的过程中不断被强调。它先入为主,成为读者想象中舞台布景的主色调。而后,一个接一个的意象出现在右边的诗行中,对布景进行填充:石灰质的脸、野雀、墓碑、墓草、十字架以及枯萎的玫瑰。至此,在白的底色上,象征苍凉与死寂的景象一一就位,一个充斥着苍白与肃穆氛围的舞台被搭建起来,为诗人进一步抒发对“战争与死亡之体悟”及“内心活动的知性探索”提供活动空间。
同时,“白的”二字与右侧诗行间存在大量的空格,诗人故意增加左右诗行间的距离,在纸面上形成一块巨大的留白。戏剧家布鲁克提出“空荡舞台”的概念,《白色墓园》中的留白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空荡的舞台”。诗人无法在诗稿上写实地绘制出墓园的样貌,于是就采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将自己对墓园的印象转换为可以为读者所接受的视觉体验,在纸面上留下大片空白,模拟出墓园的广阔与荒芜感;空白的存在,也更显左侧“白的”二字之孤独,由此渲染出更加强烈的孤寂感。诗人通过巧妙的布局,将诗歌的中心舞台留给读者,让他们在接受诗人为他们安排的视觉化意象的同时,在处于诗歌中心的舞台上发挥想象,敷演出他们心中的诗歌故事。
洛夫虽推崇纯诗创作,但也不忽视戏剧手法之于诗歌的意义:“诗中如果借用戏剧手法,或许更可以增强艺术的张力,而不致因过于依赖叙事,而使整首诗在结构上松垮掉。”纯诗更加关注的是透过诗歌的表象以达到的对世界与人生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分析与认识,所以走向纯诗创作的诗歌实践决定了洛夫诗歌中的“叙述性”不能只停留在纯粹的以类似流水账一样的方式去描述一个故事。叙述性较强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当为一种戏剧性,而非叙述。戏剧性的诗歌表演试图抓住诗歌中最关键、最有张力的特征,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指涉某种事件或情感;而不是以冗长意象和事件堆砌的方式还原事件的样貌。戏剧性的诗歌表演的目的不是让读者了解诗歌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以一种最有力度的方式,让人一下子摄住诗人想要传达的形而上的精神意味。同时,有的诗歌会出现过分追求“知性”的现象,它们大多比较抽象,诗歌中不会出现过多故事情节,抑或诗歌中的事件是零散、隐晦、跳跃的。如此,便很难引起读者对诗歌故事性的认知与对诗歌含义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戏剧感受”的凸显就变得更为重要,而诗歌中的戏剧符号恰好可以为读者提供把握诗歌意境与内涵的媒介。其《长恨歌》一改古诗洋洋洒洒的叙述模式,而是把握住核心意象形成戏剧化的视觉冲突。水、传递出热烈死亡气息的玫瑰与没有脸孔的女子,诗人将爱情、欲望与战争杂糅到一起道出爱、恨、悲哀与绝望。把握诗人想要通过视觉体验传递的内容,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其中蕴含的形而上的哲思时。诗人采用这类夸张、荒诞、符号感极强的意象,能够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淡化叙事,强调视觉上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的体现,增加诗歌的张力。
由图1可以看出,当沙门氏菌纯培养物浓度为5.6×105CFU/mL~5.6×101CFU/mL时,荧光曲线出现明显的扩增峰,仪器自动判定为阳性;当浓度为5.6×100CFU/mL时,荧光曲线平缓,未出现扩增峰,判定为阴性。因此,研究所建立RF-LAMP检测沙门氏菌的灵敏度为56 CFU/mL。
三、其他戏剧表演手法的运用
洛夫诗歌的戏剧表演性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在诗歌中还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它们或被置于开头当作题记、或被置于结尾称之后记,有的出现在诗歌内容的主体部分,并用括号标出。这些看似独立于诗歌之外的语言,扮演着与戏剧表演中“画外音”同样的角色。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画外音包括旁白、解说、独白等形式,它们是来自舞台画面以外的另一种声音。洛夫诗歌中的“画外语言”,同样具有独立性,它们不再从属于诗歌内容,而是处于与主体文本平行的空间,对主体文本进行补充与解释。它们可以是声音、是意象,是叙述或是议论。诗歌“画外音”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演空间,仿佛存在第二位作者,从另一种视角对诗歌进行创作与解读,多重声音的存在使诗歌变得更加立体化。
除画外音,洛夫诗歌还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其诗歌具有强烈的“镜头感”。以《与杜甫的影子同行》(节录杜甫草堂)为例,该诗将“我”行走于杜甫草堂与杜甫的生平事迹交叉编织在一起。事件与事件的衔接,历史与现实的贯通,洛夫采用了蒙太奇式的组接手法,在这里,时空的界限不再明朗,诗人将一个个场景并列、重叠、交融成为一首亦虚亦实的诗歌。此诗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于对历史画面的想象,第二部分则更加侧重现实世界诗人的感发。在一、二两部分中间,诗人插入了一段镜头感十足的转场:
淡出:鼠灰色的岁月
淡入:前年后的草堂
特写:微雨
我在仰读
一部倾斜的历史
此刻的诗人仿佛已经从诗歌创作中跳了出来,他拥有了另一重身份——导演。在进行诗歌的叙述、议论、抒情的同时,他同样关注读者的视觉接受效果,用一组镜头将杜甫古事与“我”的现实巧妙地衔接起来。淡入、淡出、特写,特效镜头的使用,模拟出岁月变迁下时间的纵深。诗人不再是简单的诗歌叙述者,他是生活的捕捉者,他将诗歌内容当作是正在上演的剧目,拍摄下一幕一幕的场景,进行诗化的加工,使之呈现在纸上。《与杜甫的影子同行》一诗的特写中,强调了读史之人是“我”。于是,“我”既是表演的安排者,又成了正在进行演出的表演者。如此,诗人与诗歌间的距离变得更为微妙:他既在诗内,又在诗外。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使诗歌更具张力。
小结
诚然,诗歌有其自身的体制要求,诗歌描写不能是纯粹的叙述,现代诗歌与戏剧表演之间的界限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明晰;但是,这些并不会妨碍现代诗歌沿袭或是借用戏剧表演中的某些艺术元素。有关声音的听觉想象、视觉舞台的搭建,以及其他戏剧表演手法为诗歌所吸收,并内化成为诗歌的创作机制。跨体裁视野下艺术手法的借鉴与交融,能够将常见的诗歌题材内容陌生化,更见新颖与别致,在增强诗歌艺术表达效果的同时,也拓展了诗歌的艺术承载空间。
①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4.
②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5.
③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6.
④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69.
⑤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98.
⑥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9.
⑦洛夫.世纪诗丛 因为风的缘故[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63.
⑧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76.
⑨[德]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
⑩[法]阿拉泽,[法]布洛-拉巴雷尔.解读杜拉斯[M].作家出版社,2017:218.
(11)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22.(12)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23.
(13)[英]布鲁克(Brook,P.).空的空间[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57.
(14)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168-169.
(15)洛夫.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200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