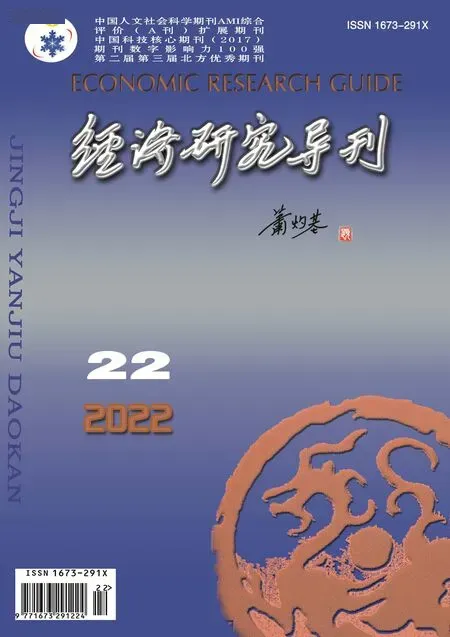《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潘雯雯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14 条对纵向垄断协议作出了规定,使其与第13 条的横向垄断协议相对应,这样设置有其特定的背景及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规范类型失调和缺漏等问题。实践中,很多案件在纵向垄断协议法律的适用上存在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立法层面和司法操作两方面的原因,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还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比如“锐邦诉强生案”,其本质上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但最终二审法院却以垄断协议案件处理结案。虽然法院用了大量论据来论证强生公司的行为限制、排除了竞争。但其在《反垄断法》第14 条的解释问题上出现了问题。而在“上海日进电气诉松下电器垄断案”中,原告坚持按照横向协议主张权利,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反垄断法》第13 条的规定。这个案件中法院似乎忽略了纵向垄断协议可能被用于协助横向共谋的考察,某些纵向垄断协议仅仅是掩盖横向共谋的幌子,即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这两个案件中存在的争议除了法院在适用法律中存在问题外,对于纵向垄断协议法律条文的设置似乎也存在着问题。如果法律条文设置不够明确,也容易造成法律条文的架空,使案件的审理陷入困境。
对此,应当反思:纵向垄断协议何时应按照垄断协议案件处理?何时应按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理?何时应作为真正的纵向垄断协议案件处理?我国《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的相关条款是否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在该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有进一步统一认识的必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对《反垄断法》第14 条进行明晰,重新构建纵向垄断协议条款的规定,以完善纵向垄断协议制度。
二、《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法条评析
(一)纵向垄断协议的典型案例分析
1.锐邦诉强生案。该案被认为是国内首例关于限制转售价格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案件,因此具有典型意义。其基本案情如下:被告强生公司是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的公司,并在相关市场中具有一定地位。原告锐邦公司是被告在北京的经销商,被告强生公司向锐邦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和售后支持。强生公司于2008 年1 月和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合同中约定了锐邦公司特定销售区域和最低销售价格。同年7 月,被告以原告未经其许可擅自降低销售价格为由,取消了原告在特定地区销售相关产品的资格并停止了供货。2009 年,锐邦公司以被告在经销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为由,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经销合同》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不能判定被告构成垄断行为,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通过大量论据分析得出,强生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医用缝线产品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地位,《经销合同》规定了最低转售价格,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且并没有明显的促进市场竞争效果,从而构成纵向垄断协议。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原告锐邦公司胜诉。本案中,虽然二审法院认定强生公司的纵向协议构成垄断行为时,对其在相关市场认定、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壁垒等做了专门分析,但最终认定了强生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该纵向垄断协议是滥用了其支配地位的行为,这或许是因为立法缺失而造成的法条适用困境。
2.日进电气诉松下电器垄断案。原告日进公司与被告青英公司、铭达公司均是被告松下电器公司工厂旗下产品指定经销商。松下电器公司在上海制定发布了《松下FA 华东最终用户一体化管理章程》。该章程规定,经销商不得向其他经销商的客户销售产品,即划定了客户保护圈,若违反,松下电器公司将对经销商采取停止特价等惩罚措施。青英公司、铭达公司均在松下电器公司的组织下根据该章程协同实施了客户保护圈制度,导致原告丧失大量商业交易机会。2013 年6 月,松下电器公司认定原告违反章程,对其进行了惩罚。日进公司以松下、青英、铭达三公司达成的协议分割了销售市场,限制了市场竞争为由诉至法院,依据是《反垄断法》第13 条。法院向原告释明被告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第13 条,但具备第14 条纵向垄断协议条款的可能性,但是原告仍然坚持按第13 条主张权利。最终法院以被告行为不属于横向协议,原告主张不成立为由驳回诉讼请求。
本案中,法院似乎忽略了纵向协议对于横向协议共谋的帮助作用。因为纵向垄断协议案件相关的主体与行为人,并不总是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中,纵向垄断协议不仅可能限制交易相对人的定价自由和决策机会,还可能帮助供应商或销售商达成共谋。换句话说,有些纵向协议是掩盖横向共谋的幌子。在这种情况下,纵向垄断协议与横向垄断协议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二)纵向垄断协议法条的适用困境
1.纵向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竞合。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但严格来说,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形式或手段。垄断协议的本质是,如果单一企业不具备“提价能力”,则由多个企业通过签订协议方式联合起来获得“提价能力”。也就是说,垄断协议所涉及的经营者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实施垄断行为。因此,垄断协议可以说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另一种形式,最终演变成不正当的提价行为,区别仅在于行为主体的数量上。如上文中的“锐邦诉强生案”中,虽然法院最终判定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判令被告败诉,但是仔细分析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强生公司其实是利用了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对下游企业进行价格控制。强生公司有极大的品牌影响力,对其经销商也有很强的控制力。同时,强生公司拥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渠道网络,能够有效地整合和控制渠道资源。因此,强生公司的缝线产品价格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维持15 年基本不变。可以说强生公司具有的市场定价能力与其自身的市场地位密不可分。无独有偶,早在1989 年的“HB 冰淇淋公司案”中,HB 公司也是与下游零售商达成并实施纵向限制的“冰柜协议”内容最终败诉。但HB 公司在其相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冰柜协议”只是其手段,其行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了市场竞争。从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来看,一切垄断行为都是可能导致价格上涨的行为,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导致价格上涨的效果更为直接,而垄断协议比较间接。
2.纵向垄断协议与横向垄断协议竞合。《反垄断法》在垄断协议的划分上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法经验,按照经营者所处的经济层次或环节的不同,以横向和纵向的方式来对垄断协议进行分类,这样划分能够缓解《反垄断法》粗线条、抽象性的特点。总体上横向协议比纵向协议更具有竞争危害性,正确区分这两类协议对判断竞争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相互交织,这样的划分容易导致框架效应和思维定式,且无法覆盖所有垄断协议类型,如轴辐协议等。这样一来,无法对企业行为准确全面的定性,甚至可能使有关主体逃逸《反垄断法》的制裁。
在上文提到的“日进案”中,法院认为横向垄断协议不会存在于同一品牌的经销商之间。
但通过经济分析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同一品牌的经销商之间达成的协议,也可能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日进案”中涉及的纵向协议事实上对于横向共谋地起到了帮助作用,即掩盖横向共谋。但目前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对帮助型的垄断行为做出规定,因此法院最后以相关企业未构成横向垄断协议为由驳回原告请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这的确值得反思。
虽然《反垄断法》第13 条中规定了几种典型的横向垄断协议,但是并没有穷尽其类型,横向垄断协议的参与者有时候可能会通过划分市场、固定价格等纵向限制措施,联合起来对下游客户或上游供应商进行大“客户封锁”和“原料封锁”,以此来抑制外部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以纵向协议作为联结方式来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这就是“轴辐协议”的其中一种类型,生产商与多个经销商与达成三角关系的共谋,也需要《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因此,就有必要诉诸《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则。但目前,我国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性、市场划分不清等问题。在《反垄断法》修改的大背景下,对纵向垄断协议做出修改和调整具有现实意义。
三、《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法条重构设想
在《反垄断法》的修订过程中,应该重视垄断协议规范类型失调的问题。在不彻底推翻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定分类及其规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改良性的方案。就纵向垄断协议来说,应该按照其在垄断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来定性,而不是一律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一)以纵向协议的形式来帮助、促成、掩盖横向共谋的,按照横向垄断协议来定性
具有横向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若通过签订纵向垄断协议的形式,来控制相对交易人与其他经营者达到共同限制、排除竞争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横向垄断协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反垄断法》第13条以横向垄断协议进行定性。但要注意,如果具有横向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并无限制、排除竞争的目的,那么此时的纵向协议不该被认定为垄断行为,而是被允许的竞争性营销行为,因为此时的市场具有竞争性。对于轴辐协议来说,虽然其同时涉及横向协议与纵向协议,但从竞争效果出发,按照横向协议来处理更为合适,相应地,在适用原则上应采取本身违法的原则。在法律规定上可以体现为,将《反垄断法》第13 条中的“联合抵制交易”修改为“以联合拒绝交易、划分市场、搭售捆绑、固定价格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这样以纵向协议为手段来达成横向垄断目的的行为,就可以划分到横向协议中来规制。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其支配地位实施纵向垄断协议,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来定性
如果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市场地位并利用其支配地位实施了纵向垄断协议,以达到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目的。那么从本质上讲,这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纵向垄断协议同样是一种手段而已。与单纯的垄断协议相比,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更容易控制价格使其上涨,其对竞争的损害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应该按照《反垄断法》第17 条规制。在法条上可以体现为,在《反垄断法》第17 条中增加一款,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纵向垄断协议来实施的规定。
(三)对《反垄断法》第14 条进行细化
若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签订的纵向协议不属于上文(一)、(二)类情况,但有充分证据证明该纵向协议具有限制、排除竞争的实质效果,就以《反垄断法》的第14 条条款来规制。但是在法律规定中,应该体现出排除与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竞合的情形。除此之外,在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定中,可以增加“限定商品转售的地域或者对象”这一子项,与“转售价格维持,适用相同的逻辑和规则,以此减少第14 条第三项中“其他垄断协议”的模糊性。
总之,利用纵向协议进行其他垄断行为的,可以将其定性为横向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其他纵向垄断协议归到《反垄断法》第14 条,再将第14条进行细化,增加“限定商品转售的地域或者对象”子项,这样可以使得《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条款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