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辐射带动影响研究
◎阮荣平 姜瑞雪 曹娟娟
一、引言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1结果,到2016年底,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98.1%,小农户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超过70%,小农户三大谷物种植面积占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的80%。在土地细碎化格局与小农经营基础上,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韩俊,2018)。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重庆、张慧鹏,2019)。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定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注重其自身发展,二是注重其社会带动作用。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更是把“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定为中国加快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普通小农户发展,与小农户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新型发展模式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现有文献关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研究中,部分是从对立或独立的角度去讨论农业生产和发展问题(赵晓峰、赵祥云,2018)。如大多数由村庄精英领办的合作社,相对于小农户来说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或是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等资源禀赋优势,在与外来企业合作时会挤压小农户的获利空间(温铁军,2009)。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地流转的速度,加剧了小规模经营主体的分化,压缩了小农户的发展空间。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包括了农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农资供应等一系列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活动(廖西元等,2011;蔡荣、蔡书凯,2014)。比较多的学者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来影响小农户的收入、要素投入、销量等(闫玉科,2006;曹子坚、张鹏,2009)。也有研究认为农地经营权产权细分以及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因为社会分工而形成规模经济。并且,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发展,可以带动小农的现代化经营且能够逐渐满足小农的利益追求(罗必良,2015)。当从农民、农村、农业三个方面综合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状况和影响因素时,阮荣平等(2017)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农户带动、金融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带动作用。这表明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小农户可能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条路径。
然而,具体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不同层面的经营行为影响是否一致?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又是否具有异质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怎样的机制来辐射影响小农户?现有研究尚未对上述问题给出充分回答,本文拟细致分析这些问题,以期对现有研究贡献一些新的认识,同时也希望为进一步制订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及它们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既定的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等)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和纽带,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Wellman B&Berknowitz S D,1988)。社会网络既会连接起没有纽带关系的行动者,也会将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的关系网络(Christakis N A&Fowler J H,2007)。社会网络理论经常被广泛地应用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产业集群并非是大量企业的简单聚集,而是企业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网络,其具有某种社会网络的属性(Nunzia C,2004)。以Coleman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意识到网络中既存的社会资本价值,会不断复制网络中已经存在的社会资本,即影响社会关系网络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是复制网络中已存在的社会资本。而以Burr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则认为,当产业集群的网络中存在结构洞时,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便具有了结构优势,其他企业只有通过它与其他个体或组织建立联系(Freeman C,1991)。
县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为产业集聚。这种集聚,可能使得农户可以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接触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利益联结机制可视为小农户接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网络的一种途径。利益联结机制中,主要有契约合同、订单合同等方式。毛慧等(2019)指出契约农业是小农户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契约农业的参与对小农户的投入具有显著影响。李克、周静(2011)在研究龙头企业形成农户带动关系的成因时,指出利益联结机制越强时,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越强。詹柴等(2020)在调研了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的实际成效问题之后,提出了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建议。所以,小农户可能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本来接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一定的资源,比如通过认识某些关键人物或者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成社会契约,形成某种利益联结机制,从而获得更多的保障,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辐射影响到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社会网络,还可能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理论的产生源自于外部性理论,是指当组织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不仅仅会产生组织内的预期成果,也会对组织之外产生一定的影响(Douglas Holtz-Eakin&Amy E S,1996)。溢出效应可以分为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应等(Zoltan J A et al.,1999)。罗默在生产函数中将知识视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建立了以知识溢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Olga Alonso-Villar, 2002)。卢卡斯构造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向他人学习或者相互之间的学习都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溢出。当一个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时,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更多有利影响,从而能够显著提高周围人的劳动生产率(Guifang Yang et al., 2001)。Magnus B M&Ari Kokko(1998)指出技术溢出效应会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James P L et al.(2007)指出了不同国家间存在经济依赖的现象并将其概括为国家之间的临近溢出效应。Philippe M et al.(2001)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地区间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外溢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县级集聚时,它的发展会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也就是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不但会影响其自身的组织演进,也会通过知识、人力资本、技术等溢出对其周围组织或者经营主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形势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范围已经不只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包括农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农资供应等一系列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龚道广(2000)指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罗必良(2015)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发展可以带动小农的现代化经营且能够逐渐满足小农的利益追求。故而,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会将知识、人力资本、技术等溢出到周围小农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会通过社会网络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并可能通过社会化服务的溢出效应等机制对小农户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本文关注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经营层面的辐射带动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于传统小农户而言,具有较高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程度以及规模经济效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技术采纳以及标准化生产等方面的水平都比普通小农户要高(纪永茂、陈永贵,2007;黄祖辉、俞宁,2010;陈永富等,2014)。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越高,小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越高。
要素投入层面,一般而言,相对于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有可能采取绿色生产方式,化肥农药的施用水平会相对较低;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较于小农户也可能成为新技术或新生产方式的采纳者。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社会网络或者溢出效应对小农户产生影响的话,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将会有利于小农户绿色生产方式以及新技术的采纳。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程度越高,小农户应用绿色生产方式和采纳新技术的概率就越大。
由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功能,所以他们对小农户生产方面的辐射带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其最为直接的功能是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龙头企业则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产业链中主要负责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以及为农户提供生产性服务(张照新、赵海,2013)。可以看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功能定位主要在于为小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以及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等。而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的主体,承担着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功能,发挥着小规模农户的示范作用,并负责带动小农户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等投入要素,提高集约化水平。所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可能都对小农户的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在辐射带动程度上可能会因为功能定位的不同而不同。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以及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16年、2019年“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同时辅之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部分省统计年鉴3。其中,“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是由经济日报社负责组织、中国人民大学负责设计的针对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小农户的全国性调查项目。该项目专门开发了相应的APP软件,同时运用GPS定位、录音和拍照等技术手段以保证数据质量。
(二)变量选择
本文将核心自变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定义为县级区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密度,密度越大表明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程度越高。由于县域总农地数据难以获得,采用县域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分母,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作为分子,除数为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密度。由于县级宏观经济状况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在计算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密度时具体使用2016年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作为分子。各个主体(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县级分布数量数据与该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作为分主体的县级发展程度。文中所使用的县级层面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数据来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数调查项目,是所涉及到的36个县截至2016年末所拥有的所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个数。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县级地区宏观变量。参考以往研究(冯晓龙等,2018),本文设置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外出比例、家庭生产规模、家庭固定资产原值,以及是否有家庭成员为村干部等。县级地区宏观变量主要包括了县域基本情况(地区生产总值、公共财政支出等)、农业发展情况(农业增加值、设施农业占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等。此外,内生性和影响机制部分分别涉及“是否举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和“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两个解释变量。本文所涉及的变量特征及相关说明参见表1。
(三)计量模型
首先,本文将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单项经营行为的影响,为此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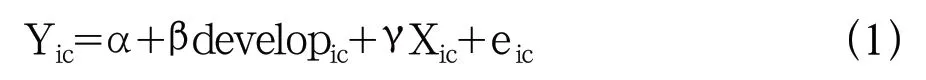
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i指的是在c县农户i家庭人均收入、要素投入(化肥)、新技术采纳(新品种采纳、生产信息技术采纳)以及标准化生产。模型中的developic表示不同农户所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发展程度,系数 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参数,表示县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的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Xic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县级地区宏观变量。
其次,本文将进一步研究不同主体(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辐射带动影响。借鉴阮荣平等(2017)建立综合带动指数的方法,本文针对小农户的经营行为建立了两个综合发展指数F1,F2。基本思路是:根据公式Yij*=将小农户经营行为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各个被解释变量指标值相加得到小农户经营行为的综合发展指数。其中Yij*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第i个农户的第j个指标值,YJ表示所有样本第j个指标的均值,var(Yj)表示所有样本第j个指标的方差。F1代表小农户的产量、收入、新品种采纳、生产信息技术采纳、标准化生产和三品一标标准化处理值之和;F2代表小农户的要素投入即化肥、农药、劳动力投入标准化处理值之和。

表1 实证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单项经营行为回归结果
为考察不同主体对小农户综合经营行为的辐射带动影响,本文的设定回归模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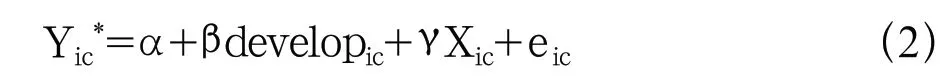
模型中,Yic*的含义为小农户综合发展指标F1、F2。模型中的develop分别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龙头企业发展程度、合作社发展程度、家庭农场发展程度和专业大户发展程度。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1)。
四、实证结果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单项经营行为影响
1.家庭收入。表2第(1)列给出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县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密度对小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此结果为研究假说1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表3 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综合经营行为回归结果
2.要素投入。表2第(2)~(4)列分别给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小麦、稻谷、玉米的化肥投入影响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分别在1%、5%、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小麦、稻谷、玉米的化肥投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越高的县域,小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每亩使用的化肥量越少。
3.技术采纳。表2第(5)~(7)列分别给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新品种采纳、生产信息技术采纳以及标准化生产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新品种采纳、生产信息技术采纳和标准化生产方式采纳都在5%~10%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越大,则小农户采纳这三种新技术的概率就越高。
总体而言,表2第(2)~(7)列估计结果为研究假说2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二)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综合经营行为影响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3第(1)、(2)列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两个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发展程度对于F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F2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都在1%水平上。此结论也再次证实了前文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发展程度对每个指标单独的回归结果。
2.龙头企业。表3第(3)、(4)列为龙头企业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两个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龙头企业发展程度对于F1具有在1%显著性水平上的正向影响,对于F2影响虽为负但并不显著。此结果说明,龙头企业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侧重于技术采纳和农产品品质方面,而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则没有显著影响。
3.合作社。表3第(5)、(6)列为合作社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两个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合作社发展程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1具有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2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4.家庭农场。表3第(7)、(8)列为家庭农场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两个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发展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1具有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2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5.专业大户。表3第(9)、(10)列为专业大户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两个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专业大户发展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1具有正向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2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合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程度对于小农户经营行为综合指标F1、F2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综合指标F1即小农户的产量、收入、技术采纳以及标准化生产等层面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综合指标F2即小农户的要素投入方面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其次,分主体看,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小农户F1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不同主体对该指标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F1指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此外,除龙头企业外,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小农户F2指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F2指标影响最大的是家庭农场,其次为合作社和专业大户(二者影响相差不大),最后是龙头企业(其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3的结果为研究假说3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三)内生性讨论
在估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影响的过程中,面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联立性的问题,即小农户的经营状况有可能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程度。不过,本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的度量是在县级层面,而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度量是在个体层面,个体层面的状态对县级层面的状态如果有影响也往往很小。由此,本文认为由联立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二是遗漏变量的问题,即模型(1)和(2)遗漏了一些既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同时还影响小农户经营行为的变量,如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等。本文认为遗漏变量问题是内生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本文拟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笔者翻阅了最近几年的政策文件,发现政府所提出的只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往往仅仅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相关,与小农户几乎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往往是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影响进而才影响到小农户。虽然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统一的规划和政策,但各地区的政策落实程度不同。因此,各个县在过去一年内是否落实过“举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这一政策指标就可能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
从表4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即第(1)、(3)列都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进一步检验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计算了本部分两个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第一个回归中,F统计量为52.83;第二个回归中,F统计量为71.73。他们都高于在10%显著水平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的临界值(约为16)。由此可以认为,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对指标F1、F2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4的第(2)、(4)列分别给出了运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剔除内生性以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综合指数F1依然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样剔除内生性后,对于综合指数F2也在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上述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核心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程度对于小农户经营行为综合指标F1、F2均具有显著作用。也就是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程度对于小农户的产量、收入、技术采纳、标准化生产及三品一标生产等层面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对于小农户的化肥、农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方面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四)作用机制
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来看,产业集聚则会产生相应的溢出效应,将知识、人力资本、技术等溢出到周围经营主体,产生一定的外部性(Cooke P et al., 2003)。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的各种社会化服务,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知识、技术经验等溢出的良好途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为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领小农户走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罗必良,2015)。

表4 内生性检验

表5 溢出效应-社会化服务影响机制检验
据此,本文选取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其中,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取值为0~6,表示小农户接受新型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种类的个数(社会化服务的种类包括集中育苗育秧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灌溉排水服务、良种引进和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服务、机械化服务)。
表5给出了将社会化服务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影响小农户经营行为作用机制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水平影响的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越高,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水平就越高,这一关系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第(2)、(3)列分别为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水平与小农户经营行为综合指标的OLS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小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越高,其F1值越高,F2值越低。此结果表明,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越高,其产量、收入、技术采纳、标准化生产等水平越高,而要素投入(化肥、农药、劳动力)的水平则越低。综上,表5的结果总体验证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会提高小农户接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而小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小农户产量、收入、技术采纳、标准化生产方式采纳等指标,减少其要素投入水平。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型主体发展程度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辐射带动作用。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促进小农户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新技术的采纳,进而对农户增收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分主体看,各类主体对小农户经营行为均具有较强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在产量、收入以及技术采纳等层面,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小农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化肥、农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层面,除龙头企业外,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小农户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家庭农场,其次为合作社和专业大户,而合作社和专业大户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
(二)政策启示
首先,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身发展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发展状况是其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的前提。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就要首先改善其自身的经营发展状况。具体而言:一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立足“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挖掘特色农产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园等方式,打造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二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生态链,提升价值链,多层面多角度发展。三要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打造品牌优势,实现农产品分等级、质量安全可追溯。
其次,要大力支持、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现代化发展进行带动,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生产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双重功能。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并不是对小农户经营行为的每个层面都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还不够完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和范围,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贴机制。由于承担了带动农户的责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成本的增加,所以政府应加大政策、税收、技术以及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对社会带动作用显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对于盲目带动或者虚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相应的惩罚。第二,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社会化服务为依托,带动周边小农户发展。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给小农户产前、产中、产后的如生产资料购买、集中育苗育秧、灌溉排水和机械化等社会化服务,以及开展生产培训等,为农民应用先进农业技术提供有关的技术服务,帮助小农户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使得小农户享受低风险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收益,并保障双方的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第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发布职能,设立信息发布机制,推动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
最后,重视对小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小农户整体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小农户采用先进农业技术以及管理技术,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也会使小农户对市场信息的把握和分析更加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具体而言:一要加大对农村职业培训基地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教育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二要加强对小农户农业技术推广的培训,使农户在生产中不断提高对现代化技术的理解,增强其采纳意愿。三要注重培养小农户对生产标准化产品以及优质产品的信心和意愿,不断提高小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生态自觉意识。四要引导小农户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设,提升小农户的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
2详见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内容,http://www.moa.gov.cn/ztzl/2018zyncgzhy/。
3具体包括2017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