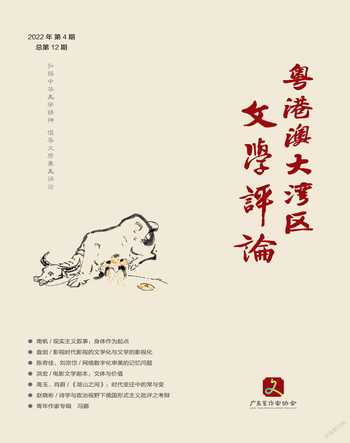在沉默的螺旋中上升
摘要:诗人冯娜2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互联网连接并改变了世界。在传播方式发生剧变的时代,诗人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在严重的时刻,诗歌何为;在与自我和外界的博弈中,诗人如何写作;身处“沉默的螺旋”,诗人又该如何维系写作的意志和伦理。本文试图通过诗人的写作实践思索并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诗歌;沉默的螺旋;互联网;意志与伦理
从千禧年(2000年)开始在语文试卷上写诗并在同年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文学奖算起的话,我写作已逾20年。年少时虽对王希孟、莫扎特、拜伦等这样天才型的艺术家常常生出可望不可及的感喟,然而,长期的写作实践让我更加确信诗人的功课乃是毕生之磨练,朝乾夕惕,久久为功。这种认知渐渐让我从精神上更加亲近博尔赫斯、珂勒惠支、希尼、苏东坡这样承受了时间重量的人。同时,也让我有意识地克服着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充溢的诱惑和消磨。
就是我在语文测验作文题里写诗歌的时候(过去的二十年,中国高考语文试卷明确“题材不限,诗歌除外”;如今依旧),世界正在被互联网所链接和改变。待我克服了在卷子上写诗歌的冲动考上大学后,几乎所有同学都开启了BBS、QQ生涯,年轻人在网络上学习、交友、娱乐,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人们的写作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输出和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范围。即时性和对话性消解着过去时代那种“正襟危坐”的写作姿态;写作不再是一个人的“苦役”。网络上连载的小说会有很多读者讨论并共同“塑造”着它的故事情节和走向;一首诗歌发表在论坛上会引来很多人评头论足各执己见,甚至相互掐架。以至我的一个诗人朋友至今还有“后遗症”,他说,只要有读者在即时通讯工具上发他的诗歌过来,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又有人要来挑毛病了,至少是来挑错别字的吧?”匿名性的互动让写作者和读者同时处在一个开放又密闭的空间中,双方都能深刻感受到影响的焦虑和激励。
互联网强大的社交功能刺激着过去需要在漫长等待中依靠手写书信、购买报纸杂志来沟通和阅读的人们,每个人渴望“看见”和“被看见”的愿望被无限放大,澎湃的表达欲鼓胀着网络空间。德国艺术家博伊斯(Joseph Beuys)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宣言在互联网上似乎正在得以实现;而这“艺术家”的实现路径不再是过去时代那样,源于个人在静默中所独立创造;更可能是创作者完全置身于大众传播的阐释空间中,一边创作,一边回应和解释着自己的创作。
可以说,我这一代作家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有一次我读到一位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提到他在连手摇电话都没有的落后乡村长大,青少年时期可以阅读的书籍十分稀少。一次邻人给他家里送来一筐食物,垫篮子的是一张画报,这新鲜的读物让他兴奋不已,他向邻人讨要了这张画报,反复阅读并珍藏起来。相较于这些如饥似渴寻找可读之物的前辈作家们的“饥馑”,我们这代作家的“饱腹感”强烈,只要你与互联网相连接,就能瞬间体会到浓稠、芜杂的信息扑面而来,“投喂”你、淹没你、窒息你。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浪潮来势汹汹,稍不留神,人就会在“物”的漩涡中打转、挣扎、迷失;而精神屏障的树立却非一日之功。我们这代人面对的困难不是困乏,而是从膨胀和过剩的资源和信息中刨出自己的真实所需;更大的困难在于拨开众声喧哗,重新回到前辈作家们所领受过的“独自”之境中。过去岁月,所爱隔山海,人心在跋涉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虑、感伤、完成自我的情志;今天,山海皆已平,被压缩的时间和空间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结构。
大学时代,我和众多文艺青年一样,在几个固定的论坛“灌水”、分享习作,在大学图书馆七楼文科基地的留言簿上用笔名洋洋洒洒抒发感受、相互留言;也因此結交了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朋友。我们自然而然地在现实中结识,一起登山、参加社团活动、搭起帐篷观测金星凌日、深夜推着自行车在校道上谈论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坐在阶梯教室的地板上一起观看女性主义的纪录片……这是21世纪初期,周遭漫溢着一种崭新的气息,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盼头奔走于生活之中。当我回想这样的青春时代,它无疑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诗篇,像一股汩汩涌出的温泉,不曾枯竭不肯冷却,提醒人保持着原初的、适度的信心和期待。度过了青春期那种表达欲旺盛而不自觉的写作阶段后,我进入了高校的图书馆工作。虽然对前路愿景依然模糊懵懂,但书籍堆积如山的地方一直清晰地吸引着我;还有,那时的我已经刻意地想与“物的喧嚣”保持一定距离。在此之前,我在报社、广告公司、电视台等多家单位实习并一度签下工作合约,但均是浅尝辄止,互不亏欠。
许多人得知我在图书馆工作,寒暄时便会提起博尔赫斯,那个遥远时代和国度的“你的同行”。博尔赫斯的名言“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网络金句一样随互联网广为流传;会援引博尔赫斯者众,但能真正领会天堂之意的人又有几何呢。正如写下《神曲》的但丁,只有那些“走在地狱的屋顶/凝望着花朵”(小林一茶)的人,才能窥见天堂的模样。天堂与地狱也许互为倒影,它们总是如影随形但不一定同时浮现。图书馆则像一块固态的时间,任世人的书写拨动着秒针。
一个写作者如果长期生活在图书馆中,那他有可能学会谦卑。当你写下一部让自己志得意满的作品,长吁一口气,成就感爆棚;互联网上的点赞率更是让你窃喜不已。这时,你走进存放着几十万册的书库深处,那些穿越时空的书籍齐刷刷望着你,有些书脊发黄变脆;有些多年来无人问津,每一页都簇新;有些画满了不同人的笔记。再想想自己的只言片语,你会哑然失笑,人类想要铭刻自身存在的信念和欲望是如此强烈,又是如此单薄微茫;像稚子蒙童往大海中投掷石子,那些涟漪在后世的回响或可忽略不计。但人类一如既往地执着着,他们深信“蝴蝶效应”掀起的狂澜足以改变世界部分的面目,这近似诗的狂想和热切,确实让他们冲破大气层迈向月球、火星;也让他们通过基因编辑改造着人类的肉身;他们还将人类个体永生的念想从古代的求药炼丹进化为人体冷冻技术……当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九段棋手柯洁,机器人“小冰”也开始写诗,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无法预期和估量的新时期,一切皆有可能,人类面临着随时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惘惘威胁。
过去的时间失效了,世界好像被推进了加速器,瞬息万变的事态、善恶莫测的世情、疾速四散的讯息,让人应接不暇,仿佛只能捎带着笨拙的肉身在无边无垠又拥挤局促的信息场中辗转腾挪。自媒体和融媒体的兴起更是将过去“文学生产者—传播者(把关人)—读者”的文学传播结构彻底打破,文学生产者的这一群体不再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也无法深隐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他们被难以逃避的传播力所裹挟,被牢牢镶嵌于文学传播的一环之中。这时候,作家本人就是他作品的一部分,他必须显露于传播环节中。当看到小说家余华在“哔哩哔哩”网站上调侃自己弃牙医从文的经历;当红的影视明星朗诵诗歌的视频能够轻易获得“10万+”的流量;作为一个诗人的我经常被杂志社公众号等要求录制音频、视频和读者们互动……你会意识到虽然每个时代写作者们都在自我与外界的博弈中写作,但这个时代的写作者面临的“威逼”和“利诱”更多元更复杂,写作者们面对的挑战似乎也更多。如何不被捆绑在资本、传播和其他力量的巨轮上,需要写作者内心有一根清晰又坚定的锚。只不过,当他们将锚抛向此刻的深海时,不知是否还能稳稳钉住最初踏上旅途时那些曾经笃信不疑的事物。
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起古人刻舟求剑的寓言。在我看来“刻舟求剑”根本不是在讲一个楚国凡俗蠢人的故事,也不是在讲变法之道,而是在讲述时间。在时间之河中,人们曾怀有刻刀一样坚硬、值得珍爱的恒定之物,猝然失去它时我们感到惊惶,赶紧标注并铭刻它的去向,并试图找回它。然而,在不可逆的时间中,那些塑造我们的过往,记忆、经验、情感都只是舟上的刻痕,如何与时间同往甚至超越它圈囿起来的河流,才是写作者的修炼。
早在1974年,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这个理论主要描述了一个社会现象,即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想法时,如果看到自己所认可的观点受欢迎并得到响应,便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传播和扩散这个观点。反之,如果某一观点遭受冷遇或者受到批评、攻击等负面反馈,一个人即使内心再认同它,也会在思忖中保持沉默。如此一来,赞同的一方人越多声势越大,而沉默的一方也将在循环往复中螺旋般下降。我初次接触这个理论时,感到它有一个颇具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精密结构,脑海中仿佛盘旋着一个彩色的螺旋,旋转着上升和下降。诺依曼的这一理论显见而精辟地解释了从众效应,在人声鼎沸的今天尤其适用。那么,如果一个写作者无可回避地置身在螺旋之中,他该如何判断哪一种声音是真正的潮汐;他是否会在犹疑不定中丧失听力?他如果能够保持镇定,又该如何描述泥沙俱下的时刻,那些泥泞混杂中发光和不发光的颗粒。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切故事袒呈于眼前,观看世界的方式多样而精微,写作者是否有信心和能力在螺旋中作为少数而上升?
——这样的问题一次次困扰和拷问着我。特别是当手机和口罩成为我们人体的新“器官”的当下,人类深深体会到并不能从过去的生存实践中获得现成的解决方案。过去的言说方式遭遇到空前的挑战,而这正是人们生命经验必须实现更新和超越的时刻。诗歌见证和记录过诸多这样的时刻,诗人们心怀悲悯和憂虑,“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约翰·多恩);他们也曾“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他们在这世上求索,体味了“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就在这技术与传播登峰造极的时代,人类面临的困境是如此具体而直接,当疫情席卷整个地球,“生存还是毁灭”,共同命运的切肤之感重新连接了人类。当人类又一次面对严重的时刻,我们是否能像布莱希特为后来者写下《致后代》这样的篇章?而我们的后代会怎样看待我们今天所写下的、所无法写下的、写下而无从流传的故事?
去年年末,我在深圳的一个场合遇到了梁晓声老师。没有多余的寒暄,他单刀直入地问我:你们少数民族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否有不同于我们汉人的看法呢?于是,我们在一个嘈杂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谈论起人类的躯体已很难再进化,精神层面是否还存在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在这次会面的两个月后,以梁晓声老师原著《人世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好多人被其感动,泪湿沾襟。这位与一个年轻诗人认真探讨人类精神如何得以进阶的前辈,在人世间惯看世道人心、离合聚散,他以他的悲悯和温暖讲出了一代人的心灵和命运。他也许没有想象过自己的作品会引发这样高密度的社会热议,而这样的传播影响不是通过传统的文字而是影视制作。
我突然也忆起某次与一个批评家朋友聊天,他说当代诗歌似乎缺乏一个整体性的面貌,诗人们各自为政、各说各话又面目模糊;找不到一个可切入的路径。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当代诗歌”,而是任何一个时代诗歌和文学存在的普遍情形:各自为政、各说各话;面目清晰与否则需要时间的碾压和“流放”。如果一个写作者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合唱”,如果写作者在螺旋中放弃寻找属于个人的声音,那么,我们如何“从天使的序列中”(里尔克《杜依诺哀歌》 )听到那呼喊呢?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追寻人类那些臻于完美的梦景,也不在于讲述人类想象力所能企及的全部故事;而是勇敢而真诚地倾诉我们所经历的、梦想的、沉沦和飞升的种种际遇、失败、努力,尊严和荣光。它自然没有仪器那般光滑、精密的技巧和手段,也没有复杂、迅捷的运算能力,也许它只是一颗残破不堪的心灵不甘地跳动;但你知道那永远与人性、良知相连并最终通向人类命运的关怀和责任,才是螺旋风暴中的磐石,一个有锚的人才能将其坦然抛出而不担心它没有着落。
57岁便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还说过一句话,“人会逐渐同他的遭遇混为一体;从长远来说,人就是他的处境。”对我而言,这句话比起身处天堂一样的图书馆更有提示性。人会不自觉地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融为一体,无论是回望深渊还是沉迷于元宇宙。在这样的时代,抑或在任何一个时代,维系和坚守一种写作的意志和伦理,似乎比强调写作的技巧和内容更加重要。
在世界上所有人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两年,我也陷入了漫长的停顿期,经常打开空白的文档呆坐良久而不知该如何下笔。失语,是这个时代的症候之一。在深不见底的螺旋中,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直到我看到85岁的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创作的长卷——《诺曼底的一年》。这是他从2019年底避疫居住于诺曼底乡村所画下的风景。依旧是画家代表性的绚丽色彩,依旧是让人心安的旷野和花朵,他所见到的世界和他年轻时所路过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处的树木与他的家乡没有什么不同,也与我的老家,中国的西南部山地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这土地历经战争、疫病、灾荒,那些残损、不堪与黑暗都一一被泥土所吐纳,在它的头顶聚雨成云,又如轻捷的鸟儿一般飞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被他透亮的凝视所安慰。这生活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用最脆弱的花瓣、草茎、叶脉恢复着四季,恢复着人们内心柔软而坚忍的部分。艺术疗愈着苦难者的创伤,艺术在崩塌中用它的时间刻度创建着新的秩序。慢慢地,我恢复了写作,一个诗人继续着她的工作。
有时我也主动向大众传播诗歌。我愿意相信人类文明之所以得以延续,不是因为纯熟的理性战胜了种种磨难,而是因为人类保有深沉的感情。这感情包含着人类不完整的智慧和在螺旋中试图飞升的信念。它就是诗。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