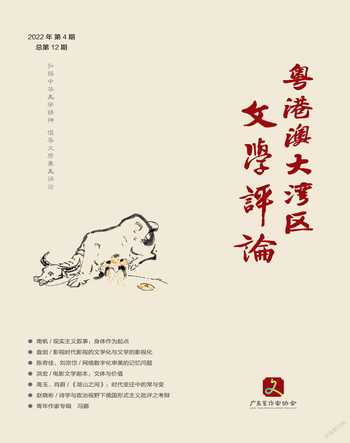历史散文中的“我”
詹谷丰
一个人的一生,常常会出现无法预知的偶然性和意外,作为一个写作者,散文,也是我的偶然和意外。《书生的骨头》《半元社稷半明臣》《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等三本散文集的出版,完全是我写作四十年里的意外收获,是我人生中的无意插柳。
与诗歌、小说等自始至终站在潮头上的文体相比,散文的保守和落寞,是众所公认的事实。
文化学者和散文家祝勇在概括散文陈腐的弊端时,用了“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咏物抒情、以小见大、结尾升华”等词,准确地描述了散文的现状。祝勇认为,“尽管中国散文有着优秀的传统,尽管《岳阳楼记》对于范仲淹本人来说可能纯属‘个人写作而并非随声附和,但是当它们成为人人必须仿制的样本,进步的可能就被取消,散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没落的文体。”
祝勇先生这段话,引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排行榜》的序言,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散文的拒绝者和局外人,作为一个顽固的虚构者,我正在中短篇小说里苦苦挣扎,执迷不悟。
我对散文的轻视,只是一种简单的直觉,它与祝勇先生的判断不谋而合。
至2011年我写《义宁的源头》这篇散文时,我已经在小说中摸爬滚打了25年,一个头破血流的人,在许多人用文字对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致赞扬的时候,我作为陈先生的故乡人,我看到了陈氏这句名言的起源,一个家族的精神史和士人气节,在陈寅恪先生这里继承衣钵和发扬光大。这句话的振聋发聩,在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现状中,陈先生学术理想的坚持和重申。
在此之前,我也无意中写过散文,那些篇幅短小,一事一议的文字,或者应景,或者为写而写,都落入了传统散文的窠臼。《义宁的源头》,完全是有感而发,是我对陈寅恪精神来路的个人理解和源头探寻。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人的精神脉络,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的地域背景下成长、成熟,那些被世人忽略了的故事,通过情节和细节,展示了一个文化家族的历史渊源。
这篇发表在《花城》2011年第5期的散文,写人物命运,写精神的成长过程,它内容的丰富,情节的复杂,结构的安排,都与传统相去甚远。这是一篇偶然之作,我尚没有意识到,这篇散文对我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对散文的认识和此后文学创作的转型,是一个分水岭。幸运的是,这篇散文并没有成为一个孤立的文本,沿着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和人生之路,我的阅读进入了“民国”,进入到了“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陈寅恪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自觉主张,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和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国家性的功用。
2013年1月,我又在《花城》发表了《书生的骨头》。这篇散文表现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对待政治和权力时的独立精神,他们为维护人性尊严和学术正统时的付出,甚至牺牲,让读者看到了乱世中读书人的自由、独立、理性和理想主义。这篇散文给我带来的影响,是我无法预料的结果。《散文选刊》《名作欣赏》和多个散文年度选本收入了这篇文章,入选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散文榜首,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都给了它意外的荣誉。
至此,散文为我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而小说,则被我关上了大门。一个人文学创作的转向,其实是有因缘的。
我与散文的人缘,最早源于无意中在杂志上读到的一段文字:
印度佛教在翻越冰寒的喜马拉雅山之后并没有丧失它的温度,佛光一旦降临在这块贫瘠的高原上,就注定会为这个几乎寸草不生的雪域种植精神种粒,使困境中的人们有所乞望。在这片荒陆之上,只有宗教能够发挥巨大的整合力量,将相距遥远、或许终生不会谋面的陌生人聚合在一起。
也许因为藏地景物的巨大尺度使人感到无助,使人们精神上的欲望远胜于其他,只有永恒的宗教可以对抗无限的空间;也许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绚丽风光的极大反差,使人们看到了痛苦与幸福之间可以穿越的距离,从而坚定了皈依佛教的信念;也许因为高原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人世间最理想的模拟天堂,它将深奥的教义体现为简明的视觉画面呈现出来,因而成为最适宜宗教的土壤……只有朝圣路上不畏风雪的藏民能够告诉你,当宗教的第一缕光芒射入灵魂的时候,他发自心底的温暖和感动。
这段文字,引自《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第2期祝勇的散文《佛光》。如今重温,并不感到惊世骇俗,但我在17年前读到时的感觉,却是醍醐灌顶,瞬间改变了我对散文的轻视。
那個时候,我不知道祝勇是何人,更不知道异军突起的新散文运动及其带来的影响、冲击和改变。我唯一能做的是顺藤摸瓜,从书店里找到祝勇,从他的《散文叛徒》中,看到散文的革命,看到一大批我陌生的名字。
我的文学创作,至此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往右,是我执迷了多年的小说,那里有熟悉的风景,往左,是一片陌生的森林,交叉小径,不知道里面潜藏着多少风险。
新散文的风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绝色。我早已过了冒险的年纪,也没有成名成家的抱负和压力,我抱着尝试的态度,贸然走进了散文的森林。一个写了二十年小说的作者,在新散文的诱惑下,绝情地转向。寻找新欢。
文学创作,犹如登山,只有险峻的地方,才能看到绝美的风景,而且,悬崖绝壁处,不容并行,也不容回头。
十年之后,我以一个登山者的姿态,站在了文学的半山腰。当我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回首山下,才发现我的浅陋和偏颇。虚构艺术的魅力,让一个起步者,以恋人般的执着,苦苦追求,所有的收获,也只是一个耕耘者,在歉收的年代里的精神自慰,而纪实的散文,更像一个饥饿的行人,在别人收获之后的土地上,无意中捡拾的一个番薯或者玉米。充饥的喜悦,是饱食之后抒情的地主无法体会的。
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从《义宁的源头》之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小说,其实,表面上的情断义绝,并不能掩盖我对小说的感恩,更不能抹杀虚构艺术对一个写作者血肉交融的影响。熟悉我创作的朋友,在我的散文中,发现了小说对我的潜移默化,同时,我也看见了二十年小说训练对我散文的改良。
从历史进入创作,显然不是散文的传统路子,勉力为之,也只是危险的逆行,但也成了一个散文新人的救命稻草。十几年之后,当我回顾自己散文创作的成败得失时,我深深庆幸自己不是中学语文课堂上墨守成规的好学生。我的幸运在于,在进入散文的起点上,我没有落入短小精悍、一事一议的陷阱,也没有在那些故土、乡愁、农耕、农具、亲情、炊烟、祠堂、土地、池塘、田园、草木、鸟兽、时令、节气的狭小世界里沉迷不拔无病呻吟。
历史散文,许多人愿意在前面加上“文化”二字,以示与传统的割裂。而在余秋雨走红的九十年代初,“文化”,正是涂抹在散文脸上的口红。在一个以“文化”自豪和标榜的时代,一种新的散文模式迅速走红,跟风者趋之若鹜,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超越了传统,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模式化之后,作为一个读者,我也发现了散文中的破绽。
在《道士塔》中,余秋雨对看护莫高窟的王道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与外国人交易珍贵文物时的描写,小说一般,破绽百出: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拾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蹊跷。
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上述没有文献记载的行为动作,不在现场的作者是如何看见的?这样的虚构有何根据?
历史散文,曾经被许多人不屑。尤其是熟悉历史的读者,没有从历史之外得到新的发现,也没有得到强烈的艺术审美感受。那些轻浮的写作者,以最简单的方法处理素材,转述历史,实在是脱不了干系。
一方面,有些历史散文的作者从史料到史料,用公共语言,将教科书上的历史或者人物复述一遍。我见过一些写民国女性的散文,连篇累牍,都是史料的照搬和重复讲述,毫无新意。那些和写作者所处的时代毫无关联的人物和故事,和当下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和当下人的生存和情感,格格不入。当所有的猎奇都成为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之后,这些打着历史旗号的散文,成了发馊的冷饭,不被读者看好,理所当然,这是阅读的灾难。另一方面的误读,也让偏见成为历史散文的先入为主。有人认为,散文所表现的内容,都是已有定评的历史,既没有新的发现,也没有新的结论,与其读历史散文,不如读教科书。这些将历史教科书同历史散文等同起来的人,不仅有一般读者,也有散文作家,更有文学刊物的编辑,他们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尤其是没有看到散文中的“人”。
历史散文,也许不是挑战历史教科书的反叛文本,从事历史散文写作的人,也不是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他们的田野调查和现场采风,仅仅是现场感受,而不是为了寻找历史的证据或重写历史的证词。
对于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表述方式和表述目的大相径庭。记得祝勇在东莞讲学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五百年之后,作家面对手机这种出土文物,关心的是这件文物的名称、功能、作用,什么人曾经用过,那些使用过这件物品的人之间构成了一种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曾经围绕这个器物是否有过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则是制作器物的材料,制造的年代。器物背后的人物,是文学和考古学的一个分水岭。文学永远是人学,是生动形象的人学,而历史学里的人物,只是一个没有性别、没有性格的符号,是历史的一处标记。
历史离我太遥远,即使离我最近的“中华民国”,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人物,也有了一百年的历史,我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只能从黄脆的故纸中寻找和发现,文献中的人物,只有生平事迹,只有教科书对他们盖棺论定,没有喜怒哀乐和心灵情感,那种平面单一的记叙,隐藏了他们的短板和缺点,却彰显了记录者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尤其是那些亲属后人创作的人物传记,隐恶扬善,美化传主,让主人公以道德完人的姿态,站立在书中。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常常被写作者用来衡量和检验小说艺术,许多热衷于传统散文写作的人,从来不将这个常识置于散文的背景之上。那些篇幅短小、一事一议的报纸副刊散文,写景抒情,讲述故事,却回避人物。两三千字的有限篇幅,并不能成为空洞无人的借口和理由。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是散文人学的理论倡导者,他的多部著作,都提到散文背后的人这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谢有顺将散文中人的缺席上升到了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困境:“在一种写作的背后,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一点上,小说、诗歌或许还有技巧可以掩人耳目,但散文是本色的文体,很难作假,它不像小說,可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出来说话,散文必须直接面对读者,随时向读者发言。所以,余光中曾说,‘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
散文革命的话题,在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那里,是一个呼吁已久的话题。但散文的传统太久太深,保守主义者占据了报刊选本等重要平台,创新的实践者势单力孤。即使是小说家,他们为散文悄悄地注入了许多新鲜元素,但他们不会为偶尔为之的散文写作分散精力,大声疾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王必胜和潘凯雄两位文学评论家编选过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那些出自小说名家之手的散文,全无传统散文的套路,自由,随意,让一个轻视散文的小说作者不由对散文产生了一些好感。
从不标榜自己为散文家的人,无意中写出了真正的散文,二十八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史铁生、方方、王蒙、陈建功、张炜、蒋子龙、莫言、铁凝、韩少功、迟子建、叶兆言、苏童、格非等小说名家对散文的发言:
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以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也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史铁生)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雕琢,没有矫饰,没有表演。(王蒙)
很久前有人问我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小说,我说:怎么舒服怎么写,这就是一种随意,对于散文,我仍得这么说。(方方)
散文突出的恰恰是它的朴素和真实,是赤裸裸的内容……写散文不能专门化,它应是情感被逼到尽头时的一次吐露。天天被逼到尽头,专门倾吐,也不可能。我要先将其写得真实。(张炜)
小说可以玩技法,报告文学可以玩事件,诗歌可以无病呻吟,故作高深。谁敢玩散文?没有真意如何成散文?唯真诚才是心灵的卫士,是散文的生命。(蒋子龙)
所谓见真性情的东西,一矫揉就完了蛋。(莫言)
小说名家们的散文观,包含了自由、随意、真实、情感、灵魂、性情等综合因素,他们对杨朔散文的模式化和教材化,杨朔散文的宗师角色等,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他们的散文,远远超出了反串意味。八十年代末期的小说家们,无意中用自己的散文实践,为多年以后的散文革命,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借鉴。
小说家的散文现象,二十年之后,成为谢有顺所说的散文背后的人的有力例证。谢有顺认为,小说家散文的兴起,让传统散文的泛滥抒情得到了有效的克制。小说家“更注重经验和事实,更注重自我存在的心灵印痕。这种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卑微而真实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谢有顺的断言,指的是现实生活,同时也适用于历史散文。我作为一个无意中闯入了历史的散文写作者,看到了那些用文学的形式支撑起历史的人物。
历史以散文的面目出现的时候,绝对不是风花雪月和草木虫鱼,而是那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朽人物。散文描写一段历史,或全面写一个历史人物,如果没有事件和人物命运支撑,万字以上的长文,将失去可读性和故事悬念,最容易变成枯燥无味的文史。
我从“民国”知识分子题材中挣脱出来,进入东莞乡贤和广东左联人物的时间很短,用几年时间,艰难地写了十几篇历史散文,编成《半元社稷半明臣》《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两本书出版。这是师友们对我写作的启发,也是一个小说的虚构者转向之后的意外收获。
一个没有太多传统约束的散文作者,打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之后,看到的史实和人物命运,是一个新的世界。过去熟知的历史结论,只是一副近看的老花镜,而由众多不同的文献资料组成的复杂景象,则是望远镜之下的万花筒。我没有能力推翻历史,但我可以用自己真诚的文字,呈现复杂多变的事实;我没有第一手资料和野心重写人物,但我可以在文献的海洋中打捞碎片,在尊重人物性格和艺术规律的原则下,描写人物,还原人物的真实面目。
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中,丘东平并不是左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柔石、殷夫、冯雪峰、冯铿、田汉、蒋光慈等左联作家相比,“丘东平”显然不是一个最有知名度的名字。然而,丘东平却是一个最有传奇色彩个性鲜明的复杂化战士,他的人生,突破了丘东平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对他的政治评价,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学理想,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争时期,丘东平就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开始了伟大的实践,由于战场上的牺牲,丘东平没有完成他的宏愿,但他“中国新的文化人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反映伟大的民族战争的盖世之作将会诞生”和在写给欧阳山和吴奚如的信中“此行所见所闻,是称伟大,此后战争题材,东北作家不能专利”“只要不死,将来就有伟大的题材写小说”的预测,其实是一个作家的断言,这些具有远见的卓识,让八十年之后的读者,看到了丘东平高屋建瓴的非凡气势和眼光。
“完美无缺”这个成语,是文学人物的最大敌人,也是散文写作的大忌。在盖棺论定的评价之外,我在文献的缝隙中,看到了丘东平作为一个正常人物的另外一面。当《中流》雜志退回了他的投稿之后,他立即给编辑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第一句话便是“我X你十八代祖宗”。《太白》主编陈望道拒绝发表丘东平的文章,丘东平耿耿于怀,当陈望道将他刚刚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送给他的时候,他不屑一顾,将书扔到一边,扬长而去。在写给胡风的信中,他坦诚自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在济南逛了一块钱的窑子,得了淋病。他还向聂绀弩表达了与寡居嫂嫂的爱情。
左联女作家冯铿,是我脑海中永远的烈士形象,是革命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华,英勇斗争,宁死不屈。但是,我更愿意将她描绘成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在许峨和柔石两个男人之间,她用丈夫和情人的角色定位他们。而且,她对柔石的性爱,并不在隐秘的地下进行,她残忍地让许峨尝到了爱情背叛之后的苦果。
散文后面站着的人,绝对不是革命样板戏中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们是和作者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广东左联人物,并非革命的符号,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将红色题材和革命人物等同起来。我在写作《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之前,也有过犹豫。一些熟悉我写作的朋友,当他们看到“左联”二字的时候,就将保守、落后和歌功颂德同我的写作作了无辜的牵连。
我的历史散文中,经常出现“我”的视角,那些用议论方式表达的“我”的身份,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它不是叙事人称,而是写作者的参与方式。
如果认同散文在场主义的观点,那么,“我”就是历史散文中的一个人物,是我穿越时光回到历史现场的最好方式。
散文的创作,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确立,祝勇先生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文中,将创作延伸到了长度、虚构、叙事、审美、语感、立场等诸多方面。祝勇写这篇宣言式的文章的时候,离当下有了十六年的时光。十六年过去,散文创作已经有了很多改变,周晓枫、格致、塞壬等散文家,已经用自己的实践,成功地呼应了散文的革命,但是,与小说和诗歌相比,散文的面目,依然模糊和传统。那些具有创新意识的散文,并不为大多数文学刊物接纳,能够用宽广的胸怀和雅量容纳创新的,大多是那些具有先锋姿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一般性文学刊物,尤其是那些专业的散文杂志,为了迎合读者和基本订户,老气横秋、不思进取和改变。甚至一些掌握了发稿权的编辑,标榜创新,但自己的散文却四平八稳,不改保守陈旧。
“革命”,是一个激烈的动词,将这个动词用于一种文体的创新,说明这种文体的陈旧和保守,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祝勇甚至用了“散文的叛徒”这样极端的语言修饰散文革命的勇气和信心。历史散文,创新的空间尤其广阔,写作者必须努力进取,才可能在文学的长河中激起浪花。
作者单位:东莞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