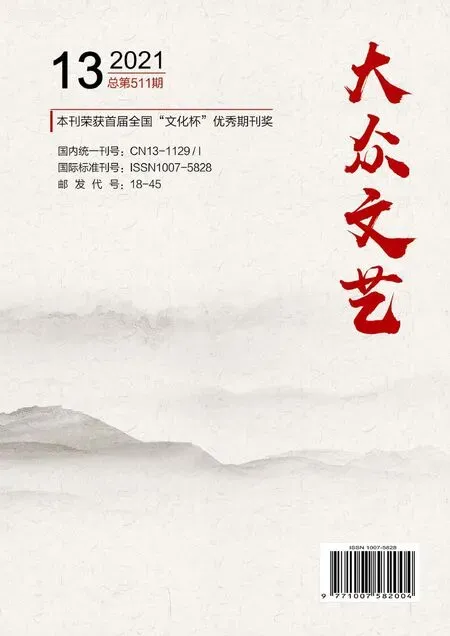吴世昌与霍克思英译《红楼梦》
唐小彬 刘 珩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天津市宝坻区 301830)
国内梳理吴世昌红学成就的文章不少,但几乎所有文章的重心都集中在吴先生的《红楼梦探源》与《红楼梦探源外编》两部作品。如施议对《吴世昌传略》、邓庆佑《吴世昌和他的〈红楼梦探源外编〉》、段启明《略谈吴世昌先生的红学贡献》、刘扬忠《吴世昌的治学道路及贡献》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谈道吴世昌先生的红学成就时,基本上都是只关注到了吴先生的《红楼梦探源》与《红楼梦探源外编》两部作品,均未涉及吴世昌对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指导与贡献。本文将从历史资料中耙梳出吴世昌与霍克思的交往来历,以及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影响与所提供的帮助,证实吴世昌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世昌与霍克思的师生缘分,源于吴世昌赴牛津教书之时。据邓庆佑先生考证,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吴世昌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教授国文。抗战后,随着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之后因作文批评政府而受到当局与校方的威胁。在此之际,收到牛津大学的聘书,不得已前往牛津教书。根据霍克思汉学年谱,1945年10月,霍克思回到牛津大学,从原来的古典学系转入汉学科,成为继戴乃迭之后牛津汉学科第二名学生。此时汉学科只有一位教师,前伦敦会士修中诚讲师。“1947年修中诚退休前又促成牛津电聘中国学者吴世昌来校任教一事”。1948年1月8日,吴世昌到达牛津大学,担任汉学科高级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史、中国诗及甲骨文等课程。吴世昌到达牛津以后,住处离牛津大学不远,霍克思此时已从汉学科本科毕业,但是很快就和吴世昌熟络起来,经常登门求学。此时的霍克斯,从学于吴世昌最多的是唐诗。霍克思曾跟随修中诚学习先秦的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和老庄等中国典籍。而且,阅读与背诵这些先秦诸子的典籍,几乎构成了他学习中文的全部内容。这和传统中国的私塾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中国文学的其他内容,比如唐诗宋词、白话文学、元明清小说戏剧等,霍克思都是一无所知。据霍克思回忆,这些先秦典籍都是特别难读,而对中国文学的全然无知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由此可见,吴世昌与霍克思不仅有师生情谊;而且,霍克思对中国文学与诗歌的了解,很有可能是受了吴世昌老师的启蒙。后来他在翻译《红楼梦》诗词曲赋的时候能够如此游刃有余,与吴世昌的诗歌启蒙应该是大有关联的。
霍克思赴北京大学留学,得到了吴世昌的引荐。1948年,霍克思自己尝试阅读白话文作品,如《水浒传》与鲁迅《彷徨》等,或许是因为一直阅读背诵的都是先秦诸子的典籍,白话文的阅读让他有挫败感。初次阅读《红楼梦》的经历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按照霍克思的回忆,他在牛津大学时就从同学那儿听说过《石头记》。这个同学就是当时正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的裘克安。裘克安不仅给他介绍红楼梦,告诉他这是中国第一伟大的小说,还送了他一本《石头记》。他说自己努力尝试读了,但因为实在太难懂,就只勉强啃了第一回的第一页。由此,他决心赴中国留学。他向北京大学投了多封申请信未得回复。临行前,老师吴世昌为其取汉名霍克思,并为其向国内好友写了多封推介信,其中有致胡适和钱钟书的信函。拿着吴世昌老师的推荐信,霍克思在上海逗留期间,专门去拜访了钱钟书先生。这次拜访,虽然为二人一生唯一一次见面,却建立了持续一生的友谊。他对钱钟书充满敬仰,此后一生始终关注钱钟书。1981年,霍克思专门给钱钟书邮寄《石头记》译本第三卷,并得到钱钟书的盛赞。钱钟书曾在给宋淇的信中,夸奖霍克思的《石头记》译本,说其文笔远在杨氏夫妇译本之上。以钱钟书先生的英文鉴赏水平,这样的断语几乎可以视为定论。后来多种红楼梦翻译研究著作中,以及霍克思、杨宪益译本在西方流行程度的悬殊,似乎都印证了这个论断不虚。
在北大学习期间,霍克思花了大量的精力研读《红楼梦》。为了提高汉语口语能力,霍克思除听课及与舍友练习外,另自请先生上门一同研读中国的经典白话作品。两人并排坐着,霍克思与老师轮流朗读《红楼梦》中的段落,然后老先生逐字逐句进行讲解。如此坚持了一年多时间,霍克思跟着不懂英文的老先生通读了《红楼梦》多个章回,为以后的《红楼梦》英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外,为了帮助理解,霍克思还翻译了部分《红楼梦》章节,如香菱学诗、宝黛读西厢等片段。1953年,霍克思受聘任牛津大学中文讲师。此时,吴世昌已经在牛津大学教书多年,二人成为同事。共同开设中国近现代文学。从后来二人的合作来看,《红楼梦》无疑成为二人经常探讨的话题,为后来吴世昌创作第一部英文红学著作《红楼梦探源》与霍克思翻译《红楼梦》都奠定了基础。
吴世昌认真做红学研究,与霍克思萌生翻译《红楼梦》的想法,几乎同时发生,这与二人在牛津共事、互相切磋不无关系。据吴世昌回忆,他所读过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拿《红楼梦》做教材。他最初读《红楼梦》,是初三生病在家得闲时,才把《红楼梦》拿来作闲书消遣。他认真搞起红楼梦研究,要到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全国性运动。国际上开始注意《红楼梦》。巴黎、海牙联合出版《汉学要籍纲目》的编者,邀请吴世昌为此书作提要。而且,这个时候,吴世昌指导的学生有人在研究《红楼梦》,正好牛津大学买到一部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庚辰本《石头记》。吴世昌才开始认真做红学。吴世昌做红学研究的资料,除了刚才提到的1955年版的庚辰本,还有1954年俞平伯编辑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以及周汝昌1953年初版的《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亲友的诗文集等。到1956年,吴世昌写完《红楼梦探源》(以下简称《探源》)前三卷共计十一章内容。1958年9月至1959年6月,霍克思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远东系担任中国文学客座讲师。赴美前,霍克思帮助吴世昌校读《红楼梦探源》一书的前三卷,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可见吴世昌在创作《探源》一书时,必常与霍克思探讨《红楼梦》。这种探讨,使得师友二人在很多层次上共享了红学的最新成果以及红楼梦的英译策略。而且,据柳存仁回忆,1957年初次拜访霍克思时,霍克思已经有翻译《红楼梦》的计划。霍克思1958年继任美国学者德效骞,成为牛津大学汉学系第六任讲座教授。之后开始加大牛津大学汉学科的课程改革,改变了理雅各所创立的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传统,将中国文学纳入课程大纲,并在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全面阐述了改革方案。牛津大学汉学科几位教师中,唯有吴世昌与霍克思志同道合,共同致力于这次改革。《红楼梦》由此纳入教学大纲,并由吴世昌专门开坛讲授。1961年,吴世昌以英文创作的《探源》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梳理了新旧红学的最新成果,而且在多方面提出创见,是第一部用英语创作、系统深入的红学专著,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为红学西渐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吴世昌《探源》对霍克思有深刻影响。至少有两处可见:霍克思英译《石头记》卷一序言以及霍克思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上面的文章《西人管窥红楼梦》。霍克思利用了三十年来最新的红学成果。霍克思英译本第一卷序言中,梳理了红学的最新成果,多次提到吴世昌老师的名字,并对吴世昌《探源》中的观点多有采纳。如认为甲戌本凡例为曹雪芹弟弟棠村的序言:“作者的弟弟说,这部小说之所以频繁地出现梦的意象,是因为作者想在书中追忆的光鲜奢华的青春岁月,在他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已经消逝的一干二净了,以至于回首往事,那更像是梦幻一场。”接着霍克思将一般被认为是曹雪芹自序的凡例翻译出来。这显然是受了吴世昌的影响。吴世昌在《探源》一书《棠村小序的发现》一节中专门论证了这一点。接着在这一节的总结处吴先生说:“曹雪芹的弟弟棠村(即‘东鲁孔梅溪’)曾为《红楼梦》的‘旧’稿《风月宝鉴》写了许多小序,可能是每回一篇。现已从四个脂本《石头记》中发现了四十九篇。其在脂残与脂京中者,过去被认为是作者写或脂砚的‘总评’,现在看来是棠村小序无疑。”据邓庆佑《吴世昌和他的红楼梦探源》一文所言,吴世昌“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甲戌本,首先对此本的命名提出了不同意见,又指出了胡适对此本的一些错误看法,还对此本的脂批、回前题诗的作者、关于此本卷首的‘凡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提出了此本中呈现有棠村小序,这是迄今为止红学界的独家主张。”在谈道贾宝玉原型时,引用了吴世昌的观点:“宝玉就一定是一个复合型人物,我想吴世昌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对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部分采用了吴世昌的观点,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猜测:曹雪芹的手稿,被一个不识字的满族寡妇收藏着,后来“请一位男性亲戚或是家族朋友‘想想法子’;经过这人的大肆修改之后,手稿辗转为程伟元买到手并交给高鹗加以编辑。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高鹗所做的是把这新近发现的后三分之一的书稿与他所采用的前八十回的脂本统一起来。”。霍克思的猜测是曹雪芹的后四十回手稿是先被一人大肆篡改以后才流入高鹗手中,高鹗只是把这经过篡改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编辑成百廿回本。这与吴世昌在《探源》中的观点部分重叠,吴也认为后四十回中有部分曹雪芹原稿,如黛玉之死、抄家、元春之死等情节,但都是经过大肆篡改的,而篡改之人正是高鹗:“有些故事透露了来自曹霑原稿的迹象,它们大概是程伟元收集到的残稿。即使是这些为数很少的遗留下来的素材,也被高鹗彻底改写过了,只留下了一点可供我们辨认的痕迹而已。”对于《风月宝鉴》与《红楼梦》的关系,霍与吴的观点差不多,都认为《风月宝鉴》是更早的小说草稿,后来弃用,在《红楼梦》中保留了部分的情节。霍克思在其英译本第一卷序言中说:“《风月宝鉴》是雪芹和他的家人曾经考虑过的书名。从脂砚斋的批语来看,这实际上是更早的、或许也更短的、后来被曹雪芹弃之不用的小说草稿。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放入现在的小说。”
关于霍克思所受《探源》的影响,在他用中文作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上面的文章《西人管窥红楼梦》中,也可见一斑。这篇文章中,霍克思就《红楼梦》中丫鬟名字的英译以及丫鬟名字的确定做了详细的阐释与考证。在论及这些丫鬟的名字时,霍克思参考了多种版本,其中引用脂批本的地方,霍克思一律采纳的是吴世昌的说法。吴世昌在《探源》中认为胡适定名的“甲戌本”“庚辰本”有误导性,改称“脂残本”与“脂京本”。霍克思在《西人管窥红楼梦》一文中,每当提到这两种脂批本时,都沿用吴世昌的说法。胡适所定的名称已经普遍为大家所接受,而吴世昌的说法除了吴个人之外,很少见其他学者使用。由此更可见霍克思对吴师红学研究成果的肯定以及在版本研究中受其影响之深。
1962年吴世昌携家人返回中国以后,与霍克思在红学问题上还常有切磋。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吴世昌在创刊第1辑和第2辑上面,分别发表了四首七绝,《题〈石头记〉人物图七绝四首》《题〈红楼梦人物图七绝四首〉》。霍克思读过这八首七绝后,用繁体汉语竖排书写,采用和诗中最严格的步韵依吴世昌《题〈红楼梦〉人物图七绝四首》中《宝钗扑蝶》一绝的韵次与韵词完成,全诗表达了对老师吴世昌先生红学研究的敬仰。霍克思全诗内容如下:“读吴世昌先生七绝《扑蝶》/学生霍克思次韵/考假询真日月飞,皇妃本即郡王妃。石兄宝鉴光重照,踏破楼梯识暗机。”可见虽然两地相隔,霍克思对吴世昌老师的红学研究一直非常关注。1979年,霍克思在澳大利亚探望大女儿期间,受女婿闵福德的博士导师柳存仁先生之邀,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开了三场《红楼梦》讲座。在讲座上,霍克思就戚蓼生序言中的典故请教柳存仁。柳存仁与吴世昌、潘重规多次通信探讨霍克思提出的问题。1994年,霍克思再见柳存仁时,还专门问及他对这一问题的新见。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窥见两点:第一,霍克思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非常的热爱与不一般的执着,往往在一个问题上,作多年的思考与研究。第二,即便在吴世昌返回中国以后,即便霍克思有红学问题没有直接向吴世昌师请教,他请教的人还会请教到吴世昌那里,相当于霍克思间接受教于吴世昌了。
从在牛津做学生时接触《红楼梦》,到1970年正式与企鹅签约开始《红楼梦》全译,霍克思研读《红楼梦》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中,有将近十五年时间,恰是吴世昌先生在牛津教书的时段。霍克思从吴先生得到诗歌的启蒙;霍克思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熟知,在《红楼梦英译笔记》中的细致比对与探索,多少与校读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手稿有关。得益于霍克思的课程改革,吴世昌在牛津大学讲授《红楼梦》。在那些岁月里,在牛津大学校园里,必定常常回响着二人探讨红学的声音。
在《红楼梦》西渐的漫长征途里,吴世昌除了用英文创作《红楼梦探源》首次向西方介绍最前沿的红学成果这一贡献之外,他在霍克思英译《红楼梦》这件伟大事业上的独特贡献同样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