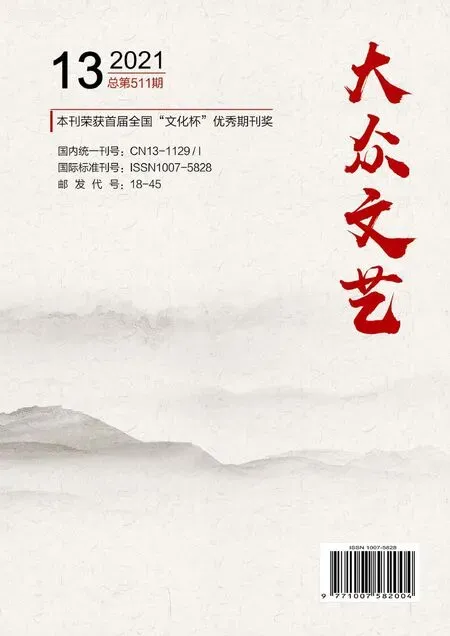追寻的生命哲思与失落的政治梦想*
——论《庸言》诗歌的情感向度与审美主题
张 辉
(西安科技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钱仲联对民国时期的旧体诗有过这样的总结:“至于民国,为时亦非太短,操觚之徒为诗话者,殊不乏人,或出专书,或散见于期刊,视前修或且过之。”张寅初进一步指出:“旧体诗的形式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积淀着汉民族的审美特性。这一形式至清末民初,又恰好遇上帝制颠覆、西夷入侵的社会大变动,从而现成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知识分子运用来抒发黍离之感的主要形式……清末民初旧体诗记录时代风云、表现人性悲欢所达到的沉郁而又酣畅的审美高度,既是这一艺术形式已有的成熟性使然,也是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诗人群体的特殊遭际及其天才的创作的又一个毫无愧色的高潮期。”
晚清帝制的结束民国的建立,为传统文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这些文人们以诗歌的活跃来对抗政治的失势,借助报刊他们的诗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报刊也成了他们发表诗作、联络友人、阐释理念的重要阵地。《庸言》由梁启超创办于1912年12月1日,地址在天津日租界旭街17号,杂志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主要撰稿人有吴贯因、黄远庸、梁启勋、蓝公武、汤觉顿、林长民、罗惇曧等十几人,从1912年创刊到1914年停刊,共出版两卷三十期。《庸言》的“艺林”栏目中“诗录”占有很大的篇幅,其中刊登了郑孝胥、陈宝琛、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方尔谦、易顺鼎、陈三立、樊增祥等人的诗作。从《庸言》上发表的诗作中,可以窥见这些文人的整体心态,尤其是他们在退出政治舞台、赋闲之后内心幽微细腻的真实情感。这一时期他们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有对清王朝政治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依恋,有对新世界的不满和抵触,有传统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不事二朝的心理,有对古典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他们经常聚集,研读经书,谈论历史,诗酒流连,以传统文学的形式寄托他们难以割舍的政治梦想,抒发他们内心的无奈或伤感,旧体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了他们的精神依托。
一、有关生命的思考: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的追寻
面对帝制终结的巨大历史变革,这些文人身心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惑,与普通老百姓相比,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与清廷之间的关系使其很难平静地面对历史变迁。身处民国如何在生命的意义上安顿自身,便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毕竟在旧日王朝已经倾覆之时,成仁取义才是易代之际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在他们的诗作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昔日守节赴死英雄地追慕。郑孝胥的《十一月十六日夜携垂二子观叫天演杨令公曲本》中化用了杨令公的典故表达了作者的心境。杨令公是宋朝的大将,当年宋军与契丹大战于金沙滩,他向元帅潘仁美提出诱敌深入、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但未被采纳,反而潘仁美要求其硬拼。杨令公要求主力在陈家谷接应,结果潘不予配合,竟自望风而逃,致使杨令公被擒。杨令公被擒之后仍坚持大义凛然的气节,终绝食而死。“杨令公曲本”这出戏曲为了表现杨令公威武不屈,以身报国的精神,使其死在李陵碑下。郑孝胥借此典故抒发了此刻内心的情感,诗作中写道:“失途供奉成遗老,垂死英雄有骏姿,霜月满天冰作涕,喑鸣犹绕李陵碑。”“垂死英雄有骏姿”是郑孝胥对杨令公的评价,称杨令公为“英雄”,正是作者赞颂其为北宋战死的大义及气节,而自己对恢复旧制却无能为力,相比之下,悲哀之感油然而生。郑孝胥的《题程伯葭所藏精忠柏片》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心情,其诗写道:“世方憎忠义,君胡表此柏,移之置岳坟,终古配毅魄,吁嗟墓中士,涅背字历历,苌叔苦违天,天假血成碧。”传说“精忠柏”原为南宋大理院风波亭畔的一株古柏,岳飞含冤入狱被害后,这株柏树如遭雷击,立即枯萎,但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枯柏却僵而不腐,像铁石一般坚硬。人们仰慕枯柏英烈般的风骨,就称之为“精忠柏”。在此诗中,“精忠柏”作为忠义的象征被郑孝胥赋予了极高的意义内涵。可见,岳飞、苌叔作为忠义之士的代表,可以以死来效忠先朝,虽死而犹未悔的精神是作者所钦佩和羡慕的,而作者自己,既不能如苌叔那样誓死来效忠周朝,又无法像岳飞一样为了国家而战死沙场,只能追怀着故国旧朝,借历史人物、历史典故来抒发心中的苦闷之情。由此可以看到,民国建制标志着一个革故鼎新时代的到来,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文人们面临着前代士大夫所经受的考验,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去实现身份的重构,如何对垂死的价值信仰体系进行修正和更新,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文人承受了这种“以生为死”的生活,而没有选择慷慨赴死,他们这样选择有种种原因,最主要的借口是“有待”。这种“有待”,有对旧日王朝没落的惋惜及对其深深的眷恋,也有对传统文化逐渐衰亡的悲哀,以及对自己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感慨,无论哪种心态,实际上他们是很难有所行动的,因此,这样的“有待”实际上是一种虚无的等待。他们期待恢复旧制时机的来临,期待着理想的最终实现,等待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支撑。方尔谦的《和穆志》是这种等待心态的集中体现。“我生万世等尘埃”,我辈的短暂生涯在万世之间如同微小的尘埃,以至于“每极颠危”的时刻都不知要为自己感到悲哀。“屡欲上天扪日月,依然无地起楼台”,屡次要奋力一搏,妄图实现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然而现实的处境却只能带来深深的失望感,随着年华已逝,人已苍老,却只能空留遗憾。在诗作中,作者自嘲道:“闻道未能还大笑,夜深独坐画炉灰。”诗人把自己鄙薄为下士,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闻道而笑的愚迷之人,因此自己未能闻道,只能在夜深的时候,独自坐在炉火边,在无聊中拨弄燃剩的灰烬,在自嘲之中,更凸显了内心的失落之情。郑孝胥的《病起读经会》中“风雨敲窗病骨酥”是他暮年的实际情况,更是其当时心情的写照,“危行终哀世澌灭,胜天聊缓死须臾”心情极尽沉痛。“孱躯便是兴亡史,可信诗人有董狐”,诗人衰弱的身躯就是国家衰亡历史的见证,不知道世间还有没有像董狐那样的执笔而书的史官来记载这一切,郑孝胥借董狐之典故,表达对故国不再哀伤的同时,也追问了生存的意义。因此,如何生存以及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成了他们要追寻的终极意义。
二、难以割舍的政治梦想:新旧之间的情感转换与恋旧情怀
对于这些文人来讲,渴望恢复故国旧制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政治梦想,始终萦绕着他们,挥之不去。郑孝胥的《答石遗》中写道:“荒池老树皆吾梦,梦境故人圣得知”,“荒池”“老树”可以看作是故国的事物的隐喻,恢复旧制便是诗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虽说是自遗于世界,却又很难忘情于先朝。方尔谦的《题红杏青松卷》中“松自青青杏自红,老僧心迹有无中,诗人爱说前朝事,犹举符离咒魏公”便直叙自己此时的心情,这种心情便是“诗人爱说前朝事”,对旧朝仍念念不忘。
因此,一旦有成熟的时机,他们便会选择再次入世,图谋恢复故国。当张勋妄图复辟帝制在天津观望形势时,陈曾寿对此十分焦灼,屡屡催促张勋尽快挥师北上,实现复辟大业。事实上,妄图恢复旧制可以看作是他们以民间的身份对民国政治的一种较为激烈的抗争,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蕴含着对清王朝的深深怀恋,这种恋旧的文化情结多与故主的知遇之恩密切相关,有时这种情结甚至会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便是对新制度的激烈抗争。实际上,对于民国而言,辛亥革命虽结束了帝制,实现了中国的重大改变,但稳定有效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未能及时形成可以面对复杂局面的国家权力阶层,以及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机构来产生可持续的影响。后来在袁世凯的一系列妄图复辟帝制的活动中,民国的“共和”理想只剩下了一块招牌。文人们对于民国社会现实的切身体会强化了他们对于民国体制的怀疑。事实上,他们或讽刺时局或感叹乱世并非对昔日帝制的完全认同与对今日“共和”体制的完全反对,他们否定的是当今军阀混战中并不安定的现实状况,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君主立宪”甚至复辟帝制都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些人为此而倾尽全力。实际上,清朝晚期的政治统治并不是深得人心,加上多年欧美政治制度及文化思想传入中国,处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太可能对西方先进的改革完全抵制,他们对西方政体及民主共和也曾耗费心力,但进入民国,却发现远非理想中的政治稳定、富裕繁盛,再加上难忘旧主、怀恋传统等多种感性因素,因此,对民国制度反对尤甚。
事实上,这些文人的恋旧心态虽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意味,但在内心中的清王朝更像是一种旧文化的载体,在看似政治倾向浓厚的活动中,渗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情感,他们对于旧朝的不舍,更多追恋的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社会秩序。因此,对于苟活于世的文人来说,改朝换代不仅仅意味着政权的更迭,更象征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因此,当民国新的立身处世的法则与他们内心坚守的标准相距甚远时,以及民国的现实状况与他们对于“共和”的期望相悖离时,他们唯一的精神归宿便是回到过去,从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寻求灵魂的安慰。
三、出游与唱和:诗酒流连中难以名状的悲哀
在难以割舍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面对民国政治屡屡失望的心态下,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追寻那一份独有的出世情怀。从他们这一时期诗作的题目来看,便可知寄情山水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如郑孝胥的《壬子重九同吴剑隐陈介菴游徐园》《九日病愈出游》《朱游一首》,方尔咸的《孝质薄游平山匆匆遂别为诗送之》,陈宝琛的《展重阳同石遗默园宿狮子窝因过秘魔崖》等,一旦退出政坛不在朝为官,寄情山水,诗酒流连便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郑孝胥的《壬子重九同吴剑隐陈介菴游徐园》中“无山易败登高兴,得酒遥望失路穷”,虽然与友人畅游徐园,饮酒赋诗,但仍然无法排遣心中的寂寞。郑孝胥的《残春》是这种感伤与落寞之情的集中体现:春天本应该是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时节,在这样的时节中出游,本应是愉悦并充满希望的,然而,作者却用“残”来形容这样一个极富生机的时节。“残春绝可衰”,诗人竟然在春天中看到了衰败,残落的春天中也无心赏景,“落魄”“客居”成为内心中独特的体验。方尔咸的《孝质薄游平山匆匆遂别为诗送之》中:“不饮胡为醉,能诗已是穷”“断发入吴中,并有兴亡感”更是直接抒发了这种在诗酒流连中难以掩饰的落寞。陈宝琛的《展重阳同石遗默园宿狮子窝因过秘魔崖》中“成毁时则然,造物测或叵,君看初日丽,倏尔黑云里,却趁半晌晴,秘魔崖下坐”,世间兴亡的变幻就如同这阴晴不定的天气一样,“君看初日丽,倏尔黑云里”,而面对民国改制的现实,除了空悲伤之外也无能为力。其另一首《中秋对月》中“当年亦自惜秋光,今日来看信断肠,涧谷一生稀见日,初花却又值将霜”,赏月中回想旧朝的难忘时光,肝肠寸断,但时光流逝来去匆匆,旧日生活毕竟已经一去不返。文人们难以摆脱来自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失意、痛苦、落寞、感伤,于是想要找寻世外桃源来寻求解脱。陈曾寿的《月夜同李道人闲步》中“夜色钟柴门,二人自成世……归写良夜图,清冷难题字。”安静清冷的月夜中,与道人散步,可以暂时超脱尘世,享受二人自成的世界,寻找一种短暂的超脱。
从诗歌的艺术形式上来看,这些文人的诗作大部分属于格律诗,讲求格律的严整与结构的工整,但也有诗作风格的差异,有的抒情较为含蓄有的则较为直率。郑孝胥主张诗歌中要体现诗人的真性情,对此他反对过分雕琢,认为“于未下笔之前酝酿停蓄,使抑郁而后达,则中气有余而自觉过巧之为累矣”。在诗歌的创作体式上,郑孝胥推崇韦应物的诗作,认为其诗缘情而作,是至情至性之作,但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郑孝胥自己却并不能做到真正的“缘情”,不能直接袒露内心的真情实感,其原因在于郑孝胥一直渴望恢复故国,这种恢复旧制的心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能明朗地表达,使得其诗作偏于内敛和伤感。从诗歌体式上来说,郑孝胥的诗作以五言居多,其五言诗有意模仿孟郊的诗作,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中,他喜用“秋风”“暮雨”“黄昏”“夕阳”“残夜”等意象以衬托一种悲凉、荒芜、萧索的氛围使得诗作在冷色的意象和低沉的情感中有一定的含蓄性。就其诗风而言,清丽俊秀、雅健苍劲。与郑孝胥相比,陈宝琛的诗作显得萧然超脱。陈宝琛推崇韩愈、王安石,其七言歌行体的诗作较多,这些诗以写景为主,在对写景的细致描摹中抒发一种对于人世的哲思,而这种哲思又突出体现了看透世事之后的一种淡泊。
民国初期传统文人虽然经受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打击,却仍然坚持着“旧式写作”,并且借助了报纸杂志这一现代传媒平台与新的媒介方式时刻互动着,他们旧有的官僚身份已经转变为传统文人,旧体诗成了表达其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载体。在某种意义上,旧体诗更成了一种象征,既表达了对往昔价值的追怀也夹杂了对新的价值体系地试图认同与理解。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里一种独特的存在,是我们了解民国文学丰富性的重要面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