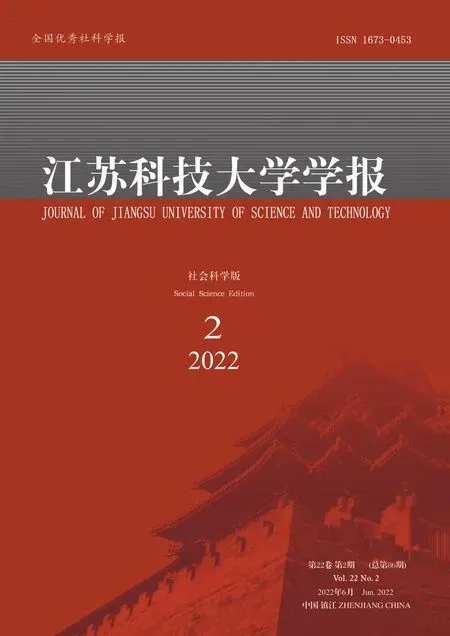美国汉学家英译《十二楼》的文化记忆研究
曾景婷, 奚琛珺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李渔(1611—1680)作品因其迥异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世俗美学思想以及充满中国风尚(Chinoiserie)元素的创作风格而深受西方读者欢迎。他的代表作《十二楼》(又名《觉世明言》)由12篇小说组成,每一篇小说都以楼阁名为题,12座楼阁既推动了情节发展,又暗示了故事主人公的命运,可谓情节跌宕,匠心独具,贯穿始末的江南园林式叙事方式体现出典型的“李渔”式审美风格。自1815年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首译至今,西方世界对李渔作品的译介从未中断,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除德庇时选译本之外,还有四个英译本,即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摘译《生我楼》(1841)、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K. Douglas)选译《夺锦楼》(1887)、茅国权(Nathan K. Mao)全译本(1975)和派屈克·韩南(Patrick Hanan)选译本(1992)。1975年,美籍华裔学者茅国权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唯一的《十二楼》全译本LiYu’sTwelveTowers,并于再版时将书名简化为TwelveTowers(以下简称“茅译本”)。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于1992年选译《十二楼》中的六篇,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ATowerfortheSummerHeat(以下简称“韩译本”)。在历史的纵深视阈下,两个当代译本有共性特征,但其在翻译策略、文化取舍、语言风格、小说体例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文化研究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两大任务,协调性旨在为交流者提供共时场域,而可持续性转向历时性,需要通过记忆来完成[1]。罗选民认为,文化记忆与翻译具有共生关系,一方面,翻译文本需要依靠集体记忆来完成;另一方面,文化传播与文化记忆紧密相连[1]。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西方学界记忆研究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是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符号象征、媒体传播、机构运作和社会实践等方式的反复运用而构建的具有传播功效并为成员间所共享的过往记忆[2]。中国文学典籍的世界化和经典化需要借助集体文化记忆才能实现,而现阶段研究多围绕个体文化记忆,在单一的译者研究或译本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1]。这种研究趋向造成了碎片化的个体记忆,阻碍了中国文学典籍的世界性、经典化进程。为此,笔者以韩译本和茅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李渔《十二楼》之《夏宜楼》的英语世界传播进行可持续性历时考察,从个体、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分析汉学家翻译的集体文化记忆,挖掘文学典籍国际传播的翻译资源,助力中国形象建构和文化传播。
一、 文化记忆的三个维度
记忆的研究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等哲人对于记忆的所思、所感便散见于诸多对话录、随感集中,如《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的“蜡板假说”(a wax block)将人的大脑比作蜡板,日常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像是在蜡板上刻上印章,蜡板表面越光滑,印记越深越持久;反之,蜡板表面越粗糙,越不容易留痕,越容易被遗忘[3]。早期对记忆的论述多来自个体的感性经验,缺乏理论框架和科学数据支持。系统的记忆理论研究源于现代心理学,以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为代表,重点从个体维度来探索记忆,记忆被当作一种精神性的实在,存在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一般是短时个体记忆,多是研究记忆得以形成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强调个体记忆的自主性而非建构性[4]。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第一次从社会学视角对记忆展开了系统研究,促成了记忆研究从个体层面转向集体层面、从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也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5]39。他也同时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5]49。换言之,这个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仍然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生物学属性上的个体。哈布瓦赫的理论虽仍未逃离“个体记忆”的樊笼,但与最初自主性、自为性、自发性的个体记忆相比,此时的集体记忆已逐步开始形成一种规范和约束,初具建构性、生成性、自觉性。在“集体记忆”研究基础上,人类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社会记忆”这个概念,并将问题聚焦于如何传播和保持群体记忆。在康纳顿的理论视野中,集体上升为社会记忆的主题,集体不再是一个群体中个体记忆的集合,而成为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记忆。虽然康纳顿在概念建构上也缺乏完整性,但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这一脉络的演进,体现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到“集体的记忆”的本质突破[6]。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研究证实,操纵记忆的不是一个“集体灵魂”,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头脑”,而是一个“借助符号和象征的社会”——记忆之场[7]。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记忆女神图集”与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相似,都是将象征与符号作为记忆主体,但他们都未使用“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理论源起20世纪末,倡导者为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在阿斯曼的文化视阈中,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为记忆主体,通过文化载体进行传承。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中,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包含某种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并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8]。
最初的“个体记忆”为记忆提供了最基本的生物载体,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研究了记忆形成的社会基础,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探讨了记忆的传承,瓦尔堡与诺拉提供了具体的文化符号,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则是尝试把三个维度——个体、群体(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起来[8]。换言之,“文化记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宽泛概念,涵盖了个体、社会与文化三个维度,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文化记忆促进了个体和集体形象的建构与身份认同。个体记忆充当了一切记忆的基础,社会维度的记忆改写并影响个体记忆,文化记忆则充分解释了记忆在社会和个体维度上的涵义及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二、 韩译本与茅译本的文化记忆比较
(一) 个体维度
个体作为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是记忆的根本载体。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经历的以及所具有的某些能力都是构成日后记忆的基本元素。“记忆与回忆虽受制于组织其回忆的‘框架’,但主体仍然是单个的人”[9],因而在译介活动中,虽然译者受制于社会框架,但作为独立个体,其个体记忆仍处于主导地位,对译本生成的影响不容小觑。总体来看,《十二楼》韩译本与茅译本的翻译在个体取向上大相径庭。茅译本面向译入语普通读者,重点关注阅读难度和读者接受程度。为此,茅国权在保留故事情节基础上采用“译述”式翻译,对原文内容进行大量删减与改写,译本仅有数十页篇幅,旨在扫清文化交流障碍。韩译本也需要顺应译入语国家的读者阅读习惯,在整体风格上不失为一部语言地道的英文小说。然而韩南作为一位专治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他的翻译往往与研究相辅相成,体现出浓厚的专业化色彩。因此,韩南在传达中国文化和民俗民情时基本采用意译或释译的方式,这样做是为了弥补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意象缺失。在翻译过程中,韩译本运用增添注释的手段替代了茅译本的删减、修改,这直接导致韩译本注释的数量、长度、专业化程度、关联度等都明显高于茅译本。
“翻译的过程即记忆的敞开,是译者调用自己关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记忆,并用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10]虽然译者受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译者作出的个体选择最终决定了整个译本的走向。译者的选择必然是一种特定的目的性行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从材料的选取到词汇的运用,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而这些通常由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根据既定的目的进行定夺”[11]。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雷勤风(Christotopher G.Rea)在茅译本前言中指出,“尽管两种译本追求的目的并不相同,但首先都是为了娱乐、消遣”[12]5。在此基础上,茅国权之所以采用“译述”式英译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读者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英文读者以及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外国学生。若对原文中的回目标题、入话、诗歌或者叙述过程中的“离题”进行保留,必然会使对传统白话小说体裁陌生的读者感到困惑甚至厌烦,在没有注释补充说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体会李渔小说中巧妙的情节设置和技巧性“离题”。反之,韩南采用“译研”式英译策略,虽只选译其中六篇,但保留了所选篇目中的诗歌、回目标题、入话、叙述过程中的“离题”以及篇末的杜濬点评,对原文的保留完整度极高。雷勤风认为韩南此举旨在“保留李渔故事中最独特的部分——叙述者的声音”[12]4,在确保完整性的前提下,使读者发现隐藏在文本中的文学手法和思想。作为李渔作品的重要发掘者,韩南通过对李渔多部作品的研究,试图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真实的李渔,再借助译本将其反馈给读者。译者在其研究著作《创造李渔》(TheInventionofLiYu)中对这种译、研并举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论述。此外,译者主观情感的介入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曾虚白认为,“化来化去,译者总化不掉自己内心的弦线所弹出来的声音,永远摆脱不了主观的色彩”[13]。茅译本对李渔的褒贬虽未直接指明,但在序言中是褒是贬已然明了。在茅国权看来,李渔只是一个“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说书人),“中国的传统小说是街头巷尾、公共集会和娱乐场所的直接产物”[12]36。茅国权认为,李渔虽在传统白话小说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删减说书套语、减少故事情节的重复等,但本质上并未脱离街头巷尾的说书人之流。在人物刻画方面,李渔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扁平的,缺乏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与西方文学标准相冲突。反观韩译本,则处处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热衷以及对李渔的欣赏。韩南在译本序言中盛赞《十二楼》是李渔最好的小说类作品,并对原作的题材、结构、创作手法以及译本的翻译策略等进行了介绍。那些被当作“题外话”或“离题”的部分,在韩南看来实则是李渔人生态度以及文学思想的具化。如在《夏宜楼》第二回中李渔对千里、显微、焚香、端容、取火诸镜的描写(此处仅节选千里镜描写片段)。
千里镜
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身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数十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者更觉分明。真可宝也。[14]57
韩译:Thousand-Li Glass (Telescope)
This glass employs several tubes of different thickness, of which the smaller ones fit inside the larger. To adjust it, you extend or react the tubes. The reason it is called a thousand-li glass is that the lenses are set at the ends of the tubes, and when you use it for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nothing is beyond its range. Although the termthousandliis an exaggeration—you can’t really see from one kingdom into another—if you try it inside that range, you will find the claim not all fraudulent. If you use it for looking at people or things at a distance of several hundred yards to a few li, you’ll find them more distinct than if they were sitting opposite you. It is a genuine treasure.
注: Aliis about a third of a mile.[15]
茅译:删除
虽然作为汉学家的茅国权与韩南都采用译、研并举的方式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不过两人所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功用都烙有深刻的个人印记,且这一印记清晰地体现在译作的呈现方式上。茅国权在翻译千里镜及其描写时,仅在首次出现时将其译为“thousand-mile mirror”,再次出现时则用“magic mirror”或“telescope”代替,后文描写吉人在古玩铺前试玩西洋千里镜的有趣经历也被当作无关情节略去不译。相反,韩南却将西方文化中不对等的意象“里”音译并辅之以注释,全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韩南对望远镜曾这样评价,“创造性地实用东西——正如在李渔时代才引进中国不久的望远镜——也会构成另外一种新奇”[16]58。亦或是“望远镜,在主人公将其当做如此有创造力的用法之前,在中国一直被视作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董”[16]83。韩南表面上是在赞赏瞿吉人的聪明、机灵,一件被大家束之高阁的古董被他开发出了新用途,实则是在赞扬写书人李渔巧妙的情节安排及其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还在书中评价道:“《夏宜楼》展示了一些李渔与众不同的才能——新奇的观念、精巧的结构、巧妙的滑稽、性感的描写。”[16]83这些评价无不流露出他对李渔的欣赏与赞美,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将“真实”的李渔展现给译入语读者。
(二) 社会维度
个体记忆为社会建构群体记忆提供素材和基础,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息息相关。一方面,个体记忆在历史跨度中不断改写社会记忆;另一方面,社会记忆也同时影响着个体记忆。《十二楼》是李渔所有作品中英译时间最早、翻译史跨度最长的小说集。自1815年德庇时爵士始译到1975年茅国权全译,再到1992年韩南选译,前后虽跨越170多年,却历久弥新。《十二楼》蕴含的文人雅趣和生活哲理备受西方汉学家关注,李渔的作品也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当代备受推崇,具有经典化趋势。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译活动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并立,并非静止的、恒定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翻译不仅是译者个体记忆的映射,更是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不同记忆的再现。记忆总是与记忆者的社会背景密切关联,作为翻译活动中的记忆主体,不同时期的译者总会囿于其所处时代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譬如政策法规的兴废、社会政治的变革等都容易造成译者记忆形态的差异,以致译本呈现全然不同的风貌。韩译本与茅译本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具体名称的翻译上。笔者对两个译本中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称以及楼名的译法整理如表1。

表1 《夏宜楼》中专有名词英译对比
茅译本中的人名、楼名、地名、朝代名称等都采用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简称“威氏拼音法”)进行音译。威氏拼音法起源于1867年,是由英国人威妥玛等人合编的注音规则。威氏拼音法自制定以来为当时中外学者广泛使用,却一直未成为官方标准。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中国的地名改用汉语拼音拼写。此后,汉语拼音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977年和1979年,联合国分别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地名与人名的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法的国际标准。从拼音法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诞生于1975年的茅译本,虽已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但考虑其译入国家并未完全摒弃原有的威氏拼音法,因此在译本中依旧继续沿用。而1992的韩译本距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法》已有34年,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接纳并采用新方法。同时,作为一项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方案》必然会对国外学者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韩译本中除对“娴娴”以及“夏宜楼”采用意译之外,其他则全部采用了汉语拼音的音译。
政策法规的更替主要作用于文本的微观层面——造成两个译本中某个具体字词或段落的偏差,而社会背景的改变则会影响译者对于译本宏观层面的把控。按照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理解,“个体记忆具有或者说需要社会的框架,它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和促进”,“记忆并不是个体活动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才能完成,特定的社会框架促成了相应的个体记忆和回忆”[17]。由此看来,若想深入、全面地了解译者本身,单纯从个体记忆进行分析则稍显片面,而应将其放置于从属的集体中——译者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对两个译本的时代背景进行比较,1975年的茅译本诞生于冷战时期,随着美、苏军备竞争的过度消耗以及日本、欧共体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国逐渐丧失其经济霸主地位,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发展。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中美邦交逐渐走向正常化,越来越多的西方普通读者急于了解中国。为此,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译介的主要特点是“文献性”而非“文学性”传播。为了顺应时代要求,茅译本运用“译述”式策略,用西方小说体制代替原作的拟话本小说体制,删去“旁枝末节”,保证“情节至上”,译文通俗易懂,故事发展脉络清晰,有效促进了《十二楼》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与传播。1992年问世的韩译本则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海外汉学研究更加关注中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以韩南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为了帮助译入语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译者在翻译中保留了承载中国文化的典故或成语,采用添加注释的方式阐释其背后隐藏的内涵,尽力保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框架下的独特 “文学性”。由此可见,韩南和茅国权都努力向美国推介中国文学与文化,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不同,加之译本受众的专业程度不同,因此在翻译策略上体现出明显差异。
(三) 文化维度
“文化记忆是一种能够巩固和传播集体形象(社会群体、民族或国家)并使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对这一形象产生认同的记忆,而这种集体形象的建构则依托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符号和象征(文本、意象、仪式)。”[4]翻译不仅架构了译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更架构了作者与读者即原作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原作一经问世,便恒定不变,但随着译者的改变,或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制于不同记忆作用的译者会随之改变翻译的呈现方式。因此即便是相同的原文,读者也会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人物形象、社会制度乃至思想文化。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而不同读者对《十二楼》有不同解读。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逐渐从对原作故事情节和社会生活的介绍转向对原作典故、习俗、制度等文化现象的探究。
《夏宜楼》是一部以千里镜(即望远镜)来穿针引线的爱情故事。如果仅关注故事情节的铺陈叙述,读者往往会被男主人公巧妙运用千里镜赢得佳人芳心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忽略作者对女主人公娴娴的褒扬之情。“嫺(即娴),雅也——《说文》娴:形声。从女,闲声。”[18]其本义为“文雅”,即柔美文静,庄重不轻浮。“娴”字所刻画的是古代知书达理、举止端庄的大家闺秀形象。而在原文中,李渔的女主角詹娴娴的确具备女性的一切美好品质,但同时又不同于传统封建主义女性形象。她聪慧果敢,胆大心细,有主见。原文有五处对詹娴娴的外貌及性格描写,如“虽生在富贵之家,再不喜娇妆艳饰,在人面前卖弄娉婷”[14]52;“自己知道年已及笄,芳心已动,刻刻以惩邪遏欲为心”[14]52;“娴娴恐怕呵斥得早,不免要激出事来”[14]53;“娴娴不肯轻恕,只分个首从出来”[14]53;“亏得他自己聪明,有随机应变之略”[14]64。由上例可见,人物性格与其名字中的“娴”字含义形成鲜明对比。李渔笔下的“娴娴”绝非终日端坐于家中只知读书写字或女工绣作的大家闺秀,而是聪明伶俐、秀外慧中、有勇有谋、大胆追求爱情并勇敢抗争古代婚姻制度的新时代女性,这完全不同于古代女性唯命是从的形象。茅国权将“娴娴”两字音译为Hsien-Hsien(见表1),虽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但却遗漏了作者藏于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茅译本刻画了一个家教严格、规行矩步的女性形象,与原作天然美质、冰雪聪明的形象相差甚远;而韩南用与中国文化含义对等的西方名字“Serena”替代音译“娴娴”,增加了译本的陌生化效果,“Serena”来源于拉丁文,意为“平静、安宁、祥和”。此处韩南看似未忠实于原文,但选取与“娴娴”含义对等的西方名字,有效保留了名字背后的意义以及李渔所期望达到的反差效果,即作者对于女性固守封建礼教、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反讽。
此外,两位译者在翻译女主人公的外貌、性格的相关描写时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娴娴自知年已及笄、自觉防闲”[14]52,这一遏制芳心萌动的聪慧与自律被茅国权改写成“Having nothing more interesting to do”。“娴娴……佯为不知……直等衣服着完之后方才唤上楼来,罚他一起跪倒”[14]53,表现出娴娴想要惩罚狡婢顽徒却又怕生出事端的玲珑心思,该部分却被茅国权当作无效情节全部删除,且在译本中多次用“strong moral principles” “strict family discipline” “puritanical”以及“severity”等词汇来形容娴娴,刻画出了一个家教严格、规行矩步的女性形象,而对原作中聪明伶俐、足智多谋的人物性格却有所淡化。女性形象的弱化使得茅国权译本中的男性角色得到强化,娴娴在这段才子佳人的美满故事中所做出的努力也化为泡影,这一出男女主人公争取幸福的佳话在读者眼中也变成了男主人公利用千里镜,骗过娴娴、媒婆以及詹笔峰,最终抱得佳人归的笑谈。反观韩南译本,虽然和茅国权译本一样,译者都省略了对娴娴的外貌刻画,但相较于茅国权将其简单译为“beautiful and graceful girl”,韩南分别用 “gorgeous” “natural”“unaffected”三个词替代原文的“秾桃艳李之姿,璞玉浑金之度”[14]52,将娴娴的天然美质、未经修饰而容貌俊美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来。同时,韩南在翻译“不喜娇妆艳饰”[14]52“只以读书为事”[14]52时,以“a girl of exemplary rectitude”以及“restraining herself without parental control”与茅译本的“无所事事”(having nothing more interesting to do)的翻译形成反差,将娴娴端庄背后的自省与自律描绘得恰到好处。显而易见,韩南着力传达李渔的写作技巧以及如何建构不同于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由此,一位独具匠心的小说家和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家——李渔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两个译本对于娴娴这一女性形象的不同建构,势必会影响读者对原作的解读,进而也会造成读者对于中国明末清初世情百态理解的偏差。
三、 结语
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文化交流的需求以及各方社会、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带来的国际变化,译者势必采用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策略。笔者根据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三维度,分别从个体维度、社会维度与文化维度对《十二楼》的韩译本与茅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在整体的翻译风格与具体的英译策略上迥然相异。茅译本整体沿用英文短篇小说体制,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与可读性,采用“译述”式英译策略,关注故事情节,大量与情节无关的内容被删减。韩译本在形式上对原作的话本小说样式予以保留,力求完整还原李渔作品的艺术风格,删减和改动较少,采用“译、研”式英译策略,音译、直译与意译结合,释译与删译并重,以期保留原作中特有的中国元素[19]。究其原因,作为一个独立的记忆个体,译者的翻译目的及其在翻译活动中形成的主观感情色彩都会影响译本的最终产出。对于特殊的目标读者——普通民众以及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来说,“译述”不失为最有效的翻译手法,因为富含趣味性、教育性的短篇故事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与更大的吸引力。韩南译、研并举,研究作品的翻译已然成为研究的重要部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严谨性。他对李渔艺术风格的再现更利于在英语世界还原李渔作品中最独特的部分——叙述者的声音。此外,茅国权对李渔的似褒实贬与韩南对李渔的欣赏与赞美形成鲜明对比,从译本中也可以看到译者无意识流露出的主观感情色彩。从社会维度来看,译者虽是独立的个体,但无时无刻不受到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关系的影响,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制定与更迭对译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字、词、段落或章节,而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改变必然使译者在宏观层面体现出“文化无意识”,进而影响译者的主体选择。译者整体译介风格与翻译策略的差异传达给读者的则是不同的文化效果。总之,韩译本和茅译本能给予当前中国典籍海外传播以方法论启示,国内译者和研究者应结合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势做好典籍外译的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