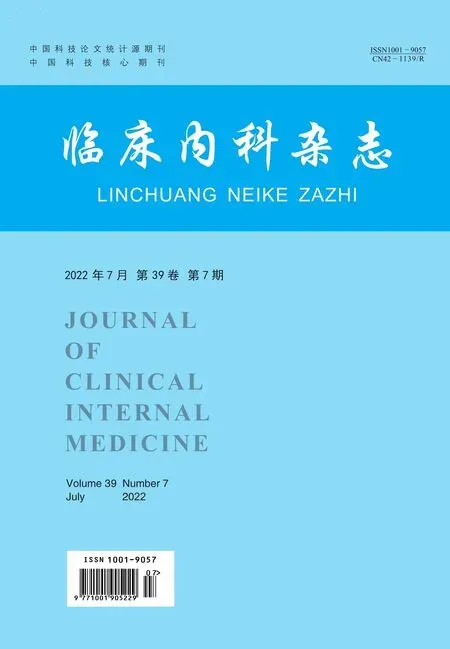原发脾脏的卡波西肉瘤一例
王艳军 赵传杰 马广贞 张磊 盛秀云
患者,男,50岁,因“腹胀10余天”于2020年7月9日入院。患者10余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部撑胀不适,以脐周部为著,无恶心、呕吐、烧心、反酸、腹痛、腹泻、黑便,进饮食量较前减少,伴有消瘦,行腹部超声检查提示脾脏肿大并异常回声,轻度脂肪肝,遂收入我院。既往体健,无相关病史。母亲健在,父亲死于脑出血,兄弟体健,无家族性遗传病史。体格检查:贫血貌,神志清楚,皮肤及黏膜未见出血点、瘀斑、血管瘤等。心肺听诊无明显异常,腹肌稍紧,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脏肋下未触及,脾脏肋下6 cm。实验室检查:血常规:WBC计数 7.73×109/L(4.00~10.00×109/L,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以下相同),RBC计数 3.36×1012/L(4.00~5.50×1012/L),血红蛋白(Hb) 92 g/L(120~160 g/L),PLT计数 20×109/L(100~300×109/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2.99%(0.50%~1.50%),乳酸脱氢酶472 U/L(109~245 U/L)。肝肾功能、电解质、胰腺酶三项(血清脂肪酶、淀粉酶、胰淀粉酶)、男性肿瘤筛查、甲状腺功能三项(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贫血三项(血清铁蛋白、叶酸、血清维生素B12)、感染四项(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HIV抗原及抗体)、自身免疫抗体、血β2-微球蛋白、尿常规、大便常规均未见异常。腹部超声检查结果示脾脏肿大并异常回声。骨髓涂片及骨髓活检结果示:骨髓增生较活跃(约80%),粒红比例减小,均以中幼及以下阶段细胞为主,巨核细胞不少,分叶核为主;淋巴细胞散在分布,倾向反应性;局部纤维血管增生。2020年7月25日上腹部MRI结果示:脾脏体积明显增大,信号不均匀,内见散在多发斑片状T1 Dual、fs T2高或低信号灶,DWI呈高信号,静注GD-DTPA后呈相对低信号。考虑为肿瘤性病变,淋巴瘤可能性大(图1)。患者于2020年8月7日输注PLT后于全麻下行腹腔镜下脾脏切除术。术中探查:脾脏被大网膜包裹并致密粘连,分别位于左腋前线(5 mm)、左锁骨中线(12 mm)、右腋前线(12 mm)、右侧锁骨中线(5 mm),充分分离粘连后可见脾脏体积增大,呈花斑样改变,游离脾脏上下极,完整剥离出脾脏(图2)。术中取脾脏组织行病理活检(图3A、B)。根据上述病理检查结果,脾脏梭形细胞增生,间质出血,结合免疫组化,符合卡波西肉瘤(KS,WHO分类为中间型血管肿瘤,低度恶性)。免疫组化结果:CK(-),ERG(+)(图4A),CD31(+)(图4B),CD34(+),CD8(个别细胞+),FLI-1(+),Ki-67(10%+),D2-40(灶性+),EMA(-),HHV(-),EBER(-)。术后患者病情好转出院。2020年9月4日患者因出现皮肤、巩膜黄染,伴浓茶尿、食欲减退再次入院。体格检查:贫血貌,皮肤、巩膜重度黄染,移动性浊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WBC计数29.01×109/L,中性粒细胞77.7%(50%~70%),RBC计数2.04×1012/L,Hb 60 g/L,PLT计数36×109/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7.02%;肝功能:ALT 90 U/L(0~33 U/L),AST 127 U/L(0~32 U/L),总胆红素229.8 μmol/L(3.4~24.0 μmol/L),直接胆红素158.0 μmol/L(0.1~6.8 μmol/L),间接胆红素68.00 μmol/L(1.71~15.22 μmol/L),白蛋白30.7 g/L(34.0~54.0 g/L),谷氨酰转肽酶320 U/L(0~40 U/L),碱性磷酸酶712 U/L(35~105 U/L),总胆汁酸167.1 μmol/L(0~15.0 μmol/L),唾液酸914 mg/L(456~754 mg/L),乳酸脱氢酶884 U/L。凝血六项:凝血酶原时间18.90 S(11.00~14.00 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67.50 S(28.00~43.50 S),凝血酶时间无异常,纤维蛋白原1.52 g/L(2.00~4.00 g/L)。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结果均为阴性。尿常规:胆红素(+++)。腹部超声结果示:肝脏明显增大、回声不均;肝右叶低回声结节;腹腔积液。上腹部MRI结果示:1.符合脾肿瘤切除后改变;2.肝内弥漫性异常信号影,参阅2020年7月25日MRI片,考虑为多发肝转移瘤。入院后给予对症治疗,患者症状逐渐加重,精神差,于2020年9月6日自动离院。出院后7天患者因肝衰竭死亡。

图1 患者2020年7月25日上腹部MRI检查结果 图2 患者2020年8月7日行脾脏切除术:切除脾脏的大小为22 cm×18 cm×12 cm,表面部分被膜缺失,切面暗红,见多处灰白灶

图3 患者2020年8月7日脾脏组织病理检查结果:A:低倍镜下组织均呈多结节状,边界清楚,由增生的梭形细胞组成,伴间质出血[苏木素-伊红(HE)染色,×100];B:高倍镜下可见增生的梭形细胞纵横交错排列,被含有RBC的裂隙样腔隙分割,呈筛孔状或蜂窝状,在梭形细胞胞质内或细胞外可见嗜伊红色透明小体,梭形细胞之问见外渗的RBC(HE染色,×200)图4 患者2020年8月7日脾脏免疫组化结果:A:ERG阳性;B:CD31阳性(En Vision法,×100)
讨 论
KS是一种具有局部侵袭性的内皮细胞肿瘤,于1872年由kaposi首次报道,又称为多发性特发性出血性肉瘤。KS主要表现为皮肤的多发性斑点状、斑块状或结节状皮损,初始发生于足部和小腿皮肤的多发性蓝色斑块或结节,并逐渐向肢体的上部发展。除了累及皮肤、黏膜外,KS最易累及淋巴结和胃肠道[1]。部分患者可有内脏的广泛受累[2],内脏病变可先于皮肤的病变或者单独发生而不伴有皮肤病变[3]。脾脏最常见的非造血系统肿瘤为血管肿瘤,常见的有血管瘤、淋巴管瘤、海岸细胞血管瘤和血管肉瘤,其他少见的有KS、血管外周细胞瘤和血管内皮细胞瘤等。卡梅现象(KMP)是在脉管肿瘤和脉管畸形的疾病基础上伴发PLT减少、微血管性贫血和消耗性凝血功能障碍的一类临床表现,病程凶险,患者病死率高达30%[4]。常见的致死原因包括凝血功能紊乱、严重感染导致败血症及肿瘤侵袭重要器官等。本例患者以腹胀为首发症状,进一步检查发现贫血、血小板减少、脾脏增大,影像学检查结果支持脾脏恶性肿瘤,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证实为KS。后患者再次出现PLT减少、溶血等表现,考虑合并了KMP,病情进展快,出现肝脏的广泛侵袭,导致肝功能衰竭,凝血功能紊乱最终导致死亡。
目前KS发病确切病因不明,但与人类疱疹病毒8(HHV8)的感染关系密切,几乎100%的病变中都存在这种病毒,因此该病毒又称为KS相关性疱疹病毒(HSHV)。其他因素如免疫抑制可能对KS发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周小鸽等[5]报道,通过采用单链探针原位杂交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在14例KS患者中共检测到10例(71%)有HHV8感染,29%没有HHV8的感染。因此,虽然KS与HHV8存在密切关系,但是也有阴性的患者,临床一定要综合分析。如本例患者,病理检测结果中HHV8为阴性。
在病理方面,显微镜下最典型的KS特征为梭形细胞形成含有RBC的裂隙,病灶内混有淋巴细胞、含铁血黄素细胞和其他炎症细胞。免疫组化结果显示Ⅷ因子相关抗原、CD31、CD3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血栓调节素、白细胞粘附分子-1等呈阳性,D2-40始终呈阳性。本例患者脾脏组织病理检查在高倍镜下可见增生的梭形细胞纵横交错排列,梭形细胞被含有红细胞的裂隙样腔隙分割,呈筛孔状或蜂窝状;且免疫组化结果显示CD31(+),CD34(+),FLI-1(+),ERG(+),D2-40(灶性+)。
KS是一种血管肿瘤,由于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几乎所有病变都是二倍体[2],因此,似乎支持其为增生性病变。但病变的克隆性和有些病变有明显的侵袭性行为,又支持病变性质为肿瘤性[6-7]。在良恶性方面,诊断病理学在皮肤章节中的血管或血管内皮细胞及淋巴管分化肿瘤中,又把KS归为恶性肿瘤[8]。而在软组织疾病章节WHO分类中认为其是中间型血管肿瘤[9],本例患者的诊断也是依据了WHO的分类标准。
在治疗方面,根据KS疾病的不同阶段、发展类型、临床类型和免疫状况而不同。若是局限性结节患者或内脏严重累及时,可考虑外科切除。如局限于皮肤或粘膜及典型的结节性病变,放疗效果也较好。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足叶乙甙、紫杉醇、阿霉素、雷帕霉素、吉西他滨等。KS的治疗方案还未有标准化指南指导,远期疗效不佳。目前,新治疗靶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阻止成瘤过程、炎症调控、阻止病毒复制、细胞周期的调控等方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