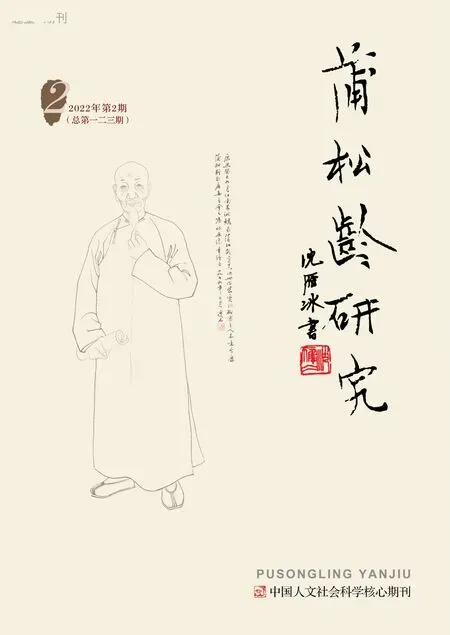奇幻、冲突和喜剧元素的改编彰显
——新近出现的聊斋题材网络电影中的审美症候探讨
赵庆超 蒲建工
(1.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2.淄博市博物总馆 蒲松龄纪念馆,山东 淄博 255120)
作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聊斋异志》凭借其丰厚蕴藉的审美魅力产生了不绝如缕的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在《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等诸多的续书和仿写行为上,还存在于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而生成的影像改编中。自从1922年任彭年把聊斋小说《劳山道士》改编为电影《清虚梦》以来,聊斋题材电影的改编就长盛不衰,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多元生成气象,也彰显出《聊斋志异》独特深厚的艺术个性和文化价值。聊斋题材电影的赋魅建构不仅与其原著小说的形象设置和叙事布局密切相关,也与不断更新的改编观念和制作技术相互关联。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影像生成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网络传播平台的扩展开放,聊斋题材电影也改变了之前单纯依靠院线发行传播的单一化模式,在制作生成和审美传播上更显多样化和便捷化趋势,既有《画皮》(2008)、《画壁》(2011)、《捉妖记》(2015)、《神探蒲松龄》(2018) 等先依靠院线传播再逐渐转向电视、网络输送的改编大片,也有《侠女》(2006)、《聂小倩之尘缘未了》(2014)、《伏狐记》(2018)、《神龟岛》(2021) 之类的主要依靠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各大网络平台传播的中小成本电影。聊斋小说影像改编遇上了网络空间传播,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审美艺术转换话题,它不仅为聊斋文化的审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同样产生了难以回避的艺术改编短板。因此,笔者拟就新近推出的11部聊斋题材网络电影(见附表)为探讨重心,并试对这一改编现象作深入论析。
一、凸显奇幻色彩
与胡金铨的《侠女》(1971)过多地指涉历史和吴佩蓉等人的《胭脂》(1980)重在现实隐喻的改编策略不同,新近的这11部聊斋题材网络电影更加凸显改编中的奇幻元素,卸掉过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负,转向尚奇重怪的幻境营造,从而去拉动大众化、浅思维娱乐的审美接受消费,这成为了诸多改编者不约而同地采用的呈现方式。《绛妃》是聊斋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描写“余”在毕家坐馆倦极入梦,被两位女郎带到仙界,完成了受花神绛妃之请代写讨伐封家女子(即风神)檄文的任务,而回到人间的故事。整篇小说故事勾勒简单明了,取自蒲松龄散文创作的檄文反而占了大半个篇幅,蒲松龄借赋体散文指斥强权,为弱者张本(“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歼尔豪强,销万古风流之恨”)的托物言志心态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据此改编的电影《妖手摧花》(2020)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充了原作的描绘空间,不仅通过唯美浪漫的影像语言展现出绛妃等人居住的似真似幻的三重天外花仙阁的天上世界,还以捕快宋逸尘追查吸血案的线索彰显现实人生的复杂故事,还有人、仙联手对付树精、花妖的邪不压正的主题来演绎人、仙、妖之间的跨界恩仇和情缘。这种故事内容和描绘空间的增补显然凸显和放大了《聊斋志异》的奇幻书写和现实隐喻特征,在影像叙事“熟悉的陌生化”呈现中满足了人们感性化的观影期待和视觉诉求。
同时,这11部影片中还出现了热衷于讲述与海有关的异域离奇故事的改编倾向。在《人鱼缚》(2020)、《罗刹劫》(2020)、《海大鱼》(2020)、《龙无目》(2020)、《神龟岛》(2021)五部改编影片中,改编自聊斋小说《白秋练》的《人鱼缚》(2020)虽然描绘着江边人、鱼相恋的故事,但又通过对人、妖殊途好事多磨得曲折描绘,对龙三太子居住的龙宫的详细布置,还有正邪力量决战幻境的虚实建构,进一步扩充了原著的审美意境;《罗刹劫》(2020)删减了原著《罗刹海市》对龙的国度的故事叙述,以出海的泉州书生马骥与罗刹国夕月公主之间的奇特恋情为生长主线,再配上侠客司徒空与夜叉国赫奴公主之间的情缘故事,着力于罗刹国的美丑颠倒的异域风俗描绘和宫廷恩怨,演绎了一段波澜起伏的海上传奇;《海大鱼》(2020)在演绎同名小说海上传奇的基础上,又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河伯娶媳和《庄子·逍遥游》的“北冥有鲲”中汲取灵感,构建故事情节,通过被送去祭海神的新娘阿狸最终识破冰棺新娘的秘密,并与半人半兽的海岛主淼(实为海大鱼)发生的情缘故事,再生产出一段人、鱼(怪)之间惊天地泣鬼神的唯美神话;《龙无目》(2020)填充同名原著的简略叙述,增加前来降雨的龙女海兰珠与沂州府衙捕头陆海笙之间的龙、人之恋,并植入兔精、树妖、东海龙宫司时官蟹云等多个异类形象,在重重险阻和误解中留下了男女主角天上人间、不复相见的悲剧隐痛;取材于《仙人岛》的《神龟岛》(2021)描写书生王勉乘船来到宛如仙境的海岛上巧遇仙女芸芷,从而渐生情愫共同斩妖除魔,上演了一段人、仙相识、相恋却好梦难圆的爱情悲剧,受黑海老妖控制的神龟重获自由,岛上再现安静祥和,但已与原著中男主角借道士之神力遇仙对句、返俗归仙的神奇书写相去甚远。
概而言之,网络电影在改编聊斋小说时重奇重幻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话语症候,奇特的异类形象的出现和诡异的审美幻境的构建成为影片的重要呈现亮点。与聊斋原著相比,它们“写鬼写妖”的描绘能力增强了,“刺贪刺虐”的现实指涉在萎缩,这些影片虽然也重在指涉现实,但不再指向过于沉重的现实讽喻,而多偏向于编织多角男女之间的复杂情缘或唯美浪漫的爱情,设奇造梦成为电影制作的重要预设内容。由于指向网络平台的传播输送和中小成本的造价预算,也使得它们在编造奇幻元素时难免粗制草率(如诸多运用特技赶制出来的妖怪符号),难掩人工刻意雕琢的复制印痕,使得这些奇幻常常格局受限,绚丽有余而底蕴不足,反而成为弘扬聊斋文化时的艺术短板,应该值得警惕。
二、强化对立冲突
纵观这11部改编影片,它们都瞄准了网络播放的娱乐消费性,在剧情设置上一边强调男女主人公之间富有奇幻色彩的唯美跨界恋情,一边又常常以富有戏剧性的正邪对立、冲突不断给跨界恋情制造“麻烦”,从而延宕美好大团圆结局的到来,甚至还会出现人妖殊途、美事难成的遗憾结局(如《奇花记》《神龟岛》《龙无目》《人鱼缚》等),因而奇幻爱情与正邪故事并行不悖,成为了这些影片的显在特征,而正邪对立冲突的设置不仅增强了电影文本的情节张力,也形成了影片多重风格的重要元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片虽然在奇幻影像中重视唯美环境的营造,其实并无走向诗化电影的风格意向。聊斋小说脱胎于传统古典文化,常常以美妙的诗化语言建构形象和意境,如《葛巾》中两位由牡丹幻化而成的少女带来的清新之美,《连城》里乔生眼中的连城“秋波转顾,启齿嫣然”的临别一笑,《西湖主》中粉垣围沓、朱门半启、高拂朱檐、香花扑人的精致院落,都呈现出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审美雅趣,但这些往往都不是网络电影改编的重点,它们的好看更多定位在故事情节的悬念设置和叙事节奏的紧凑集中上,类似于《城南旧事》(1983)、《边城》(1984)、《那山那人那狗》(1999)、《暖》(2003)等影片呈现的结构松散、诗化唯美的艺术片风格不是其预设的审美归宿,奇观与动作迭出的商业片小制作定位,才更加契合网络平台传播的快捷化特性。
因此,为了展现富有冲突性的曲折情节,这些聊斋题材电影的改编者常常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强化正邪之间的力量争斗(如《聊斋之极道天师》《美人皮》《聊斋新传之画皮人》《人鱼缚》),或者是增设正邪之间的拼斗情节(如《罗刹劫》《大梦聊斋》《海大鱼》《神龟岛》),使得整部影片不断展现情节行进的爆发点,以一个个铺垫的悬念和小高潮推向抵达结局前的大高潮。正邪力量比拼往往在最后一战终见分晓,为非作歹的恶势力遭到报应,被正派力量歼灭,而正派力量虽受到损伤,但总有向善的火种得以保存,邪不压正的主题由此得以弘扬。男女主人公要么花好月圆终成正果,要么人妖殊途误会难解;或一方为解救另一方而献出生命,最终好事难全,空留下人生的遗憾与爱情的绝响。但是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力量软弱的个体,男的大多是身体单薄的书生(如《美人皮》里的乔俊昱、《罗刹劫》里的马骥、《神龟岛》里的王勉),即使为县衙的捕快(如《龙无目》里的陆海笙、《妖手摧花》里的宋逸尘)、落魄的武将(如《人鱼缚》里的柳梦白)和朝廷的官员(如《奇花记》里的常在田),面对着强大的妖魔势力也常常一筹莫展,需要借助外在神力化险为夷;而女的多为异类幻化而成的美女,有的(如《聊斋新传之画皮人》里的狐女香儿、《奇花记》里的牡丹花精玉版)善根未退,却常常为强大的邪恶势力驱使胁迫,有的(如《龙无目》里的龙女海兰珠、《神龟岛》里的仙女芸芷)来自神界仙苑却不明人间险恶,屡遭陷害,都显得楚楚可怜,因此也需要他人相助。作为被叙述的核心角色,这些非力量型的人物成为力量型的捉妖者救助的客体,又成为另一派力量型的妖魔队伍迫害或胁迫的对象,从而带动了正邪力量之间的冲突叙事。
在增强观赏的戏剧性上,改编者总喜欢在人与异类的奇幻叙事中展现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龙无目》(2020)增加了原著小说所没有的陆海笙与害人兔妖之间的激烈打斗,《海大鱼》(2020)同样增加了海若与鲲族王妃之间的魔力斗法,《奇花记》(2021)修改了原著中常大用兄弟对两位花仙姐妹的伦理背叛,让花妖与桑道人在拼斗中一掌震天地,拂袖乱沙石,《妖手摧花》(2020)虚构了妖怪树精偷偷潜入花仙阁大战花神,直至被正义力量击败而灰飞烟灭的惨局,《人鱼缚》(2020)、《罗刹劫》(2020)里则由妖怪化身的邪恶国师危害人世,坏人姻缘,最终在捉妖队伍的齐心协力下现形身亡。与《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古典小说里的神魔斗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斗法场景往往围绕男女主角之间的跨界情缘展开,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的力量,都可能会对爱情的发展产生助推或破坏的作用,从而使得影片的魔幻元素夹杂着更多的生活化内容,把爱情叙事与魔幻叙事融合在一起,扩充了《西游记》式的单纯降妖伏怪、神魔斗法的书写格局。这种影像叙事版图的展现深得聊斋小说之精髓,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所评价的“《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的小说描写特长。这些影片坚持生活化与陌生化并重,一方面做足情感戏来彰显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以浪漫清新唯美舒缓的故事节奏,推动男女主人公深化认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跨界情缘;另一方面又不断在情感主线中加入反派邪恶力量的破坏,凸显作妖的与捉妖的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冲突,通过常人所难以修炼的魔幻法术比拼以最终解决,从而使得情节在虚实相生、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中不断前行,寻找聊斋小说影像改编占领网络平台传播消费的艺术先机。
为凸显反派力量的顽固性,增进对立冲突的复杂性,这些改编影片常常设置妖物借他人身体活动的诡异情节,来丰富正反力量对抗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实这类叙事技巧并不陌生,早在胡金铨的《画皮之阴阳法王》(1993)中,就有法王借王生身体障眼害人的阴森情节出现,更早的吴承恩《西游记》中,则有孙悟空变身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狸而捉弄他们的喜剧情节。从属于聊斋小说的电影改编谱系,新近网络电影中的妖物借体行为多呈现为一种阴森的气氛,对所借用之正方人物的身体和声音常常做陌生化处理,使之更加契合妖物的本性而凸显妖物的狡诈与凶狠。《妖手摧花》(2020)存在着紫兰借体女孩杀害县令之女封妍的设计,《神龟岛》(2021)就有深海老妖附体到筱童尊者的身上欺骗王勉等人的新增改编情节,《奇花记》(2020)亦有花妖借葛巾皮囊媚害众人的神秘情节,在《美人皮》(2020)和《聊斋新传之画皮人》(2022)中,均呈现出女妖以美人皮囊迷惑男人企图达到自己目的的故事叙述。在科学理性昌明的“唯物主义”年代反复传播这种妖物借体的叙事技巧,创编者与接受者之间自然存在着心照不宣的意会和言传,他们当然都没有把妖物当作本体的存在,这类艺术设计更多是一种游戏性的艺术创新,但是在功能论上又起到了带动情节波澜、增强故事氛围的重要作用,如果处理得比较精致圆润,它们显然能够以曲折的情节和丰富的悬念艺术增添聊斋小说改编的审美亮点,促进影像作品和聊斋文化的网络传播效能。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影片中正邪力量之间的对立冲突在强化情节张力、烘托故事氛围、改变叙事节奏的同时,常常因为自我呈现的机械粗糙而容易带来风格单一化、制作简单化的艺术问题。其实《聊斋志异》中小说的内容风格是多样化的,有重点写情的(如《婴宁》),也有擅长记妖的(如《丑狐》),有重在惩戒的(如《画皮》),也有指涉伦理的(如《王桂庵》),当然更多是写情与记妖(如《青凤》)、惩戒与伦理(如《聂小倩》)并重的,还有像《龙无目》《海大鱼》这样随手而记没有多少情节内涵可传的笔记体作品。但是网络电影对它们的改编,往往不断强化或增加人(神、仙)与妖正邪对立的突出情节,这种一哄而上寻求卖点的跟风改编行为,很容易在影像传播中遮蔽聊斋小说的多样性。另外,为彰显冲突而应景赶制的打斗和借体行为常常存在着画面或逻辑硬伤,缺乏艺术精品的圆润通透,千篇一律的捉妖模式和过多游戏性的情节赘余也影响到影片的质量,容易偏离聊斋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蕴,这也是主要依靠网络传播的中小成本聊斋电影容易产生的艺术“软肋”。
三、融入喜剧元素
在当前这样一个大众消费进入浅思维娱乐风潮的喜剧化年代,“传统的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聊斋题材电影中的喜剧元素的不断增加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在网络平台多途径、分散性、个人化的悠闲消费状态下,寻求观赏影像叙事中轻松的喜剧成分,放松奔波于快节奏生活中的自我心灵,是更多网民下意识的精神文化诉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网络平台输送的诸多聊斋题材电影中的喜剧元素,大多失去了其原著小说中的喜剧风味,没有了“刺贪刺虐”的快意讽劝和辛辣嘲笑,而化为了搞笑的噱头和狂欢的闹剧,狗血剧情配上滑稽搞怪,阴森打斗夹杂快意恩仇,古典痴情混搭现代心机,影像韵味和叙事风格做得五味杂陈,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这种后现代式的审美改编与新语境下的喜剧娱乐精神非常契合,但其暧昧游移的文化定位容易与聊斋原著的文化蕴涵不搭架,给人产生取材改编的“两张皮”感觉。因此,正视这种改编症候,廓清和厘定聊斋题材电影中的喜剧元素的功能定位,考辨其语境形成的必然性与改编呈现的偏狭性,对于建构健康生产和良性传播的聊斋题材的网络平台尤其重要。
在这11部改编影片中,后现代喜剧意味最为鲜明的是《大梦聊斋》(2020)。它改编自聊斋小说《婴宁》,把原著里的痴情少年王子服改写为上天入地、本领高强的降魔师,与自己的好搭档唐闻奔行在找妖、打妖、捉妖的业务承接过程中,幻化为美少女的青丘狐女婴宁生活于罗店城,受到当地无数粉丝争抢追捧,新植入的人物铁匠铺豪放丑女干铁锤追求王子服失败而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却能够移魂婴宁之身借体复活,痛苦地徘徊在丑女意识、美女皮囊与害人狐女之间,遭受种种波折后坚守人性良知,又最终回到自己的原型,如愿地得到了王子服的情感。期间各种喜剧环节密集出现,王子服假装自杀却附体到济南府武举人身上使其受虐,还能借僵尸婚礼下冥界寻找婴宁,婴宁与干铁锤的形象在王子服眼前快速切换,而吃了仙丹的婴宁回到阳间生下冥间妖娃,两个无赖猜拳分先后去占有女人,降魔师通过与中国象棋中的统帅对话寻找新业务,修罗借狐母之体兴风作恶,收费的天师陆判驱使附身王子服的天煞戮神打败修罗……再加上毕业于蓝翔精通烹饪的降魔师唐闻、负有前世孽缘的青丘狐母、整齐森严的铁甲伏魔卫、说着方言絮絮叨叨的驱魔道长、法术拙劣各怀心机的炼妖师、丑陋矮小残暴吃人的冥间妖娃、神奇独特的斩妖鳝琴剑等各色人物和道具的出现,使得整部影片借着聊斋文化的古典风招牌,却极尽荒诞搞笑之能事,名为改编原著,其实早已与原著大相径庭。它的叙事虽然写人写鬼、降魔捉妖,从阳间辐射到冥界,跨界色彩鲜明,描绘视域宽广,但过多无厘头元素的展现恰好折射了当前“无神”时代对于鬼怪异类的工具理性处理态度,难以与《聊斋志异》的传统文化产生深层的审美对接。
此外,《聊斋之极道天师》(2020)在影片开始不久的情节中加入了喜剧化的元素,新增了六名结义的劫匪,他们装扮得各有特征,老大高度近视导致认人不准,老二身材矮小又弯腰驼背,老三油头粉面女腔味十足,老四和老五一胖一瘦、一高一低,简直是哼哈二将的翻版,只有老六一叶姑娘俊俏飒爽,还算正常;这六个人使用雨伞、铁镐、弯钩、铜锤、撬杠、大刀等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兵器,打斗动作滑稽可笑,遭遇妖怪毒手时,戏份其实并不多,这些夸张搞笑的情节与故事主线索关系不大,只不过起到了提前热场、活跃气氛的铺垫作用,简直就是赘余的存在。《奇花记》(2021)的捉妖降怪故事里出现了一位讨价还价、啰里啰嗦多次推销护身符的叶大师,做法行为也显得稀奇古怪;常在田身边的小厮魏新与中年村妇李二嫂发生了忘年恋,接连上演了滑稽搞笑的喜剧小情节,就连被常在田正义情怀所感化的女主角玉版,在个人单相思中也下意识作出了种种啼笑皆非的滑稽行为;两个小花妖在传授玉版魅惑男人的手法时,也讲究声、台、行、表、吹、拉、弹、唱的“八项基本功”。《罗刹劫》(2020)里书生马骥的伴随司徒空是一位侠客,但喜欢喝酒,同样唠唠叨叨个不停,其喜剧行为极富表演性;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以丑为美的罗刹国,因审美标准的错位又出现了种种不适应的滑稽行为,在遭到关押时,他们以掷骰子猜大小定输赢来确定谁去引走看押的兵士,马骥使用小伎俩作弊获得成功,后来却被夕月公主识破,落得个“大骗子”的称呼。这些喜剧性色彩非常强的细节设置看似与真实生活隔了一层,却以充满夸张性的表演丰富了生活的展现视域,但过多闹剧意味的现实指涉填充,又弱化了聊斋文化的传统底蕴,容易损伤古装题材影像叙事的清新的格调与文雅的品位。
其实《聊斋志异》也包含着浓郁的喜剧元素,蒲松龄不惜以幽默诙谐之笔法,借鬼怪仙妖等异类形象描摹人情人性,道尽人间曲直,达到讽喻社会现实之目的。不难看到,《仙人岛》中的骄狂书生王勉自视甚高,来到仙界炫耀才学,被芳云、绿云插科打诨、嘲笑奚落,终现其浅薄本质,这种赋魅与袪魅同时并存的展现方式暗含着鲜明的复调意味,潜隐着作家对那些在科举文化中养成扭曲的人格的辛辣讽刺;再如对狐女婴宁天真烂漫的无拘无束的笑声的喜剧性展现,以其直率天性的自然绽放与封建家族文化的压抑形成直接的对比,寄寓着作家对理想人性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期盼;还有《画皮》中的王生见色起欲,带厉鬼幻化的美女回家,而遭其剖腹挖心之害,妻子陈氏为救活丈夫在众人围观之下遭受疯癫道士戏弄,吞食他的咳痰唾涕的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隐含着作家止色熄欲、因果相生的天道伦理思考。但是这些看似庄谐并出却给人会心一笑,体会深远的巧妙设置却没有在改编中得以延续留存,而仅仅以噱头十足、疯狂搞笑的闹剧取代之,就不免失去了深沉的韵味。作为后来者的影像作品即使要表现创编年代的现实观照印痕,也应该重视原作的审美意蕴,否则就容易产生文化传播上的误读和误导。戴锦华认为:“电影影像中的‘历史’取代甚至创造了历史与记忆自身,这已成了并不鲜见的事实。”聊斋小说中的内容叙事虽然更多来自于作家个人的想象和虚构,但是从整体上依然归属于它们所依托的历史文化传统,今天的电影改编不能因为迎合网络平台的趣味而置原著的文化传统于不顾,而造成大众对传统经典小说的记忆遮蔽与认知偏狭。
在大众传播风行于网络空间的当下,改编自古典名著的影片也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娱乐时代的流行病,放逐文本开掘的深度所指、附着于喜剧甚至闹剧的表层成为其审美呈现的重要症候。因此聊斋小说的影像改编遇到网络世界,成为了聊斋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时代话题,碎片式、喜剧化的搞笑噱头正越来越多地占据在聊斋题材影片的呈现空间,放弃院线经营而专门指向网络平台传播的此类作品也不断出笼,在此语境下的聊斋文化传播貌似繁荣热闹,其实蕴含着潜在的话语危机。尼尔·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在社会发展趋于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文化专制的可能性在大幅度降低,但文化在娱乐产业流水线上沦落为滑稽戏的可能性却在增加,一个全民狂欢的泛喜剧化语境,不可避免地让更多的文化产品沾染上追逐喜感的新时尚,也包括这些改编自传统经典的古装电影,原著中古色古香的文化意蕴遭到删减和袪魅,而那些与原著精神不太搭架的流行元素被生硬嵌入叙事链条,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审美贩卖正日渐侵蚀着传统文化的承袭根基。在这样的浅思维娱乐风潮的误导之下,文化精神的萎缩就显得顺理成章,正视由此带来的事实真相,寻求深度发扬文化传统的艺术生成路径,将会变得迫切而必要。
毫无疑问,当前的聊斋题材网络电影无法如陈嘉上的《画皮》(2008)和《画壁》(2011)、叶伟信的《倩女幽魂》(2010)那样追求较为持久的大片效应。制作成本和生产周期的限定使得作品在演员阵容的选取、影像质量的呈现和内容深度的挖掘上都无法做到淡定从容,瞄向年轻网民审美消费的制作预设,也会促动改编者对时尚和流行元素的投机抓取,尚奇重险、追闹逐喜的浅思维娱乐设置便是其下意识的改编策略,奇幻、冲突与喜剧也成为赚取接受者眼球的致胜法宝。在此操作下,作为传统文化徽章的聊斋小说容易成为改编的由头或者赢得人们消费信赖的前设文本,其蕴含的深沉复杂的文化记忆则常常得到漠视,影片表层的话语喧嚣不断掩盖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不及物,这才是审美改编与传播中的问题所在。因此,簇拥在聊斋名义下的网络改编电影因过于向现实观照靠拢,而弱化了对文化传统集体无意识地自觉呈现,这种游离于聊斋原著的后现代式的取材改编和肆意渲染既疏远了历史,又难以深入到现实的机理,往往最终沦落为娱乐工业和网络传播流水线上的精神“快餐”。周星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电影的难点,依然是克服现实表现的缺乏与探究深度。”这一诊断尤其适用于笔者论述的此类电影,人们需要在今后的改编中吃透原著,消除浮躁,精心考量,进而克服针对网络平台的艺术生产和审美传输所产生的创编困境。

附表:2020年以来11部聊斋题材网络电影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