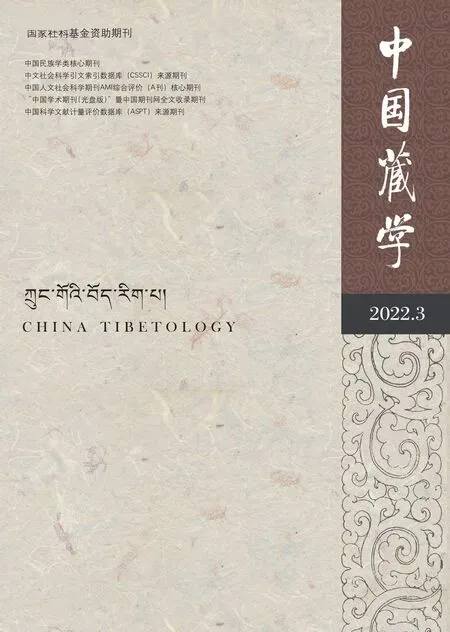17世纪白利·顿悦杰与西藏各宗派间的关系考述①
泽仁曲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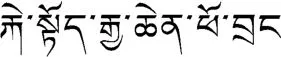
一、白利·顿悦杰家族与格鲁派强巴林寺帕巴拉活佛
根据现有资料,有关顿悦杰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协昂史籍》中,其作者释迦拉旺系昌都强巴林寺第一世根多⑤根多,全称为谢文·根多()。活佛,是昌都强巴林寺五大活佛传承“协昂师徒”()之一。书中有白利家族和其部族对第三世帕巴拉·通瓦顿典()作供养的记载,当时顿悦杰年幼,其父亲阿潘杰()在擦瓦岗(,今昌都八宿县邦达地方)的“古拉昂雅”神山脚下向帕巴拉·通瓦顿典作了大供养。该书载:“早在白利头人或白利父王时期,擦瓦岗神山之下白利王向第三世帕巴拉·通瓦顿典供奉诸多礼品,第四世帕巴拉时期白利王亦可以说是帕巴拉的老施主。”⑥释迦拉旺:《协昂史籍》(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8页。又说“白利头人将(帕巴拉)邀请至古拉昂雅附近,头人与其妻、子顿悦杰以及弘法团体、头人家族、其他诸位领袖人和各部分别致以百贡”⑦同上,第181页。。可见当时白利家族及其下属都对帕巴拉进行过大供养,且供养过程耗时久、供养丰厚,这种福田施主关系的维持显然也是有了彼此间的利益考量。
除了帕巴拉,强巴林寺的其他活佛如根多,也与白利家族弟子关系密切。《协昂史籍》载:“在‘嘉热’期间,自昌都专路邀列,白利王方邀亦会至,白利之邀甚厚,以随其行,后往‘朗青纳’,白利觉巴杰、潘秀杰至奉茶地。”⑧释迦拉旺:《协昂史籍》(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8页。白利地方专门邀请根多活佛。作者强调了在迎请的队伍中出现了白利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并对其进行了供养。由此能断定在顿悦杰的父亲阿潘杰在世时,白利家族与昌都强巴林寺有着稳固的福田施主关系。

17世纪初,白利四处扩张,势力迅速膨胀,也对昌都地方产生了影响。当时强巴林寺正值四世帕巴拉·曲吉杰布①帕巴拉·曲吉杰布(1605—1643),1642年,固始汗率兵打败白利头人,占领其治下的地区后,将四世帕巴拉·曲吉杰布尊为“恰达”,意为昌都之王,管辖寺庙50座。任法台,同时管理昌都地方政教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帕巴拉所属的昌都在各方面基本可以与白利势力相抗衡,帕巴拉基于自己已有的名望和实力,无须对白利的威逼步步忍退,并且在顿悦杰改变支持对象后,两教的关系势必会走下坡路。如此一来,昌都一方没有理由一直在军事上支持顿悦杰。根据《协昂史籍》的记载,白利与昌都的矛盾是因为白利加重了昌都的赋税:“1620年的矛盾,是因归属昌都寺的供用军税等诸税务过重等发生,不及三年,卒至1623年白利军决向昌都战。”②释迦拉旺:《协昂史籍》(藏文),第13页。如此,我们知道这个矛盾的爆发点是征税过重,并且是在日积月累之后一触即发。从这一段记载我们也可以发现,昌都与白利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爆发战争。
《康珠传记》载:“白利与昌都的福田施主关系逐渐走远,昌都的头人和下属未用灵器和朵玛等仪轨消灾,也未实施禳解,需要的尽从布仓(指顿悦杰——引者注)取,行此甚明,虽两释所平然,然一方倦而一方强,故无计可施,只略试防。”③米庞·贡嘎桑布:《吉祥嘉瓦多康巴噶玛丹培传记之成就嬉戏》(藏文),第186页。当时双方关系紧张,欲通过仪轨的方式去破坏对方。有人说是因为昌都人对白利实施破坏活动,也不像从前那样如数缴税。从相关史料来看,当时康珠活佛曾尝试进行调解,“白利兵欲击昌都明矣,思如拉萨与色拉、哲蚌相敌,虽万般无奈,诚以白利之远而罢。”④同上,第118页。至于这一纠纷最终是如何调解、何时平息的,在史料中未找到相关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相关文献和口述史,白利攻打昌都致使后者在几年内衰退不前,顿悦杰甚至在寺内建监狱。1641年顿悦杰被固始汗消灭后,固始汗把包括白利部分地方在内的大片区域供养给帕巴拉活佛,自己也从帕巴拉处接受诸多灌顶。直至今日,白利地方与历代帕巴拉活佛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二、白利·顿悦杰与竹巴噶举派康珠·噶玛丹培
尽管以往史料几乎把顿悦杰视为一名虔诚的苯教徒,但通过最新资料可以断定,顿悦杰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宗教人物其实是竹巴噶举派的康珠·噶玛丹培。




一世康珠活佛噶玛丹培唐卡画像(18世纪)
有关康珠活佛本人的法相以及与顿悦杰的福田施主关系,笔者在康巴寺找到了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绘于18世纪的唐卡,主尊像为康珠一世活佛噶玛丹培。

三、白利·顿悦杰与苯教“囊希·嘉瓦洛珠”


从顿悦杰本人和其父辈接触的高僧与寺院来看,顿悦杰并非一生只支持某一个宗派。另外,笔者根据上述《康珠传记》的记载和田野资料,了解到顿悦杰曾出资建立的几座寺院,也不限于某一个教派。
综上,可以肯定的是,在噶玛丹培与顿悦杰建立起福田施主关系后,噶玛丹培所建的寺院,几乎均由顿悦杰提供供养和支持。
据记载:“顿杰(顿悦杰)即位后虽势力迅猛发展,将囊希等苯教喇嘛尊奉为上师,却对几位利美(无宗派)喇嘛行罚,这使其成为众佛僧的公敌,进而成为他的政权根基动摇的祸根。”①绕热·阿旺丹贝坚参:《王统世系教派源流水晶鉴贤者项饰》(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可见当时顿悦杰信奉苯教而遭到其他教派的排挤,他的敌人以此为借口拉拢其他势力,名正言顺地联合起来一致攻打白利。
四、结 语
格鲁派部分高层以佛教敌对势力的名义铲除了白利·顿悦杰,并在格鲁派有关史著中将顿悦杰描绘为视佛教为敌的苯教徒。通过以上考述,可以看到历史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不只是因为宗教上的冲突导致了白利头人与格鲁派—蒙古联合体之间的这场战争,格鲁派邀请外力消灭顿悦杰本身就格外惹人注目,由此也引发了笔者对背后真实原因的思考。
其实,顿悦杰与西藏各宗派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而格鲁派笔下的苯教徒顿悦杰,实际上是格鲁派为了出兵歼灭他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甘丹颇章最初建立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格鲁派的盟友和硕特部在正式进入卫藏之前,首先在东部康区武力消灭了白利地方势力,白利头人被认为是五世达赖喇嘛在卫藏地区的竞争对手藏巴汗的盟友,因而是格鲁派的敌人。此后,在格鲁派作家的笔下,白利始终以敌对势力的面目出现,而固始汗铲除白利,被视为甘丹颇章取得控制西藏地方政治权力的关键一环。基于固始汗自身在蒙古各部中所处的险境、卫拉特部与格鲁派之间的关系积淀,以及格鲁派当时面临的困境,固始汗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应邀南下,以期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目的。然而,对于白利这个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我们知之甚少,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格鲁派史家对此事作出如此重要评价的真正理由。
这一案例也引发我们的思考,是否还有许多重要的区域、重要势力的历史真相被格鲁派的史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根据史料来看,虽然白利地方有苯教寺院,但白利·顿悦杰本人和他的家族却不是一直崇信或支持某一种宗教或宗派,而是对与其保持关系的各教派都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并持一定程度的尊重。在与康珠·噶玛丹培关系恶化前,顿悦杰支持康珠活佛在当地传播竹巴噶举。在顿悦杰生命的最后七年内,他与苯教的囊希·嘉瓦洛珠往来密切。顿悦杰自己在宗教信仰和地方政治中,保持了以政治为主的观念,并没有因福田施主关系影响政治抱负的实现,也没有让宗教人物在关键时刻充当决策者。由此,我们不仅了解到他在支持宗派方面的变化,也发现顿悦杰并不是佛教的敌对势力。
通过新发现的史料可知,顿悦杰与格鲁派的冲突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博弈。由于顿悦杰的势力扩张影响了五世达赖喇嘛的供养收入,顿悦杰的崛起也使得联合藏巴汗和却图汗共同打击格鲁派成为可能,并且这几方势力当时都是噶举派的拥趸,加上康区当时也是五世达赖喇嘛较难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地方,因此顿悦杰的崛起对格鲁派而言影响甚大,遂成为蒙古和西藏地方联军必须消灭的一方。顿悦杰的形象,由此在格鲁派的历史书写中被建构,成了一名尊苯抑佛之人,从而导致后人对这一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曲解。蒙古和西藏联盟的西藏地方政权“甘丹颇章”建立后,昌都的多座寺院被改宗格鲁派,而且这些地方也向甘丹颇章缴纳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