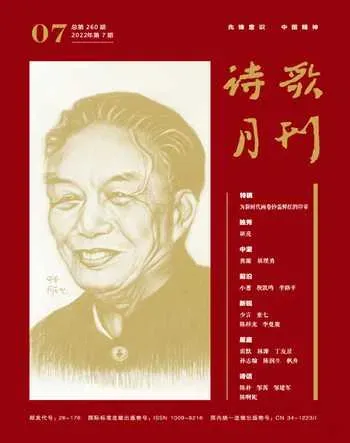冰镇浪漫主义(随笔)
胡亮
作者公开谈论自己的作品,显而易见,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按照美国新批评的观点,既要切断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以杜绝“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还要切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以杜绝“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最终的释然仍然缘于一句老话,“诗无达诂”,这句老话也许倾向于揭橥一个真相——作者公开谈论自己的作品,为害甚微,绝对不会导致读者保卫派的大面积缺席。
要问我都写出了什么样的新诗?不外乎以下几类:吊古诗、怀旧诗、感时诗、咏物诗、论诗诗,以及作为一个大宗的游仙诗。
先来说吊古诗——比如《风流》和《夜难寐》,前者献给清代诗人张船山,后者献给唐代诗人陈子昂。张船山和陈子昂都是吾乡之先贤,在一篇小文章里面,我曾经这样谈到他们:“在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亦即宇文所安——看来,陈子昂可以视为李白的前奏。而在两位清代学者——吴修和顾翰——看来,张船山可以视为李白的再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者,完全可以代表吾乡之古典诗传统。《风流》既是向张船山也是向古典诗传统致敬——想想吧,张船山,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堂兄弟,众妯娌,众姐妹,全都能写诗,那是一种多么引人入胜的风流啊?引人入胜,久已失传。再来说怀旧诗——比如《避秦》和《惊艳》,前者献给罗马尼亚体操玉女科马内奇,后者献给英国作家伍尔芙。1992 年,我见到了少女科马内奇的一帧照片。1997 年,又见到了中年伍尔芙的一帧照片。如果说科马内奇已经臻于青春、人体和清澈的至高境界,那么伍尔芙已经臻于独立、高贵和忧郁的至高境界。接着说咏物诗——比如《惨败》和《星星》,前者咏夹竹桃,后者咏墨蚊儿。咏物诗而能穷形尽相,首推杜甫,我的几首当然不值得多费笔墨。接着说论诗诗——这是我的杜撰,也就是所谓元诗——比如《干脆》和《烹饪》,前者论及世俗生活如何让诗延了期,后者论及情感如何对诗抢了先。这样两种情况,当然并非罕见:世俗生活太凶猛,诗只好掉队;情感太强烈,诗只好靠边。
我的分类法也许只能反证我的无知,或无能。比如《杭州》,是赠友诗,也是论诗诗。这件作品牵扯到我与蔡天新的一桩公案——2021 年,杭州,我们一边吃料理,一边聊及诗与语言的问题。我意,应交由诗人来解决;他说,应交由语言学家来解决。虽然小争了几句,也无妨,且让他坚持他的“平易”“晓畅”和“语言(langue)至上论”,就让我坚持我的“妖娆”“陡峭”与“言语(parole)至上论”。《杭州》继《新诗去从论》再次出示了我的汉语立场,“找回更多的汉字,发明更多的鸳鸯”,蔡天新却怀疑此处误用了动词。他问我:“发明?”是的,这正是诗人与语言学家的致命之别。
似乎已经穿过了太多的小密室,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套间。现在,重点说游仙诗——比如《放弃》《照看》《仙境》《无休》《忘机》《悟空》和《无遮》。从某种程度上讲,吊古诗也罢,怀旧诗也罢,感时诗也罢,赠友诗也罢,咏物诗也罢,论诗诗也罢,几乎全都是游仙诗。游仙诗是古典诗的一个小传统,主要有两个大宗:一个大宗是“神仙”(寄望于神仙),一个大宗是“山水”(托身于山水)。两个大宗,时有交错。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游仙诗,与道家和道教颇有关系。南朝理论家刘勰讲“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又讲“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上句说“道”的蓬勃导致了游仙诗(这个没有问题),下句说“庄老”的避让导致了山水诗(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山水诗意味着游仙诗的泛化,与此同时,山水诗意味着道家哲学向道家美学的转化。如果把“山水”解释为“自然”,把“神仙”解释为“自然规律”,所谓游仙诗也就类似于近来盛行的“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学的奥义与要领,一个是大地伦理(land ethic),一个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一个是非人类中心主义(an ti-anthropocentrism)。如果回译成老庄哲学,无非就是避免“天人交战”而促进“天人相合”。我当然并不是道教徒,却甚爱山水,不厌其烦地写到西山、渠河、涪江、动物和植物。以我观我,以我观物,以物观我,以物观物,不过四站路,我却来回走了几十年。最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平静,就是喜悦。稍微夸张一点儿来说,“我”,已经得到了或得到过“无我”。
前文已从主题学的角度交出一份自供,后文将从修辞学的角度寻来一份旁证。在论及《非李》的时候,有位北方学者,引用江弱水先生的观点,说此诗大体上乃是“棋手的诗”而非“赌徒的诗”。按照江弱水的说法,赌徒的诗——比如李白的诗——乃是 “神力”“灵感”“迷狂”和“空手套白狼”的结果,而棋手的诗——比如杜甫的诗——却是“手艺”“冥思苦想”“推敲”和“不断试错”的结果。江弱水还引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权衡损益,斟酌浓淡”,又引来南朝萧衍的《围棋赋》,“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反复论证何谓棋手、何谓棋手的诗。我确实一直致力于字字必较,步步为营,读了《鸡尾酒》前十行便可知晓——此种修辞不能不说是复杂修辞:一条线索是攀登冰山,由低到高;一条线索是吟诵史诗,由缓入急;两条线索合为一条线索,故而索道既有舌头亦有语速,故而视觉形象也就突变为听觉形象;细节与细部方面,定题、起兴、用喻、通感、夸大与缩小、炼字、造句、跨行、设色、定调、留白乃至诗速与诗形,肯定不能说,没有下过一番雕虫的功夫。也许,就大概率而言,我并没有锻造出棋手的诗,却暌违了赌徒的诗(暌违了那种可贵的冒失、冲动、热烈、孤注与孤胆)。棋手的诗与赌徒的诗,两者的对峙,被江弱水引申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峙,现代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对峙。棋手的诗,邻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赌徒的诗,邻于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诸如此类的区分与判断,当然只是假想或绝对理论,因为赌徒不妨是棋手而棋手不妨是赌徒。那么,并非出于对“博弈互济”的觊觎,我反而乐于自领一顶这样的冷色花帽子——“浪漫主义”,不,“冰镇浪漫主义”。
——兼与赵沛霖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