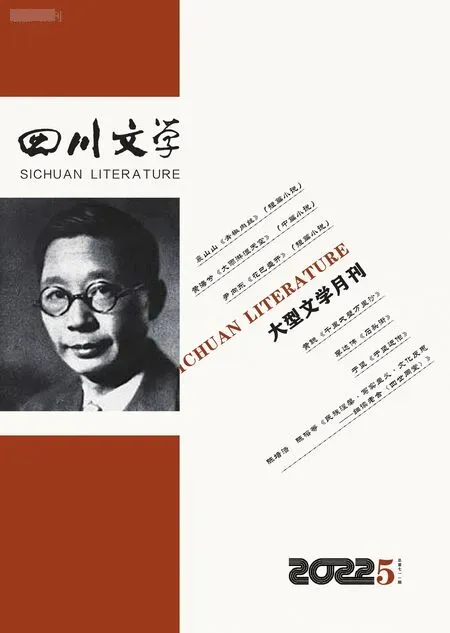岁月深处的那些动词
□文/邵永义
人是动物,需要和动词相守一生。
在反映、描摹和再现人们生活形态方面,感情色彩最丰富,组合拼装功能最强的,是动词。它不仅见证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也精准地记录着人们生活的变迁和轨迹,珍藏着人类生长的记忆和那些平凡的生命生活的态度。
剪脑壳、剃头、理发、美发。指向没有改变,只是从俗到雅的演变;会钞、结账、买单、刷卡、扫微信,都归于“付款”,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社会进步与变革,许多记录我们先辈生产生活方式的动词,如水而逝,站在岸边的我们,在偶尔回望中,找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被岁月包裹着的记忆,散发出陌生而又熟悉的气息。
讨
走进河边的菜园地,张大娘说:“讨几个茄子!”王幺娘说:“讨几把四季豆!”家里做饭时,母亲会在灶台上叫我们“快去地里讨几个海椒回来!”在川西坝子,这个“讨”不是去“要”,而是采摘的意思。
开春了,孩子们提着竹篮,呼朋结伴去岷江边河滩上、堤埂上“讨枸杞芽”!那枸杞开春新发的嫩芽,青绿稚嫩,脆生生的。用菜油一炒,是春天农家饭桌上一道稀缺物:入口微苦,继而清香,有清热、祛火、消炎的功能。难怪有民谣唱道:“吃了枸杞芽,满山爬……”
春天最辛苦的农活不是耕田,而是讨茶叶:顶着露水爬上高山,躬着背,弯着腰,在一垄垄茶地里讨茶叶。春茶量大叶肥,新春的明前茶,是清明前的嫩芽,更早一点的茶叶浅绿带黄,像雀嘴巴微张时吐出的嫩舌,叫雀芽,适宜制作顶尖的竹叶青茶,现在有技术把茶芽提前到了雪芽阶段,那顶雪而生的茶尖叶甚是宝贵,讨茶人就更辛苦了。到了秋季,一切果子都可以讨了,讨柑橘,讨柿子,讨南瓜。
讨,这个动词兼有摘、采的意思,从下向上叫摘,由上而下叫采。但川西坝子、岷水两岸的讨字很有讲究:言旁,用语言来表达要求,是否在更早的年代还要念一段文辞,递交申请?一个“寸”字,表明要得不多,一点点而已!这种谦卑,不是乞讨那种没有尊严的白要,因为无论“讨”什么,绝大部分还是自己种植的,自家菜地,自己劳动,要用了,还需要“讨”吗?这份谦卑是农民对土地的尊重,对大地所滋生万物的敬仰,便是劳动后的收获,也要感恩大地万物,风调雨顺,让劳动者讨得了生存所需。一个“讨”字,要得不多,不要穷尽了生活来源,要简约、节省、多留,少取,节制自身的需求,让大自然拥有更丰富的生活资料和生物之源。在“讨”的过程中,我们心怀感恩,节省节约,这是超越物质获得感的生命教育,充盈着传统的道德引领和自然情怀。
淘
淘,往往和洗联在一起,淘菜、淘米。高深一点的淘,比如淘沙金,指在河沙里用水冲法获得沙金的方式。
我们川西坝子的淘,就是淘沙金的淘:筛选、鉴别、选择,做起来很辛苦,也很愉快。
在主人挖过的红苕地里,因为主人粗心,因为苕根被挖断等原因,会有一些漏网之苕被遗失在地里。于是乡村的孩子们拉起一支“淘红苕”的队伍,在灾荒年,不少成年人也加入这个队伍,从岷江东岸过来,跑几十里山路到这边淘红苕。工具是一把锄头、一只竹背篼,目标是农民挖过红苕的土地,在一块地是不行的,往往要沿山坡找到更多的红苕地去淘。这个淘不沾水,完全是锄头和土壤的亲密接触,有时不幸碰到石头,让锄头曲了刃。
淘红苕也有窍门,选地,是那种较为平顺的,只被主人挖了一遍红苕的土地,如果地面乱七八糟坑坑洼洼的,那多半被“扫荡”了多次。地里那些略显地硬,有起包的地方,可能就是当时主人锄头没有挖到的角落、田埂。因为种红苕要防湿,都要起垄,叫“红苕埂”,学名叫“艮”。起包的地方,因为雨后挖过的土壤都会陷下去一层,没挖过的地方或有红苕藏身的地方,地面就起包了,易于淘到红苕。
淘红苕要走远路,爬大山,还要背着一个大背篼,带着背篼里的“胜利果实”去转战山坡。那些外乡的大人,淘到的红苕都舍不得吃一个,面带土灰色,背负着一家人的希望,把一背背淘得的红苕,可以喂猪的苕根,爬山过河背回家去。
我们只淘红苕,人能吃,猪也能吃,猪吃了红苕,我们有肉吃!
比淘红苕细致的劳动,是淘花生。川西坝子花生产地多,产量也高,沿江边沙坝成片种植。农民挖花生是纯手工劳动,一张小板凳一把平口小板锄,坐在地里以切豆腐的方式向前推进。但花生果粒小,又裹满泥土,还有挖断了根的,让很多花生遗漏在土壤中。成熟的花生一遇下雨,很快会从土地里长出白白胖胖的花生芽,暴露了主人的粗心大意。
花生是稀罕物,那些年农村大人小孩的零食,不外乎炒花生和炒豆子。炒花生可待客,油炸花生米是可以上酒席的一道菜,川西坝子淘花生的队伍多半是妇女和儿童团,也不用板凳,一把小板锄,一只竹篓子,就可以散开去在主人挖过花生的地里去淘花生。成熟的花生老气、饱满、褐黄色,有些主人不要的嫩粒花生,已有了紫色的内衣穿着,青青白白的像个小姑娘,即将成熟。孩子们眼睛好手脚快,一下午总会在主人挖过的荒地上淘出一两斤花生来,提到河边用水一洗净,就会分出成绩:白壳的灌浆不足,褐黄色的才饱满、圆润、多浆,炒来化渣。
很多淘过红苕花生的孩子,长大了开始跑到地摊上和古旧书店“淘书”,原来是习惯了这个淘字:花劳力,付艰辛,找宝物。
捡
老师在课堂上说:“捡到东西要交公!”下课后我们就会去捡东西,只是这些东西不用交公,我们捡的是菌子、橘子皮、枞果子(松球),还有石头和杏仁米(果核)。
川西坝子的“捡”,是一种劳动,公开公平并且合法正当去收获,捡的东西不交公也退不回去:没有失主!
在岷江两岸的浅丘地带,松林密布,青杠树泛黄。在那落叶层层堆积而成的腐殖酸性土壤中,数不清的菌子(蘑菇)或打着小伞,或头顶瓜皮帽,或戴着小斗笠,从草丛里、土壤里直往上蹿,这些野生菌种采天地之元气、阳光之温度,在初夏季节某一场雨后,星星点点地冒出地面,给这些贫瘠的山岭带来财富,给平淡的生活陡增无限乐趣!

捡菌子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认清哪些是食用菌,哪些是有毒的,孩子们捡的菌子,都要交给大人检查,一朵朵过手,那种色泽过于妖媚,手感缺乏质感弹性的,多半是不能食用的。菌子可以卖钱,自己食用时多用清烧,纯素烧的,我们叫“烘”。锅里多放蒜,蒜能杀毒,如果菌菜里的大蒜变绿变青,就是混进了有毒的菌子,坚决不能吃的!
小镇上柑橘上市后,可以捡到很多橘子皮,主要是红橘,皮子可以入药,晒干后送到供销社的门市,可以卖到几毛钱一斤。果核中,李子、桃子、杏仁的核,也满地去捡,晒干后,再小心地敲开硬壳,那些衣着红衣黄衫的米核,送到供销社,价格比红橘皮还贵。捡东西能生钱,捡的人就多了,但要晒十几天,再敲开核壳,也需要坚持十多天,万一中途淋了雨,就全部废了。
比较快捷地捡到东西,又有乐趣去爬树,就数捡枞果子(松果)了,那炸开了的枞果子,含油脂重,易于燃烧,是引煤的柴引子,没有炸开的叫“哑巴枞果儿”,要用专门的长竹竿去打,用力去摇动松树,不过没有炸开的不易引燃,湿气重,我们不常捡它。
现在出门能捡的,没有菌子也没有枞果子,可能只有街角落和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子了,据说也能卖钱。
闹
小时候买肉要凭肉票,一月吃一次肉叫“打牙祭”,那些江河溪沟里的鱼类,就成了我们的目标。
学校背后有一条溪沟,从鸿化山上下来,在砖厂前方修了个闸门,芦笋青葱,溪水盈盈,水草丰茂,肯定藏有大鱼。但水深草多不能撒网,也不能下去扎埂放水抓鱼。我把隔壁的青婆儿喊去看,想象着一条条白晃晃的鲫鱼、青波、白甲、翘壳跳出水面的美景。
“闹吧!”青婆儿果断地说,他比我大几岁,早就不读书了,但爱捕鱼抓虾,全身晒得像条乌鱼。
“闹?”成都回来看外婆的小勇也跟着来了,他天真地问,“在岸上敲锣打鼓地闹,鱼儿就会跳上岸吗?”
青婆儿哈哈大笑。
我告诉小勇:“闹就是用药去喂鱼,让鱼中毒后好抓!前几天,下场口不是有家人吃菌子,被有毒的菌子闹倒了吗?”
小勇听他外婆说过这件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第二天放学回家,青婆儿正在他家院子里制作“闹鱼”的饵料。那个会读连环画给我们听的小勇,像个小徒弟跟在青婆儿身边打下手。青婆儿把一捧黑色的籽粒放进铁砂锅里,说这是马桑树结的籽,鱼吃了会中毒,边说边把马桑果捣成粉状,用匙子挖出来,盛在一个瓷盆里,再把准备好的一斗碗面粉倒进去,用筷子拌匀,开始掺水搅和。
小勇说:“像和面包饺子一样!”
青婆儿严肃地告诫小勇:“千万别吃,会闹死人的!”抬头看到我,就叫我回家偷点菜油来,说这样更香,鱼喜欢吃!
青婆儿在饵料中加上菜油,把面团搓成豌豆大的小汤圆,很匀净很好看。小勇闻了一下说:“好香!”我想象着一条条大鱼从水中跳出来,落到草地上还张嘴摆尾的情景。
第二天中午,我们带着饵料、舀鱼的大网子、一个大铁桶,悄悄来到那片水域。从不让我们摸他连环画的小勇带了三本连环画,发给我们欣赏。青婆儿沉稳地说:“让太阳再晒一会儿!”看水面波光闪耀了,青婆儿叫我们别动,他端着饵料到岸边,用力地把那些小汤圆撒向水中,撒了这边又跑过上面的石桥,到对岸去撒,一边大声地说:你们就等着大丰收吧!
水面上闪出一个个波纹,是鱼在浮头,动作敏捷地吞食那些小汤圆,还有更大的鱼在水中,尾巴拍起的浪花优美地传得很远。
青婆儿开始手执舀鱼的网子,警惕地巡视着水面。我跑到上游提了半桶没有染药的干净水回来,就看见水面上那些昏了头的鱼在打转转,有一条白影直跳到岸上,被小勇双手按住,是一条窜丁子。青婆儿激动地喊了声:“收网了!”他舞动手中的舀子,像表演似的一次次从水面把鱼舀上岸来,嘴里喊着:“这一条是鲫鱼!这一条是翘壳!”那条翘壳全身银白,扁状的身子在桶里只好站着,一只大铁桶已盛了大半截,我只好去折了根柳条,把明确翻了肚的窜丁子、红尾子用柳条穿成一串。
守着大半桶鱼,小勇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死了呀!”这声音让我想起在停电的夜晚,小勇在煤油灯下给我们读连环画《鸡毛信》,画中日本鬼子用刺刀杀了海娃的羊在火上烤着吃,海娃在心里愤怒地骂:“杀千刀的鬼子呀,你们是一群狼!”
这时已有其他小孩参加进来,分享战利品,我对青婆儿说:“够了,小勇看到死鱼不高兴!”青婆儿大笑道:“马桑果儿闹不死鱼,是闹昏他们,等下再换道干净水,就活过来了!”
小勇指指我提的那串鱼,说:“还是有死了的!”我说:“那是他们太贪吃,吃得太多了就撑死了!”
清水里,被马桑闹过的鲫鱼都活过来了,青婆儿说:“我药放得少,不然喝不到鲜美的鲫鱼汤!”
闹鱼,可以放得轻点,麻醉了就好!闹耗子,我们就会下重药。
农村耗子多,家里的粮食花生常受侵害。有个腊猪头挂在楼上的木梁上,还用笋壳穿了个罩子。可当家里来了客人,奉大人之命去取腊猪头时,已被耗子偷吃了大半。父亲听说后开始谋划闹耗子!我说“青婆儿会闹耗子”!父亲嘘了一声:“别说,它们听见就不吃了!”
我们用供销社买的硫化锌之类,拌米饭,抹在肉和骨头上。黄昏时把家里的鸡都关进笼子,才开始在走廊、饭堂、猪圈外面、门背后,小心翼翼地摆放着,那情景,像电影《地雷战》中的民兵在悄悄埋地雷。第二天,我们查看战场,那米饭、肉片,都不见有动过的痕迹,甚至像是无意掉在饭桌下的肉骨头,也没有耗子去碰它。
父亲分析说:“你昨晚说的话被耗子听到了!”我说:“我没有说闹耗子呀!”父亲大笑:“你才又说了,今晚上耗子又不会来了!”
当晚放弃了闹耗子的行动,结果耗子们像狂欢般,在木楼上热闹了大半夜,示威游行呵!
偷
在乡下,割猪草时在田间地头偷摘一根黄瓜,砍柴时在路边偷挖一个红苕,即使被要求进步的同学告到老师那里,老师也往往用下不为例来了结此案。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同学唐大娃偷了贫下中农的柚子,被告到政治老师那里,政治老师高度重视,展望未来,以“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的预见性,罚唐大娃写了检讨全班念,并扫学校操场一个星期。
偷也有大事,引发成刑事案的。
家乡有个黑龙壕,是鸿化堰的放水壕,其实就一条小河。小河上为了通行,除有一座正规的石拱桥外,很多便桥是用木板铺的,甚至就是一棵大树,剖开来平面朝上,就成了两座木桥。有一年,下游一个偷儿,利用晚上跳进河里,用肩膀把木板桥扛起来,顺到河里,到下游再捞起来,他偷了两座桥,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抓了,抓他时在他屋后的竹林里,搜到了这两块木板。上、下游自来不和,被上游的“革命群众”举报为“破坏农业学大寨”。我们去看热闹时,那个偷儿被绑在公社的院子里一棵黄桷树上,手都充血了……
课本上就有“偷出血案”的课文,狗地主偷公社的辣椒,被少年先锋队员刘文学发现了,那个偷辣椒的地主竟活活掐死了刘文学。
偷大偷小都是见不得天的,更有可能违法甚至犯罪。大人和老师都这样教育我们。
但在我们家乡,有一个“偷”可以光明正大、大张旗鼓、呼朋唤友地去进行。偷成了一个人人参予、公众认可的节日:偷青!
偷青的日子只有一天,就是每年正月十五,又叫元宵节的那天。既是偷,自然是晚上的行动。青也有约定俗成的对象:青菜、青笋、芹菜、小葱、蒜苗之类菜蔬,也可“见青就偷”,因为是晚上,可以“出门一把抓,回去再分家”。偷青成了川西农村的习俗,据说这一天偷青,可以来年添财,被偷的农家也不怕:有人帮你腾地干活,那些菜地也该空出来春种了,再说,我也可以偷别人的菜,是没有吃亏的,明里是邻居,暗里可以“互偷”,心照不宣。
岷江冲积而成的河滩地,盛产一种苞苞青菜,青叶油绿柔嫩,菜心纯白如玉,关键是青菜叶茎上肉厚起苞,格外脆爽。这种菜长于冬季,老的叶茎可做泡菜,嫩的正月间煮腊肉,味极鲜香。正月间的农家待客,大多是一碗油亮色的老腊肉,一大碗如碧波般的青菜汤,荤素相伴,既润且爽。这种青菜,过了岷江这一段就不起苞苞了,自然成为“偷青之夜”的主要目标。
于是正月十五之夜,偷青的人先是若无其事漫步在田间地头,待看见那碧绿的菜畦,油亮着一蓬蓬的青菜,于是顿生偷意,选择隐蔽处,翻菜园入他人地中,夜色里蓊蓊郁郁的一片,没有照明,往大窝的青菜上伸手,于根部一提,扯出来连菜带土,再扯一窝后,泰然自若悄悄离开现场,到了小路上,碰见同是偷青之人,也不细问,互道你手气好:“这窝菜煮枕头粑,真巴适!”
偷来的菜提回家中,刀削水洗,切成方块或长条,那边就有老婆婆拿出为过年特别蒸制的枕头粑。枕头粑是川西的年货年礼,以糯米和饭米混合水磨成粉,用竹林里的粑叶裹了大蒸笼上两三个小时蒸熟而成。枕头粑是细粮,除了蒸了送客,主要的一个用场就是留到正月十五,青菜煮枕头粑。吃法也有讲究,先把偷来的青菜煮六七成熟,加盐、猪油出味,再将切成小块的枕头粑下锅,几分钟后,粑已煮软,菜刚煮熟,便下点葱花、味精,盛上碗就可上桌了。一家人也不怕是“偷”来的,白的粑,青的菜,看着透亮,吃着清爽。老人们还要念一句:“一青二白好过年,清清白白又一年!”小孩时不懂,问大人为啥去偷别人的青菜,大人很有底气:“不是偷别人的菜,是亲戚的,不然为啥叫偷亲呢?”于是我们放心吃。
对门有个邻居杨大娘,声音大,爱吼黄腔,十五晚上就会唱:“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进门偷尿缸,瞎子看见喊逮到,聋子听见在街上,瘸子跑上去把贼抓……”这唱的全是反话,从她那透着灯光的木板屋里传出来,在老街上久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