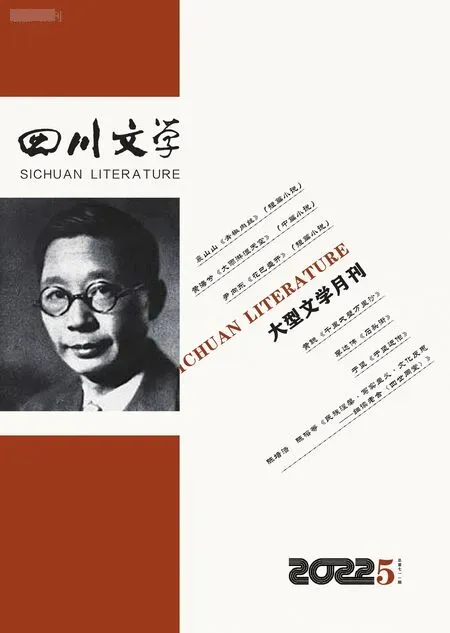仨
□文/唐俊高
一夜辗转反侧。

身子粗短,嗓门粗犷,成天像个陀螺,浑身带着风、带着响的仁兄,终于偃旗息鼓地躺下,手腕上扎着输液针,腰腹处插着塑胶管。
一生好强,一心向上,一门心思跌跌撞撞扑爬礼拜攀上了自己设定的职位,兑现了自己既定人生的仁兄,却不曾想会轰然瘫倒,更不曾想无情的病魔,会死死缠上他的高光。
我并没在他的病床上坐下。
他的床头柜上,没有水果,没有鲜花,有的全是夸张摆放着的一些文件和书本。
我不相信会有人来看他。至少,嫌他怨他的前妻跟女儿,肯定不会。
我跟他熟识较早,当时他还在乡上,刚刚完成从聘用到正式录用的身份转变,信心爆棚地规划着到好多岁当啥,到好多岁又当啥。后来果真起来起来又起来。每一次变动、升职后,他都回到乡下老家祖坟山前,一一磕头汇报。
他对自己每一次变动、升迁的日期,记得准确无误,包括哪天下的文件、哪天哪个到单位上来作的宣布,等等,常常在人前口若悬河如数家珍。
我没见他取得过啥突出成绩,就只听他一张嘴叽里哇啦:“不管在哪个单位,我都只忠于老大。”这话里当然包括他遭大伙白眼唾弃的老大,遭党纪政纪拿下的老大,甚至遭国法律条逮进去的老大。“我对他那么忠心,他肯定得对得起我噻!”他是在用他的忠心,换算着他认为应得的回报。
我没听说过他在所历单位的逸闻趣事,倒听说以前外出、下乡时,他不愿意跟一般人同车,而眼下是大伙都不愿意跟他同车……
邻床吃早餐的叽叽喳喳声吵醒了仁兄。
他睁开眼。他看见了我。倒是十分平静,眼里还闪过一丝苦恼人的笑。
“偶尔来这里走走,也好。至少会晓得身体,才是真正的本钱。”不晓得他是在说给自己,还是在说给我。
良久,他终于发出了喟叹,“我这辈子,算彻底玩完。”
我晓得他说的是个啥。绝对不是说的病痛。
于是,我给出了专门给他带来的良方:你不就是当年为了提前参加工作,把册子上(档案上)的年龄,改大了一岁吗?这次干部调整,你不就是因为虚大了一岁,退休前干不满一届,而担心退二线吗?其实这个好办,你去你档案袋里,查查你当年读初中时写的入团申请书,那个岁数跟落款时间,会证明你的真实年龄,组织上也会认可的。
立竿见影!仁兄的眼里一下子惊现了亮光,嘴里也开始碎碎念:“是吗是吗?我还有希望还有希望?那,我得赶快好起来赶快好起来……”
退出病房,一路上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真正的好心人。
一夜长吁短叹。
我提前赶到了市看守所。今天见一面后,我那兄弟就要遭发配去外地监狱了。
来这里探望的人,还多。有男,有女,有年老的,有年轻的,还有碎娃。都是沉默寡言,都是一脸恓惶。
我们扫健康码,登记,到高墙下的一扇窗口排队办手续,等待安排会见。
我们看上去都是好人,却都有着已成罪犯的亲朋、好友。
我们就这样在这样的时间,到这样的地方,来办这样的事情。
看守所高大的铁门,只对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开放。人进去后,关上;人出来后,也关上。会见室则在左侧,从一扇小门进去,那其实就一间狭窄的偏房,中间被一道铁栅栏和厚玻璃严严实实地隔开,唯一连接内外的是几部对讲电话。
隔离栏这边,是外面;那边,就是里面。那里面其实啥也没有,就一堵白墙和一道小门。这边,还有人头攒动、耳言低语跟焦躁急切的心跳,那边就只有空气,而那空气也仿佛凝重如墙。
来了。一个着制服的管教,领来三个着号衣、剃光头、戴手铐的罪犯,先一声令下,让他们在小门处立正站好,再一声令下,让他们进屋接受会见。三个罪犯都规规矩矩,规矩着手脚,规矩着身子,规矩着脸色跟眼神。我那兄弟矮矮小小的,显得特别规矩。
我俩赶紧抓起面前的对讲电话,还没开口,眼神就碰上了,居然碰出了一脸会心的笑。
我这兄弟,只是帮我开过两年车,那时我领受着单位上沉重的广告创收任务。他陪着我起早摸黑四处游说,变着法子把人家包包头的钱,说进自己单位的账户。我们少不了陪吃陪喝陪唱,也少不了遭遇冷漠遭遇白眼,甚至遭遇鄙夷。可他当过兵,懂规矩,懂自律,把我当兄长照顾,我也把他当兄弟对待。
这样的一个兄弟,这次却在激情之下,犯下大错——砍人!还好,只构成了轻伤,遭判刑八个月,还赔了一万多元钱。起因其实很简单:几个人打牌,与人起了口角,对方言语恶毒,且句句都是骂的他妈。他自首时说,“他伤到了我的底线。”
我清楚,他的妈年纪轻轻就守寡,不晓得经历了多大的苦难,才把他们三兄弟盘大。
东聊西聊,最后递进去一句“等你出来后,我们到太阳坝去喝酒”,会见就匆匆结束了。
走出会见室,走进明丽的阳光跟流畅的空气里,我突然问起了自己:假如有人那样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那样的一个妈,我会咋办?
我把自己给问住了。
我确实不晓得自己会咋办。
一夜清泪涟涟。
似乎睡了,其实醒着。窗外有风,有雨,不急不缓,嘀嘀嗒嗒。点燃一支烟,才觉出是还被过生日的酒醉着。烟熏火燎间,才觉出自己的醉生,原来是因为有一个叫雁的老哥,还躺在殡仪馆在等着我去送他。
没有一个生日,过得这样别有滋味;没有一个哥们,走得如此牵肠挂肚。
想起一首童谣:雁鹅扯长,扯烂衣裳。回去补起,又来扯长……那个叫雁的老哥还真就是那只雁,还真就是那样一次次把“衣裳”补起,又一次次将自己的生命线扯长又扯长。
老哥下过乡,顶班进过要死不活的小微企业。后干脆炒掉饭碗,自己支起个摊摊扒食,很快倒闭后,他便只身出门,浪迹于莽莽秦岭、迢迢云贵、茫茫两广、悠悠京师……还去过香港,竟是抱着车用充气胎硬游过去的。结果当然是遭到强制遣返。
他如此折腾自己,居然是为了文学!“我把生命化作尺子,丈量人类的历史;我把鲜血铸成文字,咀嚼民族的苦难!”原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要在有生之年闹出一部拯救全人类的大部头来。
我是他的另类“岁寒三友”:茶友,酒友,烟友。他每次回资阳,必定兴冲冲联系我,我则首先请他喝茶,再把酒给他备够。烟,我每抽时必定递给他一支,他却不会回递给我,因为他的烟实在是太孬。
我也去看过他两回。
一回是他还在北漂,就相约在天安门广场,国旗下。他应该才从靠蜂窝煤球取暖猫冬的小屋子出来不久,一副面黄肌瘦、昏头涨脑的样子。我给他带去了一笔稿费,三四十元吧,觉得就那样拿不出手,便加成一百元。我还刚把那张百元大钞摸出来,他的眼里突然一亮,赶快一把抓了过去。当时我脸上在笑,心里却在想:这样一个人,当他从你身边捱过时,你会晓得他居然还在帮你思索人生吗?
另一回就是前不久,他已像一叶风筝飘落在了钦州港。那时他已完成一百二十万字的初稿,并已写完了后记,一停笔却开始咯血。当时还并不为他担心个啥,就是很想去看看他,见到后也只是觉得他身体确实已不如从前。他陪我夜游仙岛公园,在红树林间放飞他一生孜孜追逐、苦苦呵护的自由心灵。我陪他在三娘湾枯坐沙滩,面朝大海,默默发呆。
仅三四个月后,他回到资阳,不想竟成了落叶归根。
我俩是有约的:今后走时,用自己的书砖做枕头。这老哥没有忘记。他一回来,就把书稿托付给一个叫朝军的老兄,请他做成五卷本。当朝军兄把那耗费他一生的枕头,抱来放在他耳畔时,我仿佛看见一滴清泪,悄然溜出了他的眼角。
给他垫上那样的枕头,把他送进火化车间,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就那样,这个叫雁的老哥仿佛确实化作了一只雁,展开翅膀,一飞冲天。
火化车间的大墙上,居然大幅书写着泰戈尔的一句诗:生如夏花之绚丽,逝如秋叶之静美。
这个叫雁的老哥,夏花过吗?绚丽过吗?秋叶了吗?静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