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到付现
斯科特·卡尼

阿肯夏不孕诊所的宿舍,位于印度阿南德。这些代孕者在九个月怀孕期间,一直受到严密的看守,生产时往往采取剖腹产。代孕者的家人被允许偶尔前来探视,屋子里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台播放着古吉拉特语肥皂剧的电视机。国外的求子夫妻支付诊所约一万四千美元,代孕者可赚得6000美元左右。有报道指责阿肯夏不孕诊所几乎无异于婴儿工厂。我问诊所创办人派特尔,她对那些批评有何看法,她回应道:“全世界的人都会指责我。女人会指责我,男人也会指责我,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一直回应这些人。”
她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似的,接下来20分钟都礼貌地回避我的问题。当我再度问她宿舍的事情时,她就直接把我送出了门。不过,像阿南德这样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帮忙,要查到那些妇女的下落也不是难事。
户外活动是禁止的
离诊所约一英里远的僻静街道上,有一间政府的食品配给店,负责发放补贴大米给无数的贫困户,店铺对面是一间外观矮宽的水泥平房,被混凝土墙壁、带刺铁丝网和铁门包围着,警方曾将这栋平房当成仓库,用来存放警方突袭时缴获的私酒。
现在,这栋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诊所两栋代孕者宿舍的其中一栋。在这里,孕母虽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离开。这些妇女全都已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身体的舒适,进入印度迅速发展的医疗与生育旅游业,成为孕母劳工,整个怀孕期间都要被关在这里。一位看守的穿着看似官方制服,携带竹杖,在前门那里监视每一个妇女的行动。家人很少会过来看她们,但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过来。
在这里,户外活动是禁止的,就算只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过警卫那关,她们必须先在诊所预约,或经过看守特别许可才行。她们用自由交换得来的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就其可怜巴巴的生活水准而言),不过诊所的国外顾客都很明白,那样的金额简直就是剥削。诊所的主要顾客都来自印度境外,阿南德市的其中三家膳宿公寓,经常会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预订。
我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间平房前。接着,我露出友善的微笑,以坚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顺利经过守门人。在膳宿公寓的主要住房里,约有20名穿睡衣的妇女正闲着没事做,她们各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同时在用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和一点英语仓促地交谈着。慢吞吞的吊扇搅动着死气沉沉的空气,一台电视放在角落里,这是我能看见的唯一娱乐方式,电视上正播放着古吉拉特语肥皂剧。一堆小铁床摆放得有如迷宫阵,占据了这个大小如教室的房间,还有一些铁床散放在走廊上,以及楼上的几个房间。鉴于这里住了这么多人,倒也不算凌乱。每位代孕者都只有几件私人物品,也许少得刚好可以塞进儿童背包里。走廊另一端是一间食品储备充足的厨房,一名兼作居家护士的服务员正在准备午餐,是咖喱蔬菜佐烤饼。
这些妇女看到有访客来,又惊又喜。其中一位告诉我,很少有白人会出现在这里。诊所不鼓励客户与代孕者有私人关系,这样等到交出婴儿时,事情会容易些。
我在翻译的帮助下,跟那些妇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个性聪明热心、处于怀孕初期的狄可莎,自愿充当发言人,并自我介绍说她其实以前是该诊所的护士。她离开家乡尼泊尔,抛下了两个学龄孩子,来到阿南德找工作。她要把赚来的钱用在孩子的教育开支上。狄可莎说:“我们很想家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待在这里,可以让想拥有家庭的女人能够拥有一个家。”她说,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妇女每个月可收到50美元,每3个月可收到500美元,剩下的生产时结算。
她们都说,一个成功的阿肯夏代孕者可赚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怀的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还会再多一些。(另外两家以外国夫妻为服务对象的印度代孕诊所告诉我,他们会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产的话,代孕者也可保留流产前收到的钱款。不过,要是她选择堕胎的话(合同允许堕胎),那么就必须赔偿诊所与客户的所有费用。在我拜访的所有诊所当中,没有一位代孕者选择堕胎。
狄可莎是我见过的阿肯夏代孕者当中,唯一一个算得上受过教育的。代孕者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数是看了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才知道这家诊所会付现金给愿意代孕的妇女。
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是唯一一家把代孕者关起来的诊所,其给出的理由是有助于医疗监测,而且也可以为妇女提供比其家里更好的条件。26岁的加州主妇克莉丝汀·乔丹便是因为得知有些诊所会雇用“基本上极为贫穷且完全是为了钱才代孕的妇女”,所以选择了一家德里的诊所,据说该诊所招募的是受过教育的代孕者,而且不會把孕母关起来。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者跟我说,若是她们大着肚子回到家乡肯定会招来不少闲言闲语。但即使如此,宿舍里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孕母,对于这整个安排似乎没有感到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边,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红色睡衣被撑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个金的带盒式坠的项链。她的年龄看起来比别人大,神情也更疲累。她跟我说,多年来,这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代孕。除了偶尔去做产检外,她将近三个月都没离开这栋建筑了,也没人来看她。不过,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体力劳动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问她对整个代孕经历有什么看法,她说:“如果流产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全额报酬,我不喜欢那样。”不过,她说能住在这里,不是住在诊所的另一间宿舍,就谢天谢地了。她说的那间宿舍就位于几个城镇外的纳迪亚德,环境没那么好。我问她,交出婴儿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回答,剖腹产会让她元气大伤。巴娜说:“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个月休养,等身体好了再回家。”我采访过的代孕者当中没一个是选择阴道分娩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剖腹产对婴儿造成伤害的风险较高,孕妇在生产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增加两至四倍,但是医生还是极为依赖剖腹产。毕竟,剖腹产比阴道分娩要快得多,而且可安排时间。
另一位孕妇加入了我们的交谈,她有着深棕色的眼睛,穿着绣了粉红色花卉的穆穆袍。我问她们,会不会觉得交出新生儿是很难的事情。这位孕妇说:“或许放弃婴儿还比较容易,毕竟新生儿长得不像我。”
2002年时,印度让代孕合法化,这是印度政府促进医疗旅游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新政策生效,私人资金开始流入印度,推动了服务外国人的世界级医院的兴起。在印度可低价孕育胎儿,不会受到政府官僚作风的阻碍,这个消息传开,促使印度代孕旅游业稳定成长。从体外受精到生产的整个过程,诊所收取1.5万至2万美元的费用;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有偿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价却是5万至10万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险会出这笔费用。德里的代孕顾客乔丹说:“印度的优点在于妇女不会抽烟喝酒。”即使美国代孕合同也大多禁止代孕者抽烟喝酒,但乔丹说:“我比较相信印度人说的话,美国人比较不可信。”
虽然难以取得较准确的数据,但是现在印度代孕服务每年起码会吸引数百名西方客户。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这一间不孕诊所就已经通过代孕者,让至少232名婴儿诞生在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诊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者。派特尔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妇女来她的诊所,希望能成为代孕者。同时,印度的生育诊所起码还有350家,可是自从政府不追踪代孕产业的情况后,已经很难查出实际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务。
孟买的希拉南达尼医院夸口自家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代孕项目,并训练外部的不孕科医生识别及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妇女。医院网站上的一个网页宣传着授予经销权的机会,宣称印度各地想创业的生育专家如欲设立有孟买背书的代孕机构,都可以跟院方联络。印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角色类似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只是权力小多了,实际上没什么执法能力。据它预测,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务在内的医疗旅游产业将可创造23亿美元的年收益。德里的不孕科医生阿努普·古普塔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型的领养方式。”
尽管预测这是一个会大幅增长的产业,但是印度官方并未监管代孕产业。印度政府对于代孕者的诊疗事宜,并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邦政府或国家当局也没有权力管制代孕产业。虽然诊所基于经济诱因,会确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诊所若想缩减代孕者费用与产后照护以降低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而且出事的话,也没有法规确保他们会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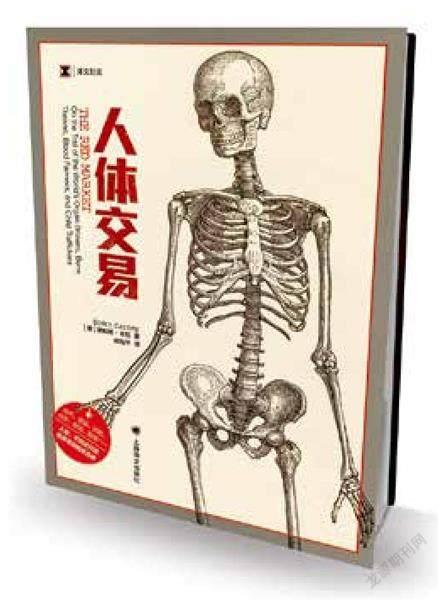
(责编:栗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