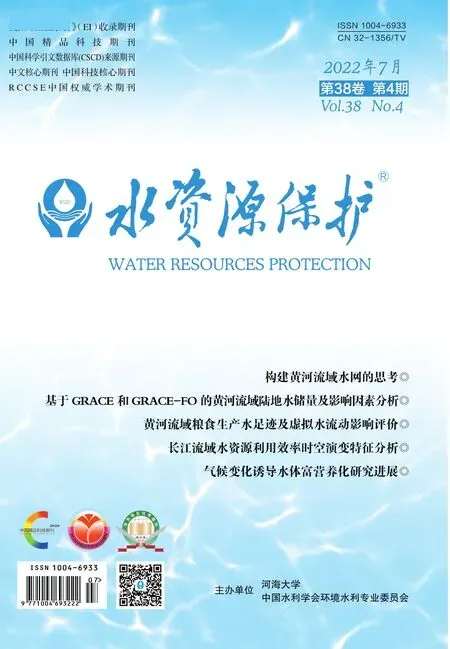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
廖迎娣,范俊浩,张 欢,张诗敏,陈 达
(1.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8)
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岸线利用率高、人类开发活动高度密集[1-2],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生活、工农业生产污染物大量进入河流区域,河流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3]。在此背景下,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人水和谐,加强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议题[4-5]。
生态护岸、生态输(调)水和磁化诱导等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已成为目前研究热点[6-7],其中,生态护岸是集防洪、景观、社会和生态为一体的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在河流治理工程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8-9]。但是,针对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或修复效果的评价还缺少有效的方法。基于此,本文采用频度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结合长江下游平原河网特点,对现有关于生态护岸、河流生态系统评价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筛选关键评价指标,构建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为实现生态护岸效果的定量化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方法
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实质上是评价生态护岸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的效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体系构建和指标选取过程中应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10]。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级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代表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准则层是对目标层和指标层之间影响机制的分类概括和解释说明[11];指标层则是由多个能够直接反映河流生态系统状况的指标组成。根据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方式以及健康河流的特征,本文提出以水质状况、生物状况、水文特征、地貌特征和社会经济5个方面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在此基础上分别确定关键性指标,以全面评估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
2 评价指标的选取
评价指标的筛选包含3个步骤:①指标梳理。在查阅2007—2021年发表的80余篇与河流生态健康、生态护岸、河流生态修复效果和水生态文明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出具有代表性且包含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共55篇,涉及评价指标共222个。②初步筛选。按照已构建的准则层将上述评价指标进行分类,以指标采用频次代表该指标的认可度,采用频度分析法筛选出采用频次不少于4次的指标作为候选指标。③适应性遴选。遵循指标选取原则,根据指标的内涵对候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避免各指标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或表达重复。
2.1 水质状况
水质状况指标反映生态护岸对河流水质的影响程度以及自净能力的恢复程度,经过初步筛选共有溶解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生化需氧量、总氮、河道水质类别、酸碱度、高锰酸盐指数、重金属、饮用水安全保证率、底泥平均污染指数、河道内底质和大肠杆菌群等15项候选指标,各指标对应采用频次分别为20次、17次、16次、15次、11次、7次、6次、5次、5次、5次、5次、5次、4次、4次和4次。优先选取采用频次不少于6次的指标,即溶解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生化需氧量和总氮7项指标。其中,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属于综合性指数,其内涵包含其他6项指标,能够反映河流水质的总体状况,但它在揭示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关联度上存在困难[12];溶解氧、氨氮等6项理化参数指标能直观反映河流健康的问题所在,进而能够对生态护岸的维护与管理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如溶解氧的高低与大型无脊椎动物数量密切相关[13];氨氮会对鱼类造成摄食降低、生长减缓和组织损坏等危害,与鱼类的存活状况相关[14]。由于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河流流速缓慢,水动力条件较弱,水体污染以富营养化为主[1],上述6项指标可以反映河流水体营养化和自净能力。综上分析将水质状况关键指标定为溶解氧(C1)、氨氮(C2)、化学需氧量(C3)、总磷(C4)、生化需氧量(C5)和总氮(C6)6项,数据的采集与标准可参照SL 219—2013《水环境监测规范》以及GB 3838—2002《地表水质量标准》。
2.2 生物状况
生物状况指标主要反映生态护岸对鱼类、底栖动物、浮游生物和藻类等生物的存活状况的影响,经过初步筛选共有底栖动物多样性、浮游植物多样性、浮游动物多样性、鱼类多样性指数、珍稀水生物存活状况、鱼类完整性指数和固着藻类多样性等7项候选指标,各指标对应采用频次分别为23次、22次、17次、8次、8次、7次和6次。在河流生态系统食物链中,底栖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鱼类从属于不同的层次,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生命形态和营养类型[15]。其中,浮游动物多样性与底栖动物多样性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宜同时作为评价指标[16];底栖动物生命周期较长,能反映长期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的扰动程度[17],因此保留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标,剔除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标;珍稀水生物存活状况在大部分地区缺乏历史资料的参考,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该类生物难以捕捉,不符合可操作性原则,予以剔除;鱼类多样性指数和鱼类完整性指数均受渔民滥放、滥捕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并不能客观反映生态护岸对河流鱼类生存的影响,且后者是包括物种丰富度指标、群落结构组成指标等16项分指标的综合性指标,其获取过程极其烦琐,因此这两项指标均剔除。综上分析,将生物状况关键指标定为采用频次较高的底栖动物多样性(C7)和浮游植物多样性(C8)2项,两者均可采用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进行计算:
(1)
式中:H为Shannon-Weaner物种多样性指数;K为总的物种数;Pk为物种k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2.3 水文特征
水文特征指标主要反映生态护岸对河流水文要素的影响,经过初步筛选共有生态流量保障程度、流速分布、流量过程变异程度、水土流失率、水温变异程度和水量等6项候选指标,各指标对应采用频次分别为25次、11次、11次、9次、8次和6次。其中,生态流量保障程度出现频次最高,该指标主要通过河流长序列水文数据来反映河流的水文特征,且能够同时表征流量过程变异程度和水量,因此剔除流量过程变异程度和水量这两项指标。由于建造生态护岸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河岸免受冲刷,所以水土流失在本文所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具有代表性。综上分析,将水文特征关键指标定为生态流量保障程度(C9)、流速分布(C10)和水温变异程度(C11)3项。
生态流量是维持水生生物存在、污染物稀释自净、河流水沙平衡和生态系统平衡所需要的最小流量[18],而在高度人工化城市中生态流量是指能保障城市河流连通性和景观娱乐等功能正常发挥的流量条件[19],应根据研究区域的特征,评估计算生态流量。考虑到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的特点,生态流量保障程度可用评估年河道实测日均流量大于生态基流的天数占总天数的比例来表征[20],计算公式如下:
C9=(ds/365)×100%
(2)
式中ds为评估年实测日均流量达到河道生态流量的天数。
河流生态环境中不同流速条件更利于不同生物群落的聚集[21],且流速分布与河流物质的交换扩散以及泥沙输移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河流的自净能力[1]。流速分布可根据河流断面流速分布的差异程度进行定性描述。
水温是水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水温的改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河流水质状况和水生生物状况[17]。水温变异程度可由评估年逐月实测月均水温与多年平均月均水温变异最大值表示[22],计算公式如下:
(3)

2.4 地貌特征
地貌特征指标主要用以表征生态护岸对河岸带与河道自然结构形态特征的影响,河流地貌直接影响着水生生物栖息环境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河流生物的种类及其群落的结构组成,是维持河流健康的重要前提[23]。经过初步筛选共有河岸带植被覆盖率、纵向连通性、岸坡稳定性、蜿蜒度、河床稳定性、护岸形式、天然湿地保留率、河岸植被结构完整性、河道渠化程度、岸坡倾角、河岸带宽度、河岸缓冲带宽度、横向连通性、水系连通性、岸坡抗蚀性、岸坡高度和渗透性等17项候选指标,各指标对应采用频次为30次、20次、20次、15次、14次、10次、9次、8次、8次、7次、7次、6次、5次、5次、4次、4次和4次。由于指标较多,优先选用认可度较高、采用频次不少于8次的指标。其中,河岸带植被覆盖率与河岸植被结构完整性均表征河岸带植被状况,内容存在交叉,选取采用频次较高的河岸带植被覆盖率指标;生态护岸应以保证岸坡稳定为前提条件进行生态修复,岸坡稳定性指标不具有代表性,予以剔除;护岸形式和河道渠化程度的内涵有所关联,均反映河岸渠化或硬质化的影响,选取采用频次较高的护岸形式指标;天然湿地保留率属于面源指标,不适用于评价河段尺度,予以剔除。综上分析,将地貌特征关键指标定为河岸带植被覆盖率(C12)、纵向连通性(C13)、蜿蜒度(C14)、河床稳定性(C15)和护岸形式(C16)5项。
河岸带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岸带植被覆盖率是表征河岸带植物群落存活状况的量化指标,能间接反映河流的水土保持度和生境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C12=(Sp/S)×100%
(4)
式中:Sp为河岸带植被占有面积;S为河岸带总面积。
河流物质循环、信息交换和生物迁徙在纵向上的畅通程度影响着水质、生物群落种类等参数的时空分布,纵向连通性表征河流纵向连通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13=N/l
(5)
式中:N为研究河段拦河建筑物的数量;l为研究河段沿河流中线的实际长度。
弯曲是河流的自然属性,河流的蜿蜒曲折有利于流速的多样性分布、多种生境的形成和水生生物群落的发展,蜿蜒度表征河流的弯曲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14=l/L
(6)
式中L为研究河段河流的直线长度。
较为稳定的河床有利于水位的稳定,能够营造良好生物栖息地,河床稳定性是表征河床稳定程度的指标,反映河床在纵向、横向和垂向维持自身结构形态平衡的能力。该指标为定性指标。
不同的护岸形式对两栖动物影响极大,最优形式为对河流横向连通无干扰的护岸,最差则为直立式硬质护岸。护岸形式为定性指标,反映陆地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通道的顺畅程度。
2.5 社会经济
河流生态系统不但承载着自然服务功能,同时也承载着社会服务功能[24],社会经济指标主要反映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在社会服务功能以及经济效益两方面的影响。经过初步筛选共有防洪能力、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建造维护成本、社会公共认可度、文化美学功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率、供水保证率、休闲娱乐功能、通航保证率、可亲水度、景观舒适度、排涝能力、维护成本、建筑材料环保性和景观多样性等15项候选指标,各指标对应采用频次分别为21次、15次、11次、10次、8次、8次、7次、7次、7次、6次、6次、6次、5次、5次和4次。优先选取采用频次不少于8次的指标。防洪能力一般由河流达标堤防长度与河流总堤防长度的比值来表示,而生态护岸的建设需满足防洪要求,所以该指标予以剔除;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和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率是指流域内各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的总量占流域内水资源的比重,与本评价指标体系所针对的河段研究尺度不符,数据不易获取,予以剔除;社会公共认可度、文化美学功能都表达了群众对河流生态景观美学功能的满意程度,均为定性指标,为了尽可能减少定性指标数量以降低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社会公共认可度来涵盖其他指标的功能。综上分析,将社会经济关键指标定为建造维护成本(C17)和社会公共认可度(C18)2项。
景观化是生态护岸在保障水安全和生态健康基础上的一项有益补充,提升了河岸水景观效果,但过度景观化却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良现象,因此需定性分析工程建造维护成本是否经济合理。
社会公共认可度是指居民或游客对河岸带景观、休闲娱乐等设施的满意程度,可以从景观的文化美学性、休闲娱乐丰富度和景观多样性等方面进行现场调研打分。该指标为定性指标。
3 评价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从水质状况、生物状况、水文特征、地貌特征和社会经济5个方面构建包含13项定量指标与5项定性指标的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评价指数法定量评价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最终可得到生态护岸综合影响指数:

图1 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7)
式中:I为综合影响指数;Wi为第i个准则层权重;wj为第i个准则层中第j个指标在该准则层所占的权重;Fij为第i个准则层中第j个指标的赋分值;ni为第i个准则层指标数。
各指标赋分等级定为理想状态(4分)、健康(3分)、亚健康(2分)、不健康(1分)和病态(0分)共5个等级。在对各指标进行赋分时,应尽量参照国家或行业明确的适用标准,确定各等级的赋分区间或定性评价标准;若无相关标准可参考,则可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区域规划要求或采用专家咨询等方法来确定。
在实际工程评价过程中,应首先对上述18项指标进行实测、定量计算或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赋分,再选择合适的赋权方法确定各准则层和指标的权重,按照式(7)计算出生态护岸综合影响指数I。根据Ⅰ级(3.2 本文采用频度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构建了水质状况、生物状况、水文特征、地貌特征和社会经济5个方面18项指标的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各项指标的赋分方法和生态护岸综合影响指数计算方法以及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等级标准,可为长江下游平原河网地区生态护岸建设与评价提供科学手段。生态护岸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过程,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研究区域的特点,充分分析各项指标的敏感性,合理确定指标和准则层的权重,准确评价生态护岸对河流健康的实际影响。4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