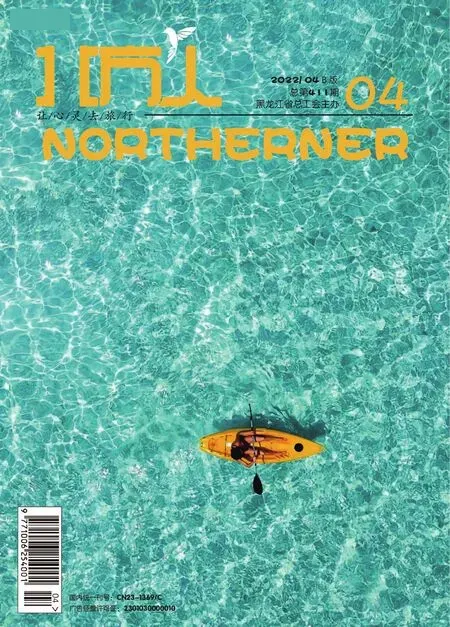捡垃圾的小女孩
文/梁晓声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元月下旬的一个日子,刮着五六级风。家居对面,元大都遗址上的高树矮树,皆低俯着它们光秃秃的树冠,表示对冬季之厉色的臣服。十点左右,商场来电话,通知安装抽油烟机的师傅往我家出发了。
前一天我就将旧的抽油烟机卸下来丢弃在楼口外了。它已为我家厨房服役十余年,油污得不成样子。一除去它,上下左右的油污彻底暴露,我得赶在安装师傅到来之前刮擦干净。我想到了用湿抹布滚粘了沙子去污的办法,在外边寻找到些沙子用小盆往回端时,见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站在铁栅栏旁。我丢弃的那台脏兮兮的抽油烟机,已被她弄到那儿。并且,一半已从栅栏底下弄到栅栏外;另一半,被突出的部分卡住。女孩儿正使劲跺踏着。她穿得很单薄,衣服裤子旧而且小。脚上是一双夏天穿的扣绊布鞋,破袜子露脚面。两条齐肩小辫,用不同颜色的头绳扎着。她一看见我,立刻停止跺踏,双手攥一根栅栏,双脚蹬在栅栏的横条上,悠荡着身子,仿佛在那儿玩的样子。那儿少了一根铁栅,传达室的朱师傅用粗铁丝拦了几道。对于那女孩儿来说,钻进钻出仍是很容易的。分明,只要我使她感到害怕,她便会一下子钻出去逃之夭夭。而我为了不使她感到害怕,主动说:“孩子,你是没法弄走它的呀!”
她却说:“是一个叔叔给我的。”——又开始用她的一只小脚跺踏。
要是有什么“叔叔”给她的话,那么只能是我。我当然没有。
她弯下腰去,一手捂着脚腕了。破裂了的塑料是很锋利的。我说:“唉,扎着了吧?你倒是要这么脏兮兮的东西干什么呢?”她说:“卖钱。”其声细小。说罢抬头望我,泪汪汪的。接着低头看自己捂过脚腕的小手,手掌心上染血了。我端着半盆沙子,一时因我的明知故问和她小手上的血而呆在那儿。她又说:“我是穷人的女儿。”我张张嘴,竟不知再说什么好。而商场派来的师傅到了,我只有引领他们回家。他们安装时,我翻出一片创口贴,去给那女孩儿,却见她蹲在那儿哭,脏兮兮的抽油烟机不见了。我问哪儿去了?她说被两个蹬手板车收破烂儿的大男人抢去了。我替她用创口贴护上了脚腕的伤口,又问:“谁教你对人说你是穷人的女儿?”她说:“没人教,我本来就是。”我不相信没人教她,但也不再问什么。
我将她带到家门口,给了她几件不久前清理的旧衣物。她说:“穷人的女儿谢谢您了,叔叔。”我兜里有些零钱,本打算掏出全给了她的。但一只手虽已插入兜里,却没往外掏。那女孩儿的眼,希冀地盯着我那只手和那衣兜。我说:“不用谢,去吧。”她单肩背起小布包下楼时,我又说:“过几天再来,我还有些书刊给你。”
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去散步,刚出楼口又一眼看见了她。仍在上次见到她的地方,她仍然悠荡着身子在玩儿似的。她也同时看见了我,语调亲昵地叫了声叔叔。我驻足问:“你怎么又来了?”她说:“我在等您呀叔叔。”我说:“等我?等我干什么?”她说:“您不是答应再给我些您家不要的东西吗?”我这才想起对她的许诺,搪塞地说:“挺多呢,你也拎不动啊!”“喏”——她朝一旁翘了翘下巴,是一块带轮子的车底板。显然也是别人家扔的,被她捡了。之后,她用一双大眼瞪着我强调说:“我都等了您几个早晨了。”我终不忍令她太过失望,再次使她满足……我第三次见到那女孩儿,日子已快临近春节了。我开口便道:“这次可没什么东西打发你了。”女孩儿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
她说从我给她的旧书刊中发现了一个信封,怕我找不到着急,所以接连两三天带在身上,要当面交我。那信封封着口,无字。我撕开一看,是稿费单及税单而已。她问:“很重要吧?”我说:“是的,很重要,谢谢你。”她笑了:“咱俩之间还谢什么。”而我却看出了破绽——封口处,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脏手印儿,而我夹在书刊中的稿费单是从不封口的。好一个狡黠的“穷人的女儿”啊!她对我动的小心眼令我心疼她。
“看!”——她将一只脚伸过栅栏,我发现她脚上已穿着双新的棉鞋了,摊儿上卖的那一种。并且,她一偏她的头,故意让我瞧见她的两只小辫已扎着红绫了。我说:“你今天真漂亮。”她悠荡着身子说:“叔叔,初一早晨我会给您拜年。”
初一我起得很早。我挺希望一大早走出家门,一眼看见一个一身簇新,手儿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两条齐肩小辫扎得精精神神的小姑娘快活地大声给我拜年。一上午,我多次伫立窗口朝下望,却始终不见那“穷人的女儿”的小身影。下午也是。到今天为止,我再没见过她。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