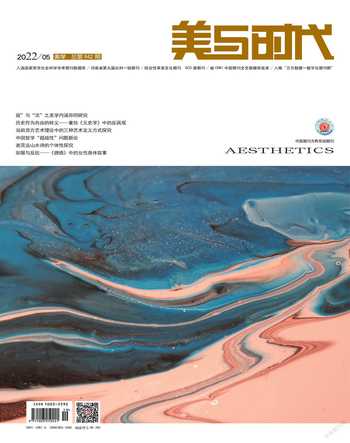论《文选》对《九歌》的选录
摘 要:《文选》整体的选录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另一个重要标准是风格的雅正。此外,《文选》的文章选录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从《九歌》六篇具体来看,萧统认为这六首符合骚体的整体风格,作为典型的代表以明“骚”“赋”之别,同时出于对“翰藻”理想的追求,从艺术水平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筛选和取舍。
关键词:文选;九歌;萧统
《文选》由南朝梁的萧统组织文人编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收录周代至六朝梁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如此规模的整理、选录、保存,可谓文学史上的盛事。萧统既是南朝梁的储君(梁武帝的长子,天监元年十一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又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梁书》记载他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1]165,无疑为他喜好、鉴赏文学有所铺垫。平日又广纳文学之士,以阅读和写作为闲暇之娱:“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1]167这两个身份成为了萧统编纂《文选》的重要基础和动因。
研究《文选》的“选学”同样是一门精深的学问,且自古就是显学。关于《文选》的版本、文献价值、文体分类和文学观、重要注本的价值等诸多问题,历代学者已有卓著的成就。由于《文选》是一部“选”集,篇幅所限不能把所有作品全都收进去,那就必然存在一个选录和取舍的标准问题。《文选》“骚”类下,共有17篇作品,分别是屈原的《离骚》《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辨》5首、《招魂》,刘安的《招隐士》(《文选》将《招隐士》的作者署名为刘安,另说为其门客淮南小山所作)。问题就在于,编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则或心理,将这17篇作品定为骚体的代表?更进一步,为何选取《九歌》而又只录其中6首,这6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因而获得了编者的青睐?虽然编者对《楚辞》和《九歌》并无明确文字的阐释,其中却暗含了某些评判,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阐释。
《文选》选录标准的问题,也是“现代文学选”的热门话题。孔令刚的《广角视域下的〈文选〉选录标准研究》[2]一文,全面而精准地梳理了《文选》选录标准研究的发展历程,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分为隋唐到清的萌芽期、清中期至20世纪前期的探索期、20世纪后期的兴盛期、进入21世纪后的新趋势等阶段,并点出了每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和观点,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根据此文的整理,可以发现,关于《文选》的选录标准,学者们首先关注到了编者萧统的文学思想,之后开始注意到时代和政治等其他因素,而近年来则越发注重拆分大问题,按照文类或作家进行细化,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得到了很多的成果。如《论〈文选〉对陆机诗歌的选录》《〈文选〉乐府诗选录情况及其乐府观念》《骚体的早期演变及〈文选〉选录标准》等文章。笔者正是沿着这一路径,从萧统的文学观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出发,具体探讨《文选》对《九歌》的选录情况。
要了解《文选》对《九歌》的选录,必须先了解萧统的文学观。如众多学者热烈讨论所明晰的,《文选》的编纂受多方面的影响,不可能是萧统的一人之力。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认为:“《文选》中对天监后期至普通中逝世的作家,其取舍似乎都与刘孝绰的爱憎有一定关系。所以,推测刘孝绰对《文选》的编定曾起过重要作用,应该是合乎情理的。”[3]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更为激进,甚至认为《文选》的实质性撰录者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4]。我们虽然要承认并研究刘孝绰等人在编纂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和体现的思想,但研究《文选》时谈到萧统的思想,其实就如研究《吕氏春秋》谈到吕不韦的思想、研究《淮南鸿烈》谈到刘安的思想一样,他们的名字实际上早就是集体创作者的代名词和一个符号,他们是这项事业的主持者和代言人。
关于萧统的文学观,从清朝的阮元开始就认为,《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義归乎翰藻”[5]4这十个字是对萧统文学观最直接的概括,也解释了选录的标准。同时,在《文选序》中,萧统直接指出了文学的审美功能,“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5]3!生活于齐梁时期的萧统,用这个比喻暗示了文学“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作用,这种功用完全与政治教化功能无关。而正如邵宗波、常佩雨《〈文选〉的选录标准复议》[6]等文章所述,如果我们细读《文选序》的原文,如果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奉为选录的唯一原则,是有断章取义、扩大文意的嫌疑的。其语境为:“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5]4这里的论述主体并非全部《文选》所收录的作品,而仅仅是针对“序述”“赞论”文体而言。前面萧统先言此为“括囊别集为书” [7]的总集,故不取经、史、子,而“序述”“赞论”为史论,原不该入选,但有的篇目较为突出,达到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程度,所以破例入选。
不过,既然“赞论”达到这个标准可以入选,那么本就属于别集中的作品若达到这个标准,就更应当入选,等于说这是一个文学作品入选的高标准。另外,萧统对于文学作品的“翰藻”,也就是文辞因素的重视,是可以见得的。结合萧统的事迹,他钟情于陶渊明的作品,为陶渊明录集、作序、立传。而陶渊明的诗文,看似天然去雕饰,却依然出于精心营造,称为“翰藻”亦可。又加之萧统自己的创作,主要以男女之情、游仙、宴游、闲适、述怀等为内容[8],文采堪称绮丽,也可以证明作为作家的萧统对“文”的看重。
当然,萧统文学家之外的政治人物身份,使他选录《文选》时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名字乃是国家延续之象征。《文选》在当时的性质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选集,要考虑到读者群体是待被教化的王朝子民。所以,“文”与“质”的矛盾再度凸显了出来,而且在萧统身上,这一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他对陶渊明虽然十分喜爱,却在《陶渊明集序》中批评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9]这些情况都体现出萧统对儒家文艺观的回护,甚至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文苑英华〉书》一文中,他直接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0]王运熙先生据此认为,“注意辞采、翰藻,是《文选》选录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还不能说是唯一的标准。《文选》选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注意风格的雅正”[11]。
另外,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文选》文体分类等方面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刘勰与萧统是同时代的人物,并存在交集,《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1]710。像殷孟伦先生分析道:“以《文选》所分的三十八类同《文心雕龙》所分的对照,很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致性。”[12]《文选》的文体分类是在继承了刘勰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改造,如《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的分类:“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1]40《文选》又细化为京都赋、郊祀赋、耕籍赋、败猎赋、纪行赋、游览赋、宫殿赋、江海赋、物色赋、鸟兽赋、志赋、哀伤赋、论文赋、音乐赋和情赋。殷孟伦先生又指出:“关于《文选》选录的作家,不见于《文心雕龙》的只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完全都有。”刘勰的年龄要比萧统大35岁左右,萧统与刘勰接触的时候,只有17岁。所以说萧统的文学观受到刘勰的影响,这种猜测是合理的。或者说,他们二人都处于一个文学大发展的时代,文学的新变十分迅速,他们共同受到时代的影响,开始探讨新的符合实际的文学理论,刘勰是利用文论来说明,萧统则是通过选集来体现。
具体到屈原的作品,《文选》对“骚”之独立性的确认,也可能来自于刘勰的启发。刘勰在《文心雕龙》已经指出,“骚”与“赋”是有区别的,他写《辨骚》主要论及屈原,而写《诠赋》则主要论及枚乘、司马相如等汉代作家。而《文选》则用分类整理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这是可以区别的两种文体,在“骚”类下只录屈原、宋玉和刘安的17篇作品。《文选序》对屈原的评价,同样透露出这样的思路:“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1]2这里特意点出“骚人之文”,是把屈原作为骚体的开山鼻祖来看待,屈原引领着“骚人”的风致。那么即是说,入选的《九歌》6首,在萧统眼里鲜明体现着“骚”的特征,是骚体的代表作。对比之下,在屈原的众多作品中,除了《离骚》全篇入选之外,《九章》只入选了1首,《天问》更是没有入选。可以说在萧统眼中,《九歌》是除《离骚》外最能代表骚体或屈原创作的作品,这一点与汉人对《楚辞》作品的排序是一致的。
那么萧统对于骚体的体认是怎么样的呢?李篮玉认为:“一是具备哀志伤怀的感情基调;二是文质兼备;三是具备社会教化功能。”并强调其抒情特征:“在所选作品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选录了《卜居》与《渔父》两篇作品。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用骚体文学的一个鲜明标志——‘兮’字,所以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骚体作品。但是《文选》仍然选入这两篇,说明比起形式,萧统更注重作品的内容与情感,尤其是楚辞独特的哀志伤怀的抒情特征。”[13]笔者基本认同这个观点。这样的体认与刘勰提出的“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14]一脉相承,《九歌》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伤情”,那么选为骚体的代表作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还需要注意到《文选》可能考虑了楚地的语言风格,屈宋毫无疑问是楚地文化的代表,淮南也与楚文化密切相关。他们作品中的楚地风范,以及完全不同于汉赋的表述系统和模式,应当同样是萧统认为的“骚”的特质之一。
我们也不能忘记萧统所重视的“翰藻”。本质上说,《文选》作为一部文学选集,虽然受到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但最为重视的还是这篇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精妙绝伦的文采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明确了这些问题,再观察《九歌》入选的六首,《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就多少能够理解萧统的意图。
没有入选的《国殇》,虽然文辞激荡、节奏铿锵,从文采的角度来看完全符合入选标准,但因为情感过于炽热、直露,有壮怀激烈的美感,与骚体的整体风格不符,不能作为骚体或屈原的代表作选录。《礼魂》则篇幅过短,很难看出实际的风格,所以也不予选录。《大司命》《河伯》《东君》三篇,也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大司命》《东君》主要凸显的是大司命主生杀的威严、神秘和太阳神的尊贵英武、灿烂辉煌,“哀志伤情”的因素相对少一些。而且从文学艺术水平的角度来讲,所入选的六篇确实都是佳作,尤其像《山鬼》《少司命》等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清代的蒲松龄《聊斋自志》开篇称:“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15]这是直接以《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作为屈原作品的象征。《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评为“千古情语之祖”[16]。至于《文选》对“雅正”的追求,与刘勰宗经的态度是类似的,是有可能随实际情况做出让步的,因此我们不能以雅正来理解《九歌》的入选。
总而言之,从《文选》整体的选录标准来讲,“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最基本的原则,同时,《文选》选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风格的雅正。此外,《文选》的文章选录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从《九歌》六篇具体来看,其一是因为萧统认为这六首符合骚体的整体风格,而且能够作为这种风格的鲜明代表,以明“骚”“赋”之别,这是对《九歌》“伤情”的抒情因素的再度确认;其二是出于萧统对“翰藻”理想的追求,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和鉴赏家,他从艺术水平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筛选和取舍,为后世的阅读、鉴赏做出了示范,同时也留待后人去进一步讨论、鉴别。
参考文献:
[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孔令刚.广角视域下的《文选》选录标准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20-125.
[3]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撰中几个问题的拟测[C]//郑州大学古籍所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4]清水凯夫.《文选》编辑的周围[J].韩基国,译.佳木斯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2):65-73.
[5]萧统.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邵宗波,常佩雨.《文选》的选录标准复议[J].许昌学院学报,2007(3):59-61.
[7]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5.
[8]艾初玲.论萧统、萧绎对“文质彬彬”论的认同与超越[J].阴山学刊,2007(5):37-40.
[9]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10]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155.
[11]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10-16.
[12]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J].文史哲,1963(1):75-82.
[13]李篮玉.骚体的早期演变及《文选》选录标准[J].文化学刊,2018(4):195-197.
[14]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4:22.
[15]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134.
[16]王世贞.艺苑卮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87.
作者简介:董方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