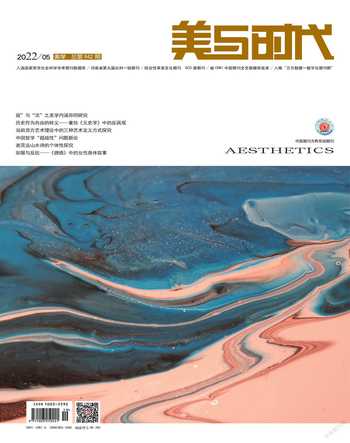再现的感官与表现的感官


摘 要:刁亦男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强化了感官叙事,感官不仅成为片中武汉“在地性”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同时,感官亦成为主人公生之欲望的表征,而连接电影“野鹅塘”和“梭罗河”共同构成的水的隐喻。借由感官叙事,电影在再现和表现两个层面上都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复归,并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作者性“再跨越”的路径变轨,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质感和更开阔的延展空间。
关键词:南方车站的聚会;在地性;隐喻;感官叙事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记忆叙事中的多模态问题研究”(XSP20YBZ169);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优秀青年)“认知诗学视阈下新生代导演艺术电影(2014-2018)叙事研究”(18B416)研究成果。
对于导演刁亦男而言,《南方车站的聚会》是一场比《白日焰火》更大的“冒险”。在获得银熊奖后,他显然不满足于在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黑色电影风格中继续“耕耘”,而决定将更贴近于现实的立足武汉的“在地性”,与更具世界电影风格的“作者性”融合起来。他在电影中同时强化了对现实的还原与超越,从而扩大了电影“再现”与“表现”之间的的张力。在这一过程中,包括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在内的感官叙事,都成为他最重要的叙事工具。
一、“可感”的在地性
《南方车站的聚会》英文名为《野鹅塘》(The Wild Gooes Lake),故事也围绕一个名为“野鹅塘”的湖区展开。虽然这一地区是虚构的,但并不影响其现实性。从刁亦男让桂纶镁(饰演刘爱爱)脱下“神秘女郎”的外衣,变成一个说着武汉方言,言行举止都表现世俗肤浅的陪泳女可见一斑。“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家乡是‘中间的地方’或者世界的中心。”[1]刘爱爱要周泽农向南逃,周泽农拒绝了。显然,这虽然是一部“逃亡”主题的电影,却并不着意于地理上的流动性,而是借助主要人物的移动,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展现“野鹅塘”这一意义的飞地的各个方面。正如麦克·克朗所言:“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2]“野鹅塘”作为一个隐藏在叙事情节背后的巨大能指,既以一种在地性的方式包容、吸纳人物的冲决、欲望和穷途,也经由人物充分表征,人物与之互为表里。在这一过程中,感官体验成为贯通人物与在地性空间的主要“桥梁”。
在电影中,来自中国台湾的桂纶镁说起了武汉方言,这和其表演一起构成了世俗化转向的一部分。但细究起来,桂纶镁说方言,与陈永忠在《路边野餐》(虽然他在本片中也客串演出)和汤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说贵州凯里话并不一样。虽然方言也在后两部电影中锚定了作为地方的“凯里”,但并非是在世俗化的意义上进行凸显,而是将凯里作为一个毕赣心中表现性的“世界”来描绘。换言之,“在地性”有两条路径,一条通往再现,一条通往表现。毕赣更偏向于表现的在地性,而刁亦男在本片中试图将再现与表现结合起来。
换言之,方言的可感只是对在地性的确认,而确认后对在地性的方向进行选择,则需要另外的感官叙事进行支撑。在电影结尾,有一出经典的“吃面”场景,刁亦男着墨甚多:刘爱爱带周泽农去小面馆吃面,饥饿到极点的周泽农面对一个地方日常性问题“吃面还是吃粉”置若罔闻,显然此刻生存的欲望压倒了日常口感的欲望。但当他吃了两口、稍稍缓解饥饿之后,马上仪式性地像一个吃辣的武汉人一样,抢过辣椒罐,舀了两勺辣子放进碗里。
这一场景由嘴部和手部的特写构成,是电影着力突出的部分。不难看出,通过对“本土口味”的图像性确认,刁亦男强调的是刘爱爱和周泽农“武汉人”的世俗身份。这与毕赣作品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性凯里人”大相径庭。这一区别与刁亦男的叙事设计密切相关:《南方车站的聚会》是建立在完整的叙事情节之上的电影,从整体上而言,它是偏向于转喻的而非隐喻的。如果电影中仍存在如《白日焰火》中“焰火”一般的隐喻的话,那隐喻本体也是“野鹅湖”这一空间本身。空间作为一个整体隐喻,剥夺了人物隐喻的功能,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人物必须以其叙事的现实性,牢牢吸附在空间中。
二、作为结构功能的感官叙事
当然,电影中的感官叙事并不仅限于再现真实。刁亦男面临的两难问题是风格与内容之间的平衡,“风格和内容是矛盾的。在追求风格的时候必然要损失内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暗合的”[3]。整个故事围绕偷车贼小头目周泽农“误伤—逃亡—夺赏—死亡”的情节展开,有完整的叙事逻辑。但刁亦男“作者性”的艺术创造,使得电影的叙事出现了一种“破坏性建设”——在这部以情节为主的黑色风格电影中,关键情节却被有意暗藏,造成一种影像上直接可感,但情节上却要咀嚼回味的层次感。正如案件的开始,是黄毛因为光线暗淡没有看到割头的叉车被撞身亡,和周泽农因为光线强烈没有看清而误伤,感官被置于“合理”与“意外”之间的模糊地带,成为驱动叙事发展的结构性要素。
在这一结构化的过程中,感官叙事呼应著人物动机的积蓄和冲突,成为其最后爆发的表征。在淑俊应爱爱之约与丈夫周泽农见面的场景中,有一个看似无用但精巧的调度:淑俊和爱爱一前一后与华华接头,华华正在小广场跳广场舞。淑俊越过华华,在前面不远处买汽水,爱爱加入华华的广场舞群。随即华华离开舞群,走到淑俊背后的摊贩前。此时淑俊继续在小巷前行,而爱爱也离开舞群,来到淑俊刚才的位置。就在淑俊将要消失在巷尾的时候,路边一个“炸米泡”①的刚好出炉,“嘭”的一声巨响,让同框三人同时悚然一惊。
这一设计非常精巧自然,它让流畅的视觉调度因为一个意外的声音而建立起了更有机的联系——三人内心的紧张感被巨响所点破,背景中小巷深处的淑俊和前景中背向而立的华华与爱爱,三个人的动机由这一意外的声音带来的惊扰在画面中同时呈现。观众可以看到,在一个三角形的构图中,声音巧妙地建构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合谋”的空间。然而,感官所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远不止于此——同样是这一声音,在另一叙事线条中,惊扰了前来接头的周泽农小弟,让他们误以为是埋伏的枪声,放弃接头落荒而逃,使叙事出现了关键的转折。
这一被反复使用的听觉符号,成了“撬动”叙事走向的意义节点。刁亦男明智的一点在于他将其作为“因”而非“果”呈现。感官要素是一个“路标”,指向的是人物幽深的心灵世界。当完成这一对叙事走向的控制后,感官叙事便悄然消失,不留痕迹。正如电影结尾那意味深长的一幕:爱爱和淑俊拿到赏金,两人紧搂着赏金并肩而行,动作僵硬、表情紧张,如同捧着周泽农的骨灰盒。直到路边洗车的水花飞溅到身上,浇醒二人,方才相视一笑,仿佛卸下重担。继而目光又分开,望向别处,让哀伤以不同的方式占据自己的身体。感官就像潜入人物内心水下世界的探照灯,让叙事从情节的表层沉入内心的深层。通过这样自然而不经意的“变轨”,电影的叙事以感官的凸显为节点,呈现出一种不断浮潜的“打水漂”一样流畅灵动的风格。
感官的,又非纯感官的,对这一尺度的把握让刁亦男在自身风格中,注入了浓郁的人文色彩。与《白日焰火》中那些不置可否、不可进入,而更像是欲望驅动的主体不同,本片的人物是可揣摩的,人物的动机在感官的衬托下有一条自洽的线索。而刁亦男的作者性表现在他通过对人物动机的“隐”和“显”的控制,以一种错综复杂的叙事线条走向可解释的结局。
三、作为隐喻的感官
感官叙事在片中的“升格”不仅限于叙事上的结构化,同时也融入了整体隐喻的建构中。显然,水构成了电影最大的隐喻,但这一隐喻是由“野鹅塘”和“梭罗河”两个相对的意象共同构成的。野鹅塘是不可逃离之地,梭罗河则代表自由。在片尾曲中,胡歌(饰演周泽农)亲自演唱了《美丽的梭罗河》,强调“逃离”的意义,但这首歌在片中第一次出现却更引人深思。
在野鹅塘边,逃亡的刘爱爱和周泽农慌不择路进入一个杂技团的帐篷躲避,在光影效果的加持下,这一小小空间呈现出一种蒂姆·波顿似的奇幻风格。这一幕在情节上几无推进,仿佛一处“闲笔”,却深受导演的重视和观众的喜爱,显然,此处强调的是一种隐喻风格。
在这一暂时与再现现实隔离的时空中,周泽农听到杂技团“美女头”演唱的《美丽的梭罗河》。正准备与爱爱接头的他此时回过头来,在一个定格镜头中,向歌声传来的方向斜目而视。这一刻是这一场景的凝聚,就像脱离了情节的束缚,而让人物的内心与歌曲完成直接对接。在这一影像中,歌声为人物的凝视附加了价值,如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所言:“当一个声音为影像附加意义,这个意义看似来自影像自身。”[4]正如这首优美的异域民歌所提供的意象,“你的源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周泽农对于歌声来源的凝视,正是其被掩盖的求生欲望对“自由流淌的远方”的渴望,并与“不可逃离的野鹅湖”构成了鲜明的对立。如此,因为一个对比坐标“梭罗河”的存在,野鹅湖在表现的意义上拓展了自己存在的空间范畴,而周泽农在这一新的隐喻空间的位置也随之刷新了。
周泽农逃亡的表层动机,即把举报奖金留给家人是叙事的“驱动器”。但从隐喻对位的角度而言,却无法完成与湖水象征“死亡”的对应。与“死”的隐喻对应的,只能是“生”的隐喻。在电影结尾,周泽农中枪死在湖边。他逃亡的旅程可以概括为:环绕湖畔—进入湖心—终于湖边。野鹅湖像一个神秘的漩涡,牢牢吸附着这个亡命之徒。生的欲望作为人物动机的隐线,与明线中周泽农的自我牺牲构成了张力。容纳这一张力存在,才是完整的人物动机,周泽农“逃着去死”这一扭曲的表层叙事才有更深层次的支撑。
生的欲望作为一个重要的意义节点,从隐喻的角度联接着“梭罗河”和“野鹅湖”这一组以水为核心的喻体,从转喻(叙事)的角度,又表征为感官的细节呈现——主要人物被塑造为可感的(而非只具诗性气质的)存在,甚至提供一种窥视视角供观众凝视其身体。正是利用感官叙事拉长并具象“去死”这一漫漫旅途,从而为两种隐喻的冲突与融合提供充分的空间。
四、结语
纵观刁亦男近年来的创作,从《白日焰火》到《南方车站的聚会》,现实可感性的凸显让电影在再现和表现两个层面上都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复归,并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作者性“再跨越”的路径变轨。这一变化过程是由明显增强的感官叙事支撑完成的。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刁亦男想达到的目标很多:凸显地方特色、坚持类型风格、保留叙事乐趣、塑造鲜明隐喻,这些目标之间本身又颇具张力。但他巧妙利用了感官叙事,在对感官叙事进行灵活的再现与表现的控制中,达成这些目标给电影带来更丰富的质感和更开阔的延展空间,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探索。
注释:
①炸米泡: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食品烹制技术,用铁制转炉烘烤大米、玉米等膨化食品,出炉时会伴随一声巨响,故谓之“炸米泡”。
参考文献:
[1]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31.
[2]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
[3]刁亦男,李迅,苏洋.《南方车站的聚会》:复原怪诞现实的审美追求——刁亦男访谈[J].电影艺术,2019(4):60-65.
[4]希翁.声音[M].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89-290.
作者简介:黄灿,博士,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叙事理论、电影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