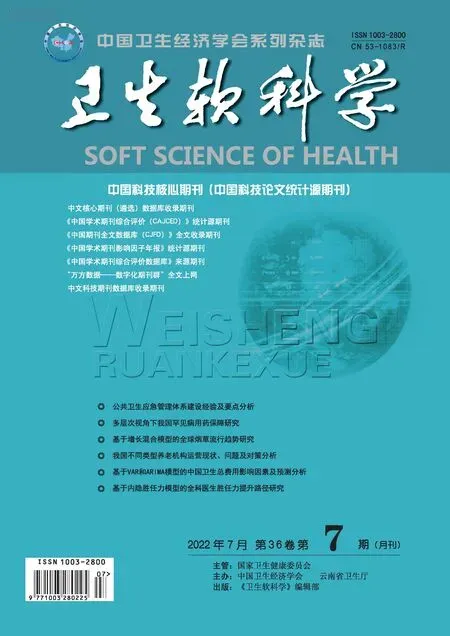基于增长混合模型的全球烟草流行趋势研究
段宇祺,王宗斌,周书铎,梁志生,尹 慧,郑志杰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北京 100191)
烟草流行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研究显示,烟草使用是20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每年导致约800万人死亡,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1]。面对烟草使用导致的巨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于2003年与2008年推出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与MPOWER系列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与基于证据的最佳实践来指导各国的烟草控制行动[2,3]。然而,尽管各国在烟草控制行动与效果方面皆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差距仍然存在[4]。本研究以全球视角,刻画了全球烟草流行负担的整体变化,并根据烟草流行初始水平及发展趋势的不同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为全球烟草流行负担的变化及差异提供了整体图景,进而为确定影响烟草流行的风险因素、完善全球烟草控制实践、减少烟草流行危害提供了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国家/地区烟草流行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5],该数据库通过各个国家/地区特定人口的烟草流行调查及贝叶斯负二项式Meta回归模型获得,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人口进行年龄标准化处理[6]。由于其高度的可靠性及可比性,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研究[7,8]。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15岁及以上人群当前烟草使用率被选定为本研究的响应变量。其中,当前烟草使用率是指调查时吸烟人群在全部人群中所占的百分比。最终,研究纳入了2007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全球149个国家/地区的数据。
1.2 统计方法
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GMM)[9-11]被用于趋势聚类分析,即将研究期间全球149个国家/地区划分为具有不同烟草流行轨迹的潜在类别。具体模型如下:
(公式1)
(公式2)
(公式3)

研究中,依次增加潜在类别数目,并根据模型的拟合指标、类别概率及实际意义,确定体现烟草流行轨迹差异的最佳分类。其中,拟合指标包括赤池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较低的AIC、BIC、aBIC代表较佳的拟合;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LMR)、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显著的P值表明该类别数的拟合优于上一个类别数;Entropy,其值≥0.80表明分类精确性较好[12]。参数估计采用稳健较大似然(MLR)估计,模型设定为增长因子方差变异跨类别等同模型[13],所有统计分析和模型拟合均在Mplus 8.7中进行。
2 结果
2.1 全球烟草流行的整体趋势
2007-2018年,全球149个国家/地区的烟草流行水平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总烟草使用率的均值由26.85%下降到22.18%,不同国家/地区的烟草流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年份总烟草使用率的极差均约达50%以上,见表1。

表1 2007-2018年全球149个国家/地区烟草流行的描述性统计
2.2 不同国家/地区烟草流行趋势的差异
使用增长混合模型识别国家/地区烟草流行趋势的差异,最终根据烟草流行轨迹将149个国家/地区分为6个类别(见附录A)。具体来看,线性增长模型的6个类别均具有显著的截距因子及斜率因子,根据其反映的烟草流行初始水平-下降速度的相对大小,将6个类别依次定义为高流行-中高下降组(占比2.7%)、高流行-高下降组(占比2.0%)、中流行-低下降组(占比12.1%)、中流行-高下降组(占比8.7%)、中流行-中低下降组(占比40.9%)、低流行-中低下降组(占比33.5%)。其中,高流行组总烟草使用率在50%左右,绝对下降速度较快,约为每年0.75%或达1%,主要包括老挝、缅甸、智利以及部分太平洋岛屿国家/地区;中流行组总烟草使用率在30%左右,但变化趋势差异较大,低下降组烟草流行水平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包括巴尔干半岛地区、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地区;高下降组以约每年1%的绝对下降速度快速下降,主要包括印度半岛地区、北美洲北部地区、南美洲南部地区的部分国家/地区;中低下降组以约每年0.4%的绝对下降速度平稳下降,主要涉及中、东亚地区、欧洲除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北美洲南部地区及非洲北部地区;低流行组总烟草使用率在15%左右,下降速度约每年0.4%,主要涉及非洲大部分地区、南美洲北部地区及澳洲地区(见表2、见附录B)。非线性增长模型的分类结果与线性增长模型类似,但总烟草使用率随时间的变化速度呈现出逐渐放缓的趋势。图1直观地展现了2007-2018年全球149个国家/地区烟草流行的6类发展轨迹。

附录B 不同国家/地区的烟草流行趋势类别

附录A 烟草流行趋势的增长混合模型的拟合指标

表2 烟草流行趋势的增长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

图1 不同类别国家/地区烟草流行趋势图
3 讨论
《公约》与MPOWER政策推行10余年来,全球范围内烟草控制行动显著加强,个体烟草使用意愿普遍降低,全球烟草流行整体呈下降趋势[14,15]。本研究着眼于全球烟草流行水平和趋势的差异化描述和横向比较,结果显示,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处于中、低流行水平并保持平稳下降;部分国家/地区由初始的中、高流行水平迅速下降,至2018年已达到低、中流行水平;但仍有部分中等流行水平国家/地区未展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3.1 烟草控制政策的投入差异是导致烟草流行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烟草控制政策及行动的加强可有效改善烟草流行水平[16,17],然而当前各个国家/地区对烟草控制政策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5],在根本上导致了烟草流行趋势的差异。一方面,国家/地区的烟草流行负担、卫生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对烟草控制的客观需求[18];另一方面,烟草控制政策的决策过程跨越多个层级、涉及多个部门、涵盖多个环节,一套科学、协调且完备的决策体系是政府破除烟草业的干扰,将烟草控制需求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决议的基础[19]。此外,国家/地区的执政党风格以及社会文化倾向对这一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如在英国,工党执政是其由烟草控制政策落后者到领导者转变的重要推手[20];在埃及和伊朗,关于禁止吸烟的宗教宣言是早期烟草控制政策推行的直接动力[21]。
针对现状,首先,应以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理念转变为契机,通过推动烟草相关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进一步加深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以强化国家/地区进行烟草控制政策投入的政治意愿。其次,应完善各个国家/地区烟草控制政策的决策机制,提高政府的决策工作能力,削弱烟草业对决策过程的干扰,以强化烟草控制政策投入的体制机制效能。考虑到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是制约烟草控制政策投入的最大阻碍,各个国家/地区在有关政策决策体系的发展中应着力于剥离烟草生产管理部门的烟草控制职能及烟草相关企业的实质性参与,强调政府尤其是卫生部门在其中的绝对决策与管理权力。对于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烟草业更易干扰其对烟草控制政策的理解,从而阻碍有关政策进入决策环节[19]。针对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应探索更加完善的烟草控制政策技术支持机制,并增加对其的实地技术指导与资源支持,以促进并协助其完成有关政策的本地化应用。
3.2 烟草控制政策的执行过程是决定烟草控制实际效果的关键环节
卫生政策有关研究表明,政策成就不足以减少疾病及其决定因素的流行,要将其转化为理想的公共卫生成效,必须改善治理及执法过程,各个国家/地区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烟草控制效果的差异。一方面,烟草制品具有经济创收商品及健康危害产品的双重性质,国家商业部门与卫生部门在烟草控制问题上具有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合作机制是国家/地区能否解决烟草控制这一跨领域复杂问题的制度性核心。如新加坡通过健康促进委员会[22]、巴西通过建立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国家执行委员会[23],促进了多部门在烟草控制中共同努力,使得烟草流行状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另一方面,是否具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是决定烟草控制政策具体执行程度的资源基础。以英国为例,过去10年其用于反烟草大众媒体运动及提供戒烟帮助的公共卫生预算大幅削减,限制了其烟草控制成就的持续发展[24,25]。而在中国,如何解决执法人员数量及质量低下的双重问题是其破除烟草控制行动困境的痛点与难点[26]。
对此,应构建以卫生部门为主导,财政部门、市场监督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等共同参与的多部门烟草控制机制,促进各部门间以烟草控制为核心的资源整合与协作互动,明确不同部门和各个层级间的职责、权限、角色和关系定位,以实现对烟草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全流程管理与监督。另外,应强化烟草控制人才投入及培养,建设一支具有全球视野及本土实践能力的国家烟草控制队伍。针对烟草控制专项预算与资金不足的问题,可通过加大政府专项预算、促进烟草税的转移利用、寻求官方发展援助支持等多途径丰富烟草控制资金来源,并通过设立烟草控制基金进行资金的统一管理。其中,烟草税的转移利用是通过增加对烟草制品的税收并将其转移到烟草控制行动中,从而将解决与烟草相关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害的成本负担从政府转移到烟草行业。
本研究创新地将增长混合模型应用于全球烟草流行趋势的描述中,但仍具有以下几个局限。首先,受数据收集的限制,难以获得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烟草流行水平的完整数据,部分数据代表性有待考察,但本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全球烟草控制的进程。其次,由于样本量较少,增长混合模型易受数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而高估或低估实际存在的潜类别数目,但本研究已结合统计指标和实际意义最大程度地确保了保留潜类别个数的正确性,研究结果具有参考意义。最后,本研究是一项描述性研究,仅对烟草流行影响因素进行了方向性的探讨,未来亟需进一步研究以精准识别影响烟草控制效果的关键环节及其中的促进与阻碍因素,为完善全球烟草控制政策、制定具有针对性及成本效益的政策实施策略提供建议。
4 结论
《公约》与MPOWER政策推行10余年来,全球烟草流行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国家/地区烟草流行水平与趋势仍存在较大差异。烟草控制政策的投入强度与执行效力可能是导致此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未来应从提升政治意愿、优化决策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增强资源保障等维度对烟草控制行动进行系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