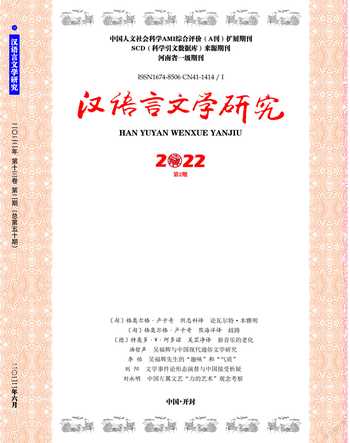歧路
格奥尔格·卢卡奇 熊海洋
摘 要:卢卡奇在这篇文章中通过评论布达佩斯的卡尔曼沙龙上展出的艺术团体THE EIGHT的绘画作品,集中展现了一种新的艺术主张。卢卡奇认为19世纪以来的经验、生活乃至艺术都分解为瞬间和情绪,永恒的价值和本质趋于消解。印象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现代性的艺术流派,它们拥抱情绪、瞬间和感觉,放弃价值和秩序,最终主体自身也淹没在客观经验之流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表面的和装饰性的艺术。而以肯斯特克为代表的THE EIGHT艺术团体,却能够复兴“旧的艺术”,召唤一种秩序和价值。所谓“歧路”,主要是指现代性的社会及其文艺的短暂与永恒、流动与不变、混乱与秩序、融化与坚固的两种不同景观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其青年时代就已经站在了这个辩证法的后半段,已经成为现代性坚固景观的召唤者,形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独特维度。
关键词:经验;瞬间情绪;艺术形式;价值;印象主义
这些评论并不必然地限于在布达佩斯的孔尼维斯·卡尔曼(Könyves Kálmán)沙龙上展出的那些图画。这个展览激起了热烈而尖锐的争论,充满了相互揭短和鸡零狗碎,因为这些图画在我看来第一次清晰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歧路(the parting of ways)。让我们简短地评论一下这种分歧的起因和重要性吧。
对于任何看着这些图画并知道如何去看这些艺术作品的人,将不会真正理解这场争论和喧嚣是关于什么的。被展出的作品不代表任何流派(甚至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们没有展示任何野心和倾向;他们不代表任何或许会与旧的态度发生冲突的新的态度。这些图画传达着静止、平和和和谐——因此很难想象它们会扰乱任何人。
然而,这些图画等于宣战。但是,这场战争并不像19世纪被无数“艺术运动”和“分离派”所打响的战争那样。那里新的“态度”常常攻击旧的。当后者被证明不合时宜了,人们将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态度”,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用同一种眼光看待事物感到厌倦。这导致了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一个新的方向,并且两种方向总是彼此争斗,直到第三种出现,这最新近的一种向第一和第二种方向的联合力量宣战,这个戏剧循环往復下去。
然而,这儿的议题有所不同。我们不是讨论不同,而是谈论对立。这里的彼此对立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不同的趋向,而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本质。危在旦夕的不是新艺术的优势,而是旧艺术的新生,是艺术自身的新生,和由它的新生引起的与新的、现代艺术之间的生死争斗。
卡罗利·肯斯特克(Karoly Kernstok)已经清晰地描绘过这里卷入的东西①。也就是说他和他的朋友所画的画(与少数几位诗人的诗歌,以及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想)都试图表达事物的首要本质。
事物的首要本质!这个简短的词组不带任何论证地表明着大争论的实质,并标记出道路分歧的地方。由于我们面对它,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关于世界的整个概念,从中我们获得最伟大的印象的艺术,对现实并不熟悉,并且否认一切都有一个首要的本质。它以一种俯就的微笑对待那些敢于思考或谈论事物的本质的人,并将其贬为老套的、中世纪的和经院哲学的。我们成长起来的时代——以及整个19世纪——不相信任何永恒的事物。稍早的一个世纪,“风景不过是情绪”这个说法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一切都是情绪。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坚固永恒的;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想象或允许从瞬间的奴役中带来解放。一切都变成了瞬间;一旦我接触一定的经历和情感,和在一定的视角中看事情,那么,除了一个瞬间,一切都消失了。结果却是完全改变了下一个瞬间。在瞬间的嘈杂的漩涡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创造秩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事物中充当公分母,因此,超越这些瞬间:在一个事物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因而能将它提升到瞬间之上。由于事物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情绪的无尽的连续,并且在情绪之间,并没有也一直没有任何价值上的差异。
即便是那个占据统治地位的自我,它以自己的情绪将一切事物形塑为一致,也将自己融化为流动的瞬间。这个自我在它的情绪的帮助下涌进世界并吸收了它,但也正因此,这个世界也侵入到自我之中,并且没有什么能在二者之间划上一道分界线,也没有什么能够在被淹没的和模糊的自我之中创造一种秩序。伴随着事物坚固性的终结,自我的可靠性也随之停止存在;而且事实的流失意味着价值的流失。这里除了情绪,一无所有。在个体之内和之间,只有一种同等级和同等重要性的瞬间。一切都变成了一个观念问题;一切都是一个感知问题,都是个人观点问题。唯一能赋予个体观点以意义的是它的个体本质,个体观点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一切都是主观的,一切意义的一致性都消失了;陈述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因为它们不再排除对立陈述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一切事物都与其他的事物吻合、共存,根本不存在能够排除其他事物的情况。
关于这种生活情绪的唯一可能的艺术就是一种感觉的艺术,经验交流的艺术,仅仅主观的、瞬时的艺术。但是越是主观,与瞬间关系越密切,能被交流的能力也就越成问题。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普遍常见的东西才能被交流,而这种艺术(印象主义)却不惜任何代价去交流艺术家生活中的一个不可交流的瞬间。因此,任何影响都变得偶然了。它就是偶然的快乐曲线、和谐地渐变的颜色,以及快乐却偶然的调好的声音的毫无意义的游戏。毫不奇怪的是,创造性艺术家的忧郁的情绪能够在接受者那里促成一种偶然的欢乐情绪。或者,相反地,艺术家的无限种类的细微差别就只产生不可预计的反响。
最终,艺术变成了表面的艺术;表面之后空无一物,表面也不意味着什么②,它们也不表达任何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偶然地存在着,或者偶然地产生一些影响。即使有这些影响,也不顾及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的。表面的艺术只能是一种感觉的艺术,一种拒绝深度、拒绝价值评判或拒绝制造区别的艺术。新的范畴,悖论性的范畴产生了,仅仅通过意识到有必要去毁灭自身,价值就被创造了出来:像价值、只像价值一样新颖、有趣。因为如果这里只有情绪和感觉,那么就只有它们的新颖性和力量能将彼此区分开来。随着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类似、每一个循环,各个感觉就变得不那么新鲜、不那么有趣,直到最终它失去了作为感觉的特点;它不再有影响了,它寿终正寝了。
这种艺术缺乏物质,因为物质是一种需要空间的同质的、有形的东西;它是坚固而恒久的。在这种艺术中没有形式,因为形式是明确的,排斥别的形式以及其他非形式的事物;因为形式是评价、区别和创造秩序的原则。
但是,在我们这个一切与另一切都共存兼容的世界,这种艺术甚至不能注意到它的致命的对手和刽子手。或者,它注意到了这些但却不能行动,不能将任何东西感受为自己的对手:它也感觉到这个了,但仅仅是一个与所有的旧的感觉不矛盾的新的感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极少的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文学科的突破(例如马克思主义)已经对印象主义形成第一次挑战。他们否定主观的、印象主义者的生活概念的合法性:坚持明确性、可证实的陈述和事物中的秩序。陈述都有一个结果,或许因为它们是真的,或许因为它们是不真的;要么它们有效,要么它们无效。进一步,任何一个对真理的许诺、承认和证实,都意味着对其他一千种未证实的真理的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反对。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陈述都是与某事有关:与事物有关。事情能够被讨论是因为它们之中有恒久的东西,这些东西独立于我们的情绪和感觉之外,事情完全不受我们在何種特殊的瞬间、在什么影响下看待它的影响。事物存在着,在它之中,有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一致的和多样的表面和实质。
印象主义者也勉强同意这些真理。他们那全面理解的大脑也接受这些真理——并且在他们的情感和经验中,一切都保持着它本来所是的样子。
然而,今天这些认识已经最终变成了情感价值(emotional values)。我们再一次地渴望事物中的秩序。我们渴望认识秩序,渴望在我们自身认识到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渴望恒久,我们渴望自己的行为能被衡量、我们的陈述能够明确而可证实。我们也想给我们的所有经验赋予意义,因此,它们就有结果并能够排斥一些事物。我们渴望评价。我们渴望区别。我们渴望深刻的思想。
在瞬间的漩涡中存在着明显恒久的东西的信念,事物存在并有一个首要本质的信念,排斥了印象主义和它的所有表现。因为恒久意味着我们有值得获取的目标,并且,我们必须为它努力奋斗,我们选择达到这些目标的道路也不再是无关轻重的了。我们再也不能说匈牙利最好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之一所说过的那些话:“假使他知道如何做他喜欢做的,那么艺术家就能做任何他喜欢的事情。”①因为目前,我们的目标自身受制于批评,而且一门艺术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那么它在为一个不值得追求的目标而奋斗时,就会被用以追求这一目标的更卓越的智慧和技巧所拒绝。的确,实际上采取的道路能被批评,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衡量成功和不成功,无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这种新的感受已经出现在方方面面,在很多地方,它已经找到了诗歌、建筑、绘画、悲剧、雕塑和哲学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已经得到多方面体现的新艺术和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还没有获得一种有意识的表达。由于很少有人能在他们的自我中认识到它,更不用说在别人那里,在他们自己或同类的艺术那里。或许,肯斯特克和他的朋友们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吧。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了这种感受和看待事情的模式的最清晰、最富有艺术性的表达。
这种艺术(THE EIGHT)是一种旧的艺术,一种秩序和价值的艺术;它是一种建构性的艺术。印象主义已经将一切转变为一种装饰性的表面,即便建筑自身也是如此;它的色彩、线条和词语由它们的吸引性和产生感觉的效果赋予价值,因为它们不能将任何事物带向深入,也不能表达任何具体的东西。新的艺术在旧的和真实的意义上是建筑性的(architectonic)。它的色彩、词语和线条只是事物的本质、秩序、和谐、重点以及平衡的表达。一切都表达着力量和物质的和谐,并且只能在质料和形式的平衡中获得表达。只有当它们能够表达出力量和物质的平衡、以最简洁最清晰最集中和最重要的方式构成事物时,每一根线条和每一块色彩——正如在建筑中——才是美的和有价值的。这里的一切也是被限制在表面。我们的感官只能对那些一直只能作为表达手段的表面、色彩、词语、调子和线条作出反应。但是,表达手段现在的确只是表达手段,不是目的和结果。印象主义经常停留在表达可能性的发现上,表达手段的新趋向的出现和它常常归于僵化的消失。印象主义仅仅提供可能通往任何目标的态度。
但是肯斯特克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他感到态度本身就是目标,因为它们也能成为情绪和感觉的承载者。假如它们足够新颖和有趣,肯斯特克就会视之为目的。对于肯斯特克而言,这些观念意味着目的,而不是手段;感觉和刺激(就是目的),而任务和责任(则不是)。新艺术是创造总体的艺术(the creation of the whole),是完全一致(going all the way)的艺术,是意味深长的艺术。
道路已经岔开。祈求印象主义的天才们是没有用的。真正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只有在他们不是印象主义者的意义上才是真正伟大的。他们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仅仅是通往对事物真实的理解的道路,他们的态度仅仅意味着通往总体性的创造,艺术性是一种深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伟大的。正如将自己的观点和视点不作为任务和武器,而是作为目标和快乐的人是配不上他们的,印象主义者也配不上那些从他们那个等级中超脱而出的杰出的艺术家。他们配不上他们,也不理解他们。天才的道路从观念到整体,印象主义者则以相反的方式看待他们的作品。天才以礼物的形式呈现给印象主义者的东西,他们已经贬值为一个态度而已。他们已经缩减为一种手法主义,艺术表达了它,并仅仅从天才的思想中抽绎出诸种感觉。
道路已经岔开。聪明的没有任何信念的印象主义者声称“理解”这种艺术的很多艺术性瞬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理解”也仅仅是一个观念,仅仅是从无论什么事情中抽绎出的感觉,并且没有任何转变紧跟着它。印象主义者看到棍棒将要敲到他们头上,却在那只来势汹汹的手的有力的姿势中获取精致的快感。但是他们的敏锐的理解力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姿势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姿势。因为这棍棒确确实实敲在他们头上。肯斯特克的带来寂静的艺术意味着对印象主义者宣战,意味着一场生死争斗。这种秩序的艺术必须摧毁所有情绪和感觉的无政府状态。单单这种艺术的存在和出现就等于一次宣战。它是对所有的印象主义、所有的情绪和感觉、所有的价值混乱和放弃、任何写着“我”是它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词的世界观和艺术的宣战。
* 本文译自[美]卡达凯编:《卢卡奇读本》,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73页。(Geory Lukács,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The Lukács Reader, Arpad Kadarkay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 pp.167-173.)脚注为原英译注。摘要、关键词系中译者添加。
① 在他的艺术宣言《探索艺术》中,肯斯特克聚焦于本质,以及艺术家是如何发现他们自己处理本质的术语。正如肯斯特克所言,“那些看我们的画的人,在我们前面或在我们旁边,当我们的面嘲弄本质。是的,有一个本质。但是这些被扔给我们的争论并不存在。本质并不像他们所言,本质是不同的;本质中没有这些特征;本质是自然的——这是主要的争论。本质——啊,这么耐心——不仅仅忍受被盯着,而且当被不同的流派剥夺时也不会反对”。否定印象主义的精湛的用笔和色彩,肯斯特克的绘画试图恢复文艺复兴的艺术表达存在于头脑中的美的理念的理论。正如肯斯特克所言,“艺术不能镜照自然;但是在它从自然中抽绎出新的价值的意义上,艺术是艺术家才智的镜子”。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基本前提。欧文·潘诺夫斯基:《观念》,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特别是第四章《文艺复兴》。
② 卢卡奇声称印象主义者的世界观意味着空无是不公正的和站不住脚的。当他们画肖像和人物形象足够真实之时,印象主义画家并不处理什么心理学和哲学问题。但是卢卡奇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德加和马奈到雷诺阿和莫奈的印象主义画家,给公众渴望受到有组织的都市工业化世界威胁的那些价值的符号以表达:自发性,个体主义和在自然事物中寻求安慰的自由。罗伯特 L·哈波特:《印象主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① 卢卡奇的朋友拉约什·菲莱普(Lajos Fülep),一个爱上佛罗伦萨艺术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否定印象主义。菲莱普完全同意米开朗基罗的主张:“一幅画不是用手画出来的,而是用脑子画出来的。”1911年,卢卡奇与菲莱普发行了《精神》杂志(Szellem)。这份在佛罗伦萨编辑的杂志对印象主义、实证主义、决定论和进化论大张挞伐。在一篇名为《艺术创造中的意义的作用》的重要文章中,菲莱普以贝纳代托·克罗齐的这个主张——艺术作品的总体影响,不论它如何被哲学概念所浸透,都是一个直觉——提出问题。正如克罗齐所言,“直觉即表现;表现之外无他物(没有更多的,只有更少)”。这使得菲莱普确信克罗齐是“印象主义的美学家”。菲莱普用记忆去取代直觉。就像一个优秀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那样,菲莱普如此反驳克罗齐:“我们并不一定记得我们已经看过的,但是我们能看到我们记得的或能记得的。”菲莱普:《艺术创造中的意义的作用》,《精神》(1911年3月),第69頁;克罗齐:《美学》,道格拉斯·阿英斯列译,波士顿:极品图书(Nonpareil Books),1983年版,第3页。
译者简介:熊海洋,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