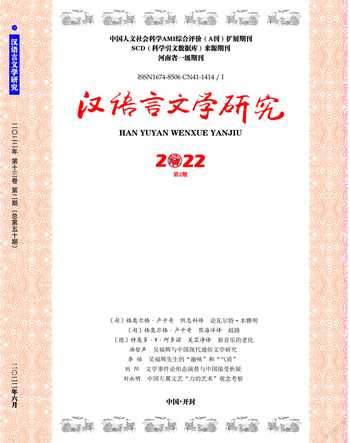论瓦尔特·本雅明
格奥尔格·卢卡奇 阴志科
摘 要:卢卡奇认为,本雅明为现代艺术提供了深刻且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支撑。本雅明从当下意识形态和艺术需求的角度解读了巴洛克与浪漫主义,经过本雅明解读的德意志巴洛克悲苦剧拥有了内在的一致与连贯性,其中包含着揭示艺术本身的法则的意图。本雅明认为寄喻和象征表达了人类对现实回应的根本性分歧,由此卢卡奇也探讨了歌德、谢林、索尔格到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等人对象征和寄喻所做的区分。当然,卢卡奇也在暗中把本雅明的思想延伸到了他自己的拜物(恋物)和典型等概念上来。
关键词:卢卡奇;本雅明;寄喻;物
本文意在阐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现代主义先锋派都明显体现着寄喻(allegory)的精神。
最近几十年间,批评家们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巴洛克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根本关联,另一方面探讨现代主义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为现代主义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下一个定义,并使其合法化,让后者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深刻危机的代表,成为我们现时代重大危机的子嗣与接班人。正是本雅明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最深刻且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支撑。他在对巴洛克悲苦剧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即作为风格(style)的寄喻与现代世界的情感、观念以及经验有着最本真的契合度。只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作者明确公开的宣布。相反,本雅明的文稿严格限定在他自己选定的历史主题之中。不过,它的精神却远远溢出了这一有限的框架。本雅明从当下意识形态和艺术需求的角度解读巴洛克(与浪漫主义)。为此他选择了这个狭窄主题,但此选择尤为巧妙,因为巴洛克时期的危机元素,与当时德国社会特定语境中明确无误的清晰度是同时涌现的。这是德国暂时沦为世界历史(world-history)某个纯粹对象而产生的结果。这反过来导致了一种绝望的、只关注自我的乡土习气,其结果在于,现实主义者对这个时代的反抗倾向随之变得软弱无力——否则,只有类似于格林梅尔肖森(Grimmelshausen)这样的特殊情况里,这种反抗倾向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凭借这一才华横溢的洞察,本雅明把研究的主题锁定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尤其是此时的戏剧。他无须采用在当代通史中常见的方法,即强行使用或歪曲历史事实,照样可以对实际的理论问题做出生动描绘。
本雅明的巴洛克研究从当代艺术成问题的特征角度入手,在对此研究做出更细致的考察之前,快速检视一下由浪漫主义美学确立的象征与寄喻的区别对我们而言将是积极有益的,这也是一项基础的预备性工作。这也将反映出,他们的立场与危机前后的思想家相比依然不那么清晰明确。他们保持中立的立场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歌德本人个性的绝对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歌德对这一问题有清晰的洞察,并且他也认为自己的见解对艺术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活跃于歌德时代的艺术中,那种朝向现实主义的强烈驱动力强化了这一元素,但这并不单单发生在歌德一个人身上。此外,浪漫主义认为其自身处在两次危机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便导致了一种特定的、也可能是成问题的、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本质的洞见,而且,任何打算界定寄喻的尝试,其内部所蕴含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化解。
谢林在其美学中①,根据古典艺术属于象征时代的原则整理了艺术史,而基督教则被寄喻的法则所支配。谢林的古典艺术主张以温克尔曼、莱辛和歌德所确立的传统作为基础;基督教艺术则旨在为某种特定的浪漫主义艺术提供历史支撑。与其说,对基督教时代缺乏真正精确的了解导致了这个计划的含糊不清,不如说,事实上这个浪漫主义的视角过于单一了。谢林的观点消除了我们早已熟知的象征与寄喻在雕塑领域中的冲突,它甚至把处于现实主义象征当中首要地位的作者和作品解释为寄喻。索尔格继承了谢林对象征和寄喻的区别,但又在一般理论的层面上对寄喻做了更清晰的界定②。
处在浪漫主义寄喻危机趋势中的真正理论家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为了适应这一危机趋势,他们之所以过滤并扩散危机的理念以及把寄喻视作对危机的表达方式的理念,与此前概述的历史哲学有密切关联。然而,若纳入某种客观的历史哲学之中,这个问题就显得不那么尖锐,对谢林来说尤其如此,施莱格尔认为,神话的消亡可能是文化尤其是艺术(形成)的基础。尽管施莱格尔依旧希望并坚信,创造一种新的神话有可能找到一条出路,一条打破他自己所处时代深刻危机之僵局的出路,但神话的消亡还是被视为危机的标记。因为对施莱格尔而言,每一个神话都不过是被想象力和爱所变形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大自然的象形文字表达”,所以施莱格尔得出了“一切美皆寄喻”的结论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因为,最高真理是无法言说的,只能通过寄喻的形式来表达”。这就导致寄喻在所有人类活动形式当中拥有某种普遍威权;语言本身在其最原初的显现形式上,就“等同于寄喻”③。
不难看出,这种分析渐渐倾向于把寄喻从与基督教那古老的关联中分离出来,两者的关联曾被宗教神学精确规定,甚至被条条框框固定了下来。但是,寄喻却与情感特有的現代式混乱确立了某种亲缘性,并且与某种形式的消解建立了亲密关系,这种消解反过来导致了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④的崩溃。正是诺瓦利斯从这种倾向当中探寻到一条明确的公式:“故事缺乏逻辑关系,只有联想,不过就是梦而已。诗歌旋律动人,辞藻华丽,但若缺乏意义或者连贯性,最多也只是停留在理解层面的几行诗节而已——就如同一堆由各不相同的物品拼凑起来的碎片。真正的诗歌就像音乐之类,最多只包含某种笼统的寄喻意义和某种间接的影响。”①
浪漫主义者的说法飘忽不定、晦涩而且自相矛盾,与之相对照,德意志巴洛克悲苦剧经过本雅明的刻画,拥有了内在的一致和连贯性,令人印象深刻。这里不展开讨论他那些常见的精彩辩论,比如反对歌德的论战,或者富有启发性的详尽分析等。首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他对巴洛克的全部理解并没有停留在巴洛克与古典主义的对比之上,也没有试图在矫饰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确立某些相关的、互补的趋向(这是后来某些折中主义者的典型)。他反而朝着自己的目标发起了直接进攻,即去揭示艺术本身的法则。他说:“在寄喻式直观的王国里,图像是碎片,是儒尼文。当神圣知识的光辉降临其上时,它作为象征的美就消失了。整体性的假象被消除了。原因在于,一旦理念(eidos)消失,对它的比喻便不复存在,理念所包含的宇宙也随之塌缩。……对艺术问题性的深层次直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其出现是对自我确证的一种反抗。”②然而,本雅明论证的逻辑导致了这样的结论:艺术的问题性就是世界本身、人类世界、历史和社会的问题性;所有这些东西的衰败在寄喻的意象之中清晰可见。在寄喻里,“观察者所要面对的是历史的希波克拉底面相,它来自一种石化了的、有关原始图景的历史”。历史不再“去假设某种永恒生命进程的形式,无法抗拒的衰败也是如此”。然而,“寄喻由此宣示了它对美的超越。思想王国中的寄喻即实物王国中的废墟”③。
本雅明的视角是绝对明晰的,尽管象征和寄喻的对立对所有艺术作品的美学定义来说都至关重要,但从根本上说,二者的对立并非美学思辨自发或有意为之的结果。它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来源:人类会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做出必要的回应,这回应会促成或阻碍他的行动。有了这些,无须赘述就可以发现,本雅明采用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处理并深化了现代艺术的这一问题,而在20年前,威廉·沃林格在他之前就在《抽象与移情》中定义了这个问题。和前辈相比,本雅明的分析更深入、更有鉴别力,就审美形式的历史分类法而言,他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和敏感性。正如我们所见,随之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二元论,它在浪漫派那里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现如今则被具体化为某种基础牢固的、来自艺术和意识形态之现代危机的历史描述与解释。与沃林格和后来的现代艺术批评家不同,本雅明认为,为了凸显象征和寄喻之间的鸿沟,没有必要将其精神和思想基础投射回原始时代。他的成就显然不会被以下事实损害,即社会历史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些模糊不清、不受重视。
因此,本雅明的研究是从这一理念出发的,即寄喻和象征表达了人类对现实回应的根本性分歧。他尖锐地批评了浪漫主义者的构想的晦涩难懂,这一批评把人们的视线转向这一事实:归根结底,寄喻这一模式是建立在破坏人类对世界的拟人化回应的扰乱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拟人化是审美反映的基础。但在摹仿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与自然及社会特有的活动领域的诸多关联之中,人类努力追寻着自我意识,很明显可以看到,关注寄喻必然会破坏审美反映当中始终隐含着的普遍人性。我们在这里无须笼统概括,本雅明非常肯定地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以下情况并非不证自明的,物高于人,碎片高于整体的优先性再现了寄喻和象征之间的对抗,就对抗而言,这是相对的两极,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力量上是势均力敌的。寄喻式的人格化总是在隐瞒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它所要做的不是把物人格化,而是通过把物装扮成人来为物赋予某种引人注目的形式。”④
问题的关键因素至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本雅明只关心为寄喻在美学(或跨美学)中讨回公道。因此,他仅停留在单纯的描述上,尽管从概念上讲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拟人化的摹仿艺术不同的是,赋予事物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形式便等同于拜物(fetishize),相反,摹仿艺术具有去拜物教化(defetishization)的天然倾向,它关于物的真正知识都是人类关系的调节器。本雅明甚至都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但随后的理论家远没有本雅明那么挑剔,在后来的前卫艺术宣言里确实频繁地使用了“恋物”(fetish)一词。但是,他们当然也会用它来表示某种“原初”的东西——这种表达呈现出面对事物的真正原始的、“巫术”的态度。不言而喻,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未能认识到,试图恢复一种古老的巫术文化只可能发生在想象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对人与物关系的拜物行为(fetishization)。即便是时常用“象征符号”(emblem)(用其最近取得的含义)来代替”恋物”(fetish)也丝毫不会改变这种情形。因为在寄喻的语境里,一个象征符号(emblem)如果是未加批判便加以肯定的拜物行为(fetishization),那么它就可以表达任何东西。
本雅明准确地洞悉到宗教与传统在巴洛克时代是不可分割的联合体。这两种元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氛围(atmosphere)(寄喻在此相互作用之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削弱了所有真实的客观再现)。我们已经对拜物行为这一趋势做出了考察。但是,本雅明也察觉到这个因素引发了另一个处在运行过程中的相反因素。“任何人、任何物都有可能意指其他任何东西,这个可能性对世俗世界来说是一种具有破坏性但却公正的裁决:这个世界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因为处在其中的细节没有任何价值。”①这是一个个体价值被贬低的宗教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被维持在一种贬值的状态当中。反拜物教的物必然具备它自己的品质和细节;反拜物教的物性(thinghood)是一个确定的个别事物恰好成其自身的方式。除此之外,现象与本质、细节与客观整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必须得到强化。如果诸细节可以在超出自身而指向某种本质的地方获得某种症候性的特征,那么一个物(object)才可能是被理性规划过的,它才可能被提升到单独个体(Besondere)也就是典型的层面上,它才可以成为一种在细节上被合理规划过的整體。
当本雅明正确指出寄喻完全废除了细节以及所有具体客观的再现,此时他似乎是在对所有个体性更彻底的毁灭做出诊断。但现象都具有欺骗性;这种毁灭实际上暗示着重演。这种替代行为仅仅意味着,互相替代的物与细节在它们恰好出现的具体形式当中被扬弃了。所以这种扬弃只会影响到它们的既定性质,取而代之的是内在结构与它们完全一致的物(objects)。因此,既然个别之物相互之间被简单替代的情况确有发生,这种对个体性的废除也不过就是它自身持续不断的复制。这个过程在每一种对待再现的寄喻观点当中都始终如一,绝不意味着和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基础产生冲突。
然而,在巴洛克本身特别是在本雅明对它的解读当中,逐渐浮现出一个新的主题。事实上,那种超越性不再包含任何具体宗教内容(这种超越性为我们刚刚概括过的过程提供了背景)。这完全是虚无主义的——尽管并没有改变这一过程在根本上的宗教性质。本雅明提醒道:“寄喻两手空空地离去了。邪恶本身,被寄喻珍视为永恒深邃之物,邪恶只能存在于寄喻之中,它只能是寄喻,它意指着与自身不同的其他事物。它所意指的恰恰是它所呈现之物的不存在。”同样地,本雅明敏锐洞察到此处表述的是“这一主题的神学本质”②。这种主体性的创造力拥有一种与自身相对应的接受模式,这种创造性已经超越了所有界限并达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在这里,本雅明坚持不懈的严谨态度给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评价:“寄喻是忧郁者给予自我的强大且唯一的消遣。”③本雅明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家,我们不能忽略掉他笔下的“消遣”一词所暗含的贬义。当物(objects)的世界不再被严肃对待时,主体的世界的严肃性也必然随之荡然无存。
* 原题为On Walter Benjamin,原刊《新左派评论》1978年第110期,第83—88页,英译者为Rodney Livingstone。摘要和关键词系中译者添加。
① Friedrich W. J. Schelling, Werke, Stuttgart and Augsburg 1956, Vol. 1, 5, p. 452.
② Karl W. F. Solger, Erwin, Berlin 1815, pp. 41-9.
③ Friedrich Schlegel, Prosaische Jugendschriften, Vienna 1908, Vol. II, pp. 361, 364 and 382.
④ 原文英译为objective representation,亦有“客观再现”之意——译者注。
① Novalis, Werke, Jena 1923, Vol. II, p. 308.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 176.
③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 166,p178.
④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86-187.
①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75.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233.
③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85.
譯者简介:阴志科,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近现代美学与近代文论史。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