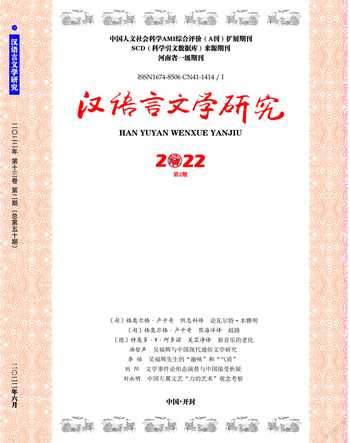人性与世态的体察者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在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却已经形成了一代代传承有序、脉络清晰的学术传统。按照温儒敏教授的说法,第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以王瑶、李何林、唐弢等前辈学者为代表,主要活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则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学界的主力军,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复兴乃至成为“显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发挥了学术上承前启后的功能①。此后,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现代学院体制的稳固,学科的代际传承大致可以按照所谓“六○后”“七○后”“八○后”等进行划分,并已经显现出各自不同的学术风貌。而张恩和先生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代表。
此前,笔者只是在查询前人研究成果时,零星地阅读过张恩和先生的论文。今年春天,刘勇老师邀请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办的“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史书写——张恩和学术思想研讨会”,促使我阅读了张恩和先生的全部著作,随着了解的加深,开始由衷地钦佩他的研究。张恩和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论文和传记文学创作,开创出一条独特的文学研究道路,不仅关注创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文学研究的传统话题,更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对人性和世间百态的妥帖体察。在科班出身的青年文学研究者逐渐将文学研究变成一项“技术活”的今天,张恩和先生那种充满生命气象的治学理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张恩和先生的文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其学术道路起步之时,就已经非常突出。他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是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上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正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这篇论文锐气十足,一上来就对当时学界流行的两种对狂人形象的理解提出了批评,即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虽然充满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②,是一篇反封建的檄文,但其主人公既不是被封建统治者诬蔑为疯子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战士,也不是一个虽然真的已经疯狂,但却仍然没有停止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斗士。从这里出发,张恩和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说鲁迅试图在《狂人日记》中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那么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他为何选择去塑造一位“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③的狂人?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张恩和首先区分了作家与人物的思想,指出狂人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小说家鲁迅“通过战士的思考得出封建社会吃人的结论”,并“选中了一个不可能具有清澈思想的狂人作为作品的主角”④。接下来,他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鲁迅为何要在小说中塑造一个狂人。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小说家在构思过程中受到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影响,且自身具有较为丰富的医学知识,使他能够将狂人作为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而主观原因则是,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的時候,刚刚“经历一段沉思苦闷”,“心情仍不免带有一些痛苦和寂寞”,这使得他“更多的是看见周围的黑暗和‘昏睡’的人们,较少注视为数寥寥的‘精神界之战士’”,于是“自然而然地选中一个社会的牺牲者——狂人为描写对象”①。
分析至此,这篇论文本已经较为完整地回答了其原本要解决的问题,但张恩和先生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他继续追问:“鲁迅是怎样做到在描写狂人特殊心理的同时,将自己的思想见解寄寓到狂人的日记中去,既不影响狂人形象的真实性,又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极为充分的呢?”②这就使得论文讨论的对象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小说样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落实到小说技法和艺术特色的层面。张恩和指出,小说中狂人在日记中写下的“吃人”,指的是诸如狼子村佃户吃人、食肉寝皮以及五岁的妹妹被吃等具体的吃人事件,而鲁迅将封建礼教理解为“吃人”,则是在比喻和抽象的层面上严厉抨击封建制度对国人精神的摧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然而,两种不同的“吃人”虽然在内涵上截然不同,但在语言上则叠合在一起,于是,“语意双关的话语,比喻象征的手法,便成了沟通狂言和真理之间的桥梁”。读者可以“通过狂话的形式通向作者真正的原意,从经过艺术制作的狂话中体会深刻的寓意,从狂人说的吃人彻悟到封建社会礼教的吃人”③。一下子点出了《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艺术效果的来源。
粗读这篇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的论文,读者或许会觉得其中运用的思想资源相对来说有些陈旧。毕竟,那种在人物形象背后寻找作家思想内涵的分析路径,探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小说的艺术风格、政治倾向的批评方法,都不断让我们回想起曾经笼罩中国文学研究界多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唯一的文学思潮,至少也是最被认可的文学观念,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反映论式的认识模式在彼时的批评话语中极为普遍,通过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叙述结构来认识社会,乃至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了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评价文艺作品高低的标准。张恩和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使用这样一套批评话语展开对《狂人日记》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
不过,读者如果仔细阅读《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就会发现这篇论文存在着某种特殊之处,使其超出了那个时代论文写作的常规路数。张恩和先生没有像当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那样,从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叙事结构等因素入手,去探讨作家的思想内涵、创作意图,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分析小说家如何寻找、塑造合适的人物形象,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正是这一颠倒,使得张恩和的研究思路超越了反映论,进入到创作论的层面。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轻视这一颠倒。对于鲁迅这样已经充分经典化、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享有崇高政治地位的作家来说,由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入手去分析背后的思想内涵,其结论往往是事先给定的,难免会让读者产生千篇一律的厌倦感。而张恩和将这一惯常的研究路数颠倒过来,从创作意图出发,探究小说家的艺术构思,呈现出抽象的思想观念最终落实为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复杂过程,则巧妙地打开了现实主义文论固有的疆界。于是,无论是属于外部研究的内容,例如作家的性格特征、成长背景、教育经历、阅读偏好、思想变化、时代特征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的话题;还是属于内部研究的内容,诸如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技法,不同人物形象的特点和优长,如何将人物形象的现实性与象征性有机结合起来等,均纳入了分析视野,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空间。这或许就是《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这篇论文发表已经近60年,但仍然不断被研究者提及的原因之一。
青年学者在写出其最初的几篇学术论文时,或许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充分的自觉,但在这些早期尝试中,其实已经蕴含了他的思维特征、问题意识以及学术兴趣点,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其今后的学术道路。从上面对《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的分析可以看出,张恩和先生的研究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即他没有像很多研究者那样,站在第三方“理性”“中立”“客观”的视角上,去分析研究对象的风格特色、思想内涵,而是努力靠近研究对象的位置,将自己代入作家的角色中去,用对人性和世间百态的丰富理解,去分析创作构思落实为人物形象的整个过程,直面小说家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这种独特的研究思路,似乎表明张恩和内心一直潜藏着文学梦,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要对作家的创作过程进行如此细致的分析和关注。这也就难怪他后来花费不少精力,写出了一系列文笔精妙、情理兼备的散文。张恩和先生的这一独特研究方式,可以说更接近所谓的创作论、作家论,天然地适合解释作品的创作构思和写作过程,也特别适合从事作家传记的写作。在笔者看来,张恩和后来正是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写出了独具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
或许最能体现张恩和先生这种研究特色的传记作品,是《郭小川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在“评传”这样的书写体例中,对诗人生命经历的生动叙述与文学作品的准确评析能够较为均衡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郭小川评传》第四章《写出革命的人情美》中,张恩和就利用独家资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分析了郭小川1957年的名作《一个和八个》。这首叙事诗因为塑造了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冤枉的共产党员王金,与主流的革命历史叙述存在较大差异,发表之后受到当时评论界的很多批评。因此,张恩和不得不花费较大篇幅为《一个和八个》的创作合法性进行辩护。他有意识地代入诗人的角色,尽可能地还原1957年特殊的时代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郭小川选择那个含冤受屈的王金作为诗歌主人公的原因。张恩和指出,“郭小川在1957年写这首诗,从表面看‘不合时宜’,其实极有深意,有相当的现实性。据郭小川夫人杜惠说,小而言之,这是为教育她而写,至少是为她历史上的冤枉和当时的委屈而引发;大而言之,则是诗人看到一些他信任了解的同志被冤枉划为右派,不但想借此安慰和鼓励这些好友,也为自己思想苦闷的状况找到一个突破点,使自己的心理情绪求得平衡”①。也就是说,是现实生活中妻子在1943年和1957年两次在政治上被冤枉的经历,很多好友被错划为右派的刺激,共同促使郭小川在特殊时期选择塑造一个蒙冤受屈的共产党员,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员的理解:“真正的共产党(员)要经受得起任何考验,包括被组织怀疑,当成敌人加以审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行动,为革命事业发挥最大作用,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②因此,郭小川才会在《一个和八个》中写下那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以表现共产党员王金身上所具有的崇高品质和巨大的感染力量。这是研究者借助来自诗人家属的独家材料,对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做出的新颖阐释。由于这一将诗歌与生活结合起来的判断背后,蕴含着张恩和对人性、人的行为逻辑的妥帖理解,使得其诗人创作选择的推断颇具说服力,令读者不得不信服。后来,张恩和还将《郭小川评传》删削、扩充、修改为《郭小川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由于体例上由“评传”改为“传”,因此,在叙述中更多地偏于传主生平的呈现,诗歌解读的部分被大量删减,极大地增加了传记作品的可读性。
显然,张恩和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是情有独钟的,因此,他接连写出了《风雨情囚——郁达夫的女性世界》(与张洁宇合著)、《鲁迅与许广平》等著作。在这些传记作品中,张恩和仍然延续了那种善于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注重分析人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做出选择,探讨作家创作过程的研究思路。例如,《风雨情囚》完整地讲述了郁达夫一生的故事,其中传主与王映霞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情感纠葛,自然是叙述的重点。传记作者携带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从郁达夫、王映霞两个人物的年龄、性格、受教育背景等因素出发,揣摩他们在生活中不同选择背后的复杂动机,从而合情合理地解释了两个人在精神、生活、为人处世等各个层面上的深刻矛盾。不过,笔者阅读这本著作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其中叙述郁达夫如何创作《沉沦》的部分。表面上看,这个段落只是大段抄录了小说《沉沦》中的部分内容,但传记作者创造性地穿插了对郁达夫创作过程中心理活动的揣测,使小说的叙述内容与作家的心路历程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例如,在抄录小说《沉沦》的间歇,传记作者就不时穿插了诸如“写了这些,他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了,但感到还应该多描述几句,特别是多写点‘他’的内心。于是接着往下写”①“写到这里,郁达夫确实非常激动。接着,他又想,既然按照自己的情况写了‘他’的处境和‘他’的心绪,何不干脆就按照自己的样子把‘他’身世情况都写出来呢?于是,唰唰唰,手中笔就又飞快地游动了起来”②“郁达夫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自叙传。他只一个劲地写下去,……他想,既然身世情况交代了,就应该深入写‘他’的‘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了。于是他又想起自己在东京住在房东家的情形”③等内容。由于小说《沉沦》的写作技法直白、浅露,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根据作品所叙述的内容去揣摩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有足够的说服力,也能够更好地说明小说风格如何来源于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激越心情。在笔者的视野范围内,这种关注作家写作心理状态的研究路数极为罕见,非对艺术创作过程有着独到见解者不能为之。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来自张恩和先生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与许广平》。据相关统计,与鲁迅有关的传记作品至今已经超过了一千部,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将关注重点放置在鲁迅的情感生活的传记,张恩和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由此可以看出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许广平》在第一章试图钩沉出鲁迅的初恋,并以此为出发点,对鲁迅的诗作《自题小像》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张恩和根据相关史料指出,鲁迅在与朱安结婚前,曾与一位名叫“琴姑”的姑娘议婚,只是因为生辰八字不合,最终未能成婚。这段无疾而终的议婚历来不为研究者关注,张恩和却从散文《阿长与山海经》的只言片语中,发现鲁迅对笃信种种禁忌的长妈妈破坏了自己与琴姑的婚事颇为不满。而小说《在酒楼上》中的人物“順姑”,因为误信一个痞子“长庚”的谣言,最终郁郁而终。巧的是,鲁迅自己当年的法名正是“长庚”,琴姑也恰恰是因为与鲁迅婚事不成,不久即离开了人世。因此,张恩和将作家生命经历和作品内容相互对照,得出结论:“从作品里这些叙述和描写中,我们多少是可以体察出一点你对琴表妹以及对这次议婚的心意和感情来的。”④以此为立论的基础,他还认为鲁迅1903年写下的旧体诗《自题小像》中的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因为用了丘比特爱情之箭的典故,不能像很多人那样,解释为对祖国的热爱,而是表达了对初恋对象琴姑的爱。显然,张恩和再一次运用自己擅长的研究方法,将自己代入创作者的视角中,通过揣摩作家写作过程中的心理动机来阐释作品。必须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毕竟在很多情况下,作家写作时的心理状态犹如一个“盲盒”,即使作家本人在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进行了阐述,研究者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更何况鲁迅这样很少谈论自己情感经历的作家。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熟悉与鲁迅相关的史料及研究文献,对小说、散文的艺术特征保持足够的敏感,更重要的是要有着妥帖的对人性和世间百态的体察,丰富的人生阅历,只有做到了这些,研究者才能通过感知作品语言上的微妙变化,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心理波动和行为逻辑。幸运的是,张恩和先生身上恰恰具备这些特点,这使得他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传主的叙述传神、生动,趣味盎然,同时,蕴含着对作品独具只眼的解读,是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佳作。正像温儒敏教授所说的,张恩和的传记作品虽然是“比较通俗、平易、好读的书,其实处处都埋藏有扎实的学理性考证”⑤。
法国学者亨利·密特朗在谈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共同之处时,认为“它们的经久不衰以及‘杰作’的身份,既得益于对人性和世态的洞见,也得益于高超而独特的技巧和风格”①。的确,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固然有作家在创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独特贡献,但作品中蕴含的对于人性和世间百态的深刻理解,也是其艺术效果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说,要想准确感知前者的艺术魅力,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和系统的文学批评训练,因此,对于那些普通读者来说,在很多时候真正吸引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其实是后者。不过在今天,接受过完整学院派教育的文学研究者,已经不愿意花费一丁点儿精力去探讨作品“对人性和世态的洞见”,而是更愿意去关注技巧、风格,乃至版本、史料等学术话题。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学术风向变化是错误的,甚至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学术研究专业化、正规化的重要表征,但文学研究不再关注作品对人性和世态的体察,多少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这一语境下,重新回顾张恩和先生的鲁迅研究,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对这位研究者生出几分亲近感,并由衷地敬佩他对自己独特的文学研究道路的坚守。
① 温儒敏:《序言》,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②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③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④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第180页。
①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第181页。
②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第182页。
③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第184页。
① 张恩和:《郭小川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② 张恩和:《郭小川评传》,第92—93页。
① 张洁宇、张恩和:《风雨情囚——郁达夫的女性世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② 张洁宇、张恩和:《风雨情囚——郁达夫的女性世界》,第62页。
③ 張洁宇、张恩和:《风雨情囚——郁达夫的女性世界》,第66页。
④ 张恩和:《鲁迅与许广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⑤ 温儒敏:《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张恩和教授》,《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① [法]亨利·密特朗:《现实主义幻想——从巴尔扎克到阿拉贡》,孙婷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作者简介: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