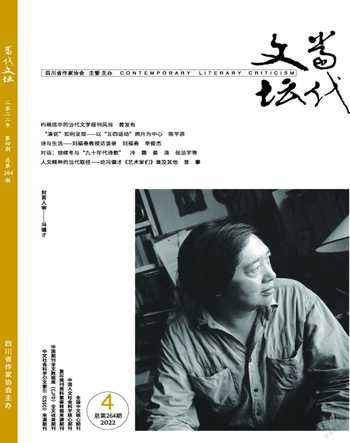从舍勒的“持续去象征化”论“文学经验”
严金东
摘要:“面向事情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和经验的简述,舍勒认为这一经验即“去象征化”“去符号化”,具体揭示了“自然世界观充满了象征”而“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舍勒的说法拉近了现象学经验和文学经验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文学经验也是一种“去象征化”的现象学经验。但常识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经验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经验。置身于真实的文学经验之中反观这个常识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文学经验是“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语言符号经验。
关键词:舍勒;去象征化;文学经验;现象学
“朝向事物本身”或者“面向事情本身”,这是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研究的共同口号,如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一书中胡塞尔就说过:“合理化和科学地判断事物就意味着朝向事物本身(Sachen selbst),或从语言和意见返回事物本身,在其自身所与性中探索事物并摆脱一切不符合事物的偏见。”①海德格尔也说过:“‘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述为:‘面向事情本身!’”②这里的“朝向事物本身”或者“面向事情本身”,凸显了一种现象学经验,“事物本身”或“事情本身”(為简洁,下文一般只用“事情本身”)当然也是在此现象学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事情本身”,那么我们可以问:何谓现象学经验?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又究竟何所指?很明显,此问题不算新鲜,它隶属于诸如“什么是现象学”等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哲学而言,基础性的问题从来又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不同时代的众多的现象学研究者,他们一再提出类似的问题并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之。以笔者所见,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外的另一现象学大家舍勒对此亦有解说,值得重视,且舍勒的解说似乎更能启发我们从现象学经验拓展到文学经验,启发我们以更接近文学本身的方式去认识文学经验。
一 “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
如上所引,胡塞尔说“返回事物本身”就是返回其“自身所与性中”,由此可见,胡塞尔的这个“事物本身”即是其著作中经常出现且颇具其个人风格的一个表达:“自身被给予之物”。像胡塞尔一样,或者说秉承现象学的共识,舍勒的“事情本身”同样指现象学直观中的那些“自身被给予的东西”,但舍勒对此强调的是,“自身被给予的东西只能是那些不再是通过某种象征而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被意指为对一个在先以某种方式被定义的符号的单纯‘充实’。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③这里的“去象征化”,也可谓“去符号化”,本质上则是“去中介化”,如舍勒在另外地方又说,“唯有现象学经验给予事实‘本身’并因此而是直接的,即不具有任何类型的象征、符号、指示的中介。”④舍勒的这些说法富有意味,但若仅就其字面含义而言,似乎也没说出更多的东西。毕竟,原则上我们都知道,现象学的经验是一种叫“直观”或者叫“本质直观”的经验,而这个“直观”术语在其基本含义上并不特殊——它依然指我们直接看见、直接听见等等,既如此,那么“直观”一词本身即含有舍勒所强调的直接的、非间接的、去中介的等内涵。至于胡塞尔不断使用的“自身被给予”一词,其本身同样包含有舍勒强调的“去象征化”“去中介”等意义——说某个东西、某个对象是“自身被给予”的,即是说它不是通过某种“中介”被给予的,即不是通过“象征”“符号”等被给予的。说到底,舍勒对现象学经验的理解,对现象学“事情本身”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同胡塞尔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接下去解读舍勒思想时应该认识到的前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说,比起胡塞尔的论述,舍勒对“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强调确实又有独到之处。概言之,相较于胡塞尔专注于对意识行为的分析,舍勒的这个说法既是一种对意识行为的分析,也较易转换为一种对语言行为的分析(符号、象征)。众所周知,在后期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现象学分析中,“语言”的分量越来越重,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海氏后期哲学体现了20世纪两大哲学潮流现象学与语言哲学的会通,而在海氏之前的舍勒这里,我们看到了两者会通的萌芽。这是从大的方面说,本文限于篇幅,无意对其进一步展开;从小的方面也就是从本文的构思而言,如前所言,舍勒的这个说法有助于我们去拓展思考文学经验,有助于我们以更接近文学本身的方式去认识文学经验。
让我们继续跟随舍勒的思路,听一听他是如何从反面来阐发现象学经验的。他说:“所有非现象学的经验原则上都是通过或借助于某种符号的经验,因而也是永远无法给予实事‘本身’的间接经验。”⑤舍勒对此更具体的分析是:
在对自然的自然世界直观中,例如颜色和声音就从未作为其本身出现,可见的质性在直观中仅只表现为:对于区分和估价事物统一或过程统一,对于这些统一的“特性”,它们也具有再现功能。这些统一在这里是某种可用性的统一或实践的含义统一,例如,钟——起身。……事物性作为本质并不显现在自然感知的事物中,反而会在被标识为此物和彼物的过程中被吞噬。……所以,自然世界观充满了象征并且因此而充满了随之而来的被象征化之物的超越。⑥
它(指“自然科学”,笔者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对在其中还是被给予之物的象征化,例如颜色和声音对它来说完完全全就变成了符号,无论它是对在物理学中某个被当做是光线之基础的基质的运动以及此基质在某些实体上的中断而言的符号,或是对在生理学中于视神经内发生的化学过程而言的符号,或是对在心理学中的所谓“感觉”而言的符号。而颜色本身并不包含在这些科学中,在自然世界观中,这个在绿树上的红只是在如此必要的程度上被给予,从而使人们所意指的樱桃得以暴露出来。……颜色本身——它的纯粹内涵——在科学面前则已成为一个单纯的X。人们总是说:这个红的颜色是一个与这个运动、这个神经过程、这个感觉相符合的X。⑦
从现象学的诞生开始,胡塞尔反复强调的就是,现象学经验不同于甚至可以说直接对立于“自然态度”主导下的自然认识、自然经验。舍勒同样在强调这一点,甚至比胡塞尔说得更加鲜明,更富冲击力,“在对自然的自然世界直观中,例如颜色和声音就从未作为其本身出现……自然世界观充满了象征”,上述第一段中的这个说法主要是针对日常经验而言,而在第二段中,针对“自然态度”主导的自然科学,舍勒认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对在其中还是被给予之物的象征化,例如颜色和声音对它来说完完全全就变成了符号”,也就是说,比起日常经验不同程度的象征化、符号化,科学活动则“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地变成了这样。
舍勒的表述颇有警醒的力量,但同时也让人有点迷惑,因为上述断言听上去似乎不太符合常识,这里需对其稍作阐释。就科学活动而言,舍勒的说法不难理解,如天空中传来一阵阵轰隆声,物理学家会对我们解释说这是云层中的某种放电现象;秋天的树叶变红了,植物学家会说这是外界温度等的变化引发了叶片的某种机制性改变。于是我们看见,在科学中“颜色和声音对它来说完完全全就变成了符号”。日常经验没有科学活动这么“完完全全”,但同样倾向于把声音和颜色作为符号、作为象征,而不是抓住它们“本身”,如屋外传来突突的声音,我的确听见了这个声音,但几乎同时也会滑过这个声音,我感到“听到”门口来了一辆汽车;我看见树上有红色,我的确看见了这个红色,但几乎同时也会滑过这个红色,我注意到的是樱桃熟了。顺着舍勒的思路,我们可以说,不仅颜色和声音,实际上所有的一切——质地、形状、整个的事物、人、社会、历史,乃至于世界全体,在人的自然经验中都倾向于成为某种“符号”“象征”,人的自然意识很难停留在所有这一切的“本身”上面,总是由此“符号”“象征”滑向他处。换句话也可以说,“自然态度”主导下的非现象学经验(从日常生活到科学研究)“原则上都是通过或借助于某种符号的经验,因而也是永远无法给予实事‘本身’的间接经验”,与此相对立,因而舍勒又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
二 文学经验也是一种“去象征化”的 现象学经验
现象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其对“现象”的强调,对“直观”的强调等等,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象学经验和文艺经验的相通甚至相同,而上述舍勒对现象学经验的阐释,则显著加强了我们的这一印象。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上文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合理地把舍勒“持续去象征化”的意义内涵扩展描述为:持续地停留在所见所闻的事情本身上,关注事情本身,凝视事情本身,聆听事情本身,不再跳跃、不再推移,不再滑向别处。事情本身就是事情本身,我们直观着它,感受着它,它不再是我们习惯性地通向别处的“象征”“符号”“中介”“工具”等等。按照舍勒揭示的如此意味的现象学经验,我们的确可以感到,这并不是现象学或现象学家独有的,更多的人不一定从事现象学思考,但他们可能会在真正的艺术经验、真正的文学经验中体会到相同或类似的感受,或者说,对于更多的一般人来说,如此这般的现象学经验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艺术经验、一种文学经验——当他们投身于文艺作品中时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此外,各种美学理论、各种文艺理论对文艺经验的揭示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这一点。如美学上的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面对一棵松树,商人想到了木材的价格、市场的行情等,植物学家想到了某科、某属,而只有诗人才真正看见风中摇曳的松枝、嶙峋苍劲的树干等等;再如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艺术“使石头成为石头”;还有如《冷斋夜话》卷三记载的“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⑧;以及王夫之对诗歌显现世界的评论:“物无遁情,字无虚设……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⑨等等,文艺领域中的这些不同说法虽然各有其具体含义,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它们都强调了唯有在艺术中“松树”“石头”“天下清景”才被“看到”,被真正经验到,才成为其本身,才“如所存而显之”。无疑,这样的艺术经验即使不等同也是非常接近于舍勒闡释的“持续去象征化”的现象学经验。实际上,国内知名现象学学者张祥龙直接就肯定了“现象本身的美”:“在现象学的新视野之中,那让事物呈现出来,成为我所感知、回忆、高兴、忧伤……的内容,即成为一般现象的条件,就是令我们具有美感体验的条件。”⑩
这就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说现象学经验在实质上相通甚至相同于艺术经验,这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有些疑问需要进一步澄清,即如果说艺术经验是一种现象学经验,那么,就以文学为例,对于文学这样一种语言符号的艺术,又如何理解它的“去象征化”“去符号化”?这是就“文学整体”而言,不仅如此,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而言,其中不乏比喻、象征、借代……不乏各种各样言外之意的表达,各种各样由此及彼的艺术手法等等,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说文学经验就是舍勒意义上的“去象征化”“去符号化”?
先从具体文本谈起。对于文学中那些通常理解的具有“象征化”意味的“修辞”及“技巧”,现象学不一定这样看,现象学要求我们换一种眼光去观察。如海德格尔在针对特拉克尔的“你驶入夜的池塘,驶入那片星空”的诗句时,他的评论就很不一般:“夜的池塘这一诗意形象描绘了星空。这乃是我们的寻常之见。但就其本质真实而言,夜空就是这个池塘。相反地,我们别处所谓的夜,毋宁说只是一个图像,亦即对夜之本质的苍白而空洞的摹写。”11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通常会认为“夜的池塘”是诗人对“星空”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认为,日常语言中“所谓的夜”过于“直白”,缺乏文学意味,而诗人通过“夜的池塘”这一比喻,“间接地”但更形象、更富有意味地言说夜空。但海氏这位现象学哲学家不这样看,他认为“夜空就是这个池塘”。海氏的评语初听好像不讲道理,但细加思考,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非“寻常之见”可比。用舍勒的术语展开海氏之意,即是说诗人在这里并非通过“池塘”这个“象征”或“符号”去“间接地”“中介地”言说“星空”,他“直观”着“星空本身”,他在“夜的池塘”这个语词意象中直接呈现着这个“星空本身”,此时此刻,“星空”不是“像夜的池塘”,它“就是这个池塘”。如此看来,“池塘”这个通常意义上的“比喻”或“象征”,实际上并不妨碍说特拉克尔带给我们的既是一种文学经验,同时又是一种“去象征化”的现象学经验。事实上,恰是因为特拉克尔创造性地运用了“池塘”这个“象征”或者“比喻”,它才使得我们能够“去象征化”地“直观”“星空本身”,直接地真正看见“星空本身”。相较而言,如上引海氏所云,“别处所谓的夜,毋宁说只是一个图像,亦即对夜之本质的苍白而空洞的摹写”。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因为日常语言中的“别处所谓的夜”完全不能让我们真正去凝视夜,真正地把目光停留于夜,因而完全不能让我们真正直接“看见”夜。
显然,如果具体文本中比喻、象征等的存在并不影响我们说文学经验是一种“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现象学经验,那么,就“文学整体”而言,就它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艺术而言同样也不影响我们这样说。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经验”二字——只要我们真正回到活生生的文学经验,那么具体的修辞也罢,普遍意义上的语言符号也罢,都将不再作为单纯的“符号”“象征”或者说“中介”而存在。事实上,在真实的文学经验中修辞技巧的消失、语言符号的消失,这不是什么奇特之事,正如中国古人在对那些最好诗歌的切身感受中,他们常常由衷地感叹:“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皎然),“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刘熙载)等等。诸如此类的评语并不是修辞性的夸张,很多情况下它们就是真真实实的阅读体验——想象一下我们对杜甫诗句的体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说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毫不为过。同样的,对于上文所引的“夜空就是这个池塘”语,应该说海德格尔亦非故作新奇之论,他能这样说也只是他忠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罢了。总之一句话,着眼于真实活动的发生,我们不难感知到文学经验在达到一定程度、一定境界后,恰如同舍勒描画的现象学经验一样,是“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经验。
三 文学经验是“去符号化”的语言符号经验
借用舍勒的术语,我们说文学经验也是一种“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现象学经验,但是回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个常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文学经验依然还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经验。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两种说法的观察角度各自不同。前者是从文学经验内部,是对文学经验的一种体验性反思。在这个体验性反思中,我们看见文学“让石头成为石头”,让世界“如所存而显之”,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恰是对现象学所谓的“事情本身”的呈现,文学经验也是一种“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现象学经验;后者是从文学经验的外部,我们的确看见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编织物,因而理所当然我们判定文学经验也必然是伴随着这种语言编织物的经验。后者的判定偏于常识,也自有其特定的合理之处,我们不能说这种判定就是错的,但是因为有了前者的观察,后者的这种偏于常识的判定就有了进一步辨析乃至修正的必要。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完全站在文学经验之外谈论文学经验,我们必得在体验着“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同时意识到文学经验的语言符号性质,此时此刻我们再说“文学经验依然还是一种语言符号经验”,那么这句话更加合理的含义只能是指:文学经验始终是文学语言成就的经验,文学语言始终是充盈着文学经验的语言。
这即是说,文学经验和语言符号是融为一体的,既是原本就是融为一体的,也是始终融为一体的。当然,这样一种看法听起来并不新颖,如上所说,它内含着一些常识的因素,也不难在现代的所谓语言本体论的文学观中看到它的一些影子,但笔者想说的是,常识中的东西仍需去追究,为其贴一个语言本体论的标签也无助于更好地理解它。让我们稍详细地谈一下。“文学经验和语言符号始终是融为一体的”,这个说法自然是反对传统的语言工具论的文学观的(语言工具论的基本误区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同世界分离的单独存在的工具),但它亦非主张语言决定一切,语言就是一切,简言之,它也反对语言决定论并因此不太赞同语言本体论。固然,语言本体论不等于语言决定论,但我们都知道,伴随着20世纪以来语言本体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流行,诸如“作者已死”“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不是人说话,是话说人”等口号的声响也非常大,这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就是语言本体论偏颇化、极端化发展而来的语言决定论。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对此展开论说,本文的观点直接就是,“本体”二字,几乎内在地就含有“决定”的意义,语言本体论几乎内在地就通向语言决定论,但文学经验不单纯是语言决定的经验,文学经验也非简单地以语言为本体的经验,更简洁地说,文学经验绝不是唯语言的经验。“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读到此处,置身于真实的文学经验中,我们听见的是凤姐爽利的笑语,不是听见描写这笑语的语言。同样的,读到“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我们看见了倨傲无比的凤姐其人,不是看见描写凤姐其人的这一串语言符号。好的文学确能够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甚至可以说,最好的文学可以把“如”字去掉,直接就让读者闻其声、见其人。这样的举例,又让我们回到了前述对文学经验“去象征化”“去符号化”的理解,但是,我們已说了,文学经验和语言符号是融为一体的,我们能在文学经验之中认识到这一点、确切地感知到这一点吗?否则的话,说它们“融为一体”就是空洞的,不过是把两种角度的两个观点捏合到一块罢了。笔者以为是可以的。如上述例子显现的,就在我们不见文字、但见凤姐其声其人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禁不住地发出感叹:曹雪芹写得真好!一句“写得真好”,作为小说艺术杰作的《红楼梦》的语言符号因素就凸显出来了——并且,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是在真实而鲜活的文学经验之中而不是之外看见了这个“语言符号”,这样,我们就有把握说,文学经验和语言符号是融为一体的,继续借用舍勒的术语,不妨说,文学经验就是一种“去符号化”的语言符号经验。
“去符号化”去掉的是工具、中介,由此文学经验带来一个如其所是而显之的世界。此时此刻,不再有作为工具、中介的语言,但语言符号本身并未消退,相反,这个文学的世界越显亮,语言符号就越显亮。我们读文学经典时,这样的文学经验总让我们体验感知着最动人最真切的人、事、物、情,也同时体验感知着最恰切最显豁的语言符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等等,无一不是,无所不是。应该说,这样的文学经验已超出舍勒的现象学经验描述,毕竟,舍勒所说针对的是一种狭义的哲学经验。舍勒之后,更关注诗与艺术的海德格尔对此有了明确的揭示:“虽然画家也使用颜料,但他的使用并不是消耗颜料,倒是使颜料得以闪耀发光。虽然诗人也使用词语,但他不像通常讲话和书写的人们那样不得不消耗词语,倒不如说,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且保持为词语。”12海氏所说是一种语言本体论吗?如果只在一种反对工具论的意义上理解本体论,那不妨说是,我们不反对这样的语言本体论,我们反对的是唯语言论。海氏后期越来越看重语言,但作为一个终身的“存在”思考者,海氏肯定不是唯语言论。文学经验不是唯语言的,文学经验是全部世界的动态展开,它一定是言之有“物”的,是实实在在的“物”的存在,“物”的世界,否则的话,它就不是文学或者是低劣的文学;但同时,文学世界中的万“物”又总是一种语言存在,不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而存在,它直接就是语言存在。应该承认,我们的思考由舍勒开始逐渐向海德格尔靠近,这不是偶然的,是现象学的思路使然。
限于篇幅,我们的讨论告一段落。很明显,“文学经验是一种‘去符号化’的语言符号经验”,这个说法没有终止对“文学经验”的探讨,相反,它可能刚刚开启一个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这样看来,本文最多只能是一篇导论了。不过,若它果能引发更多的问题,也不失其有限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②〔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33页。
③④⑤⑥⑦〔德〕舍勒:《哲学与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第5页,第6页,第62页,第63页。
⑧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9页。
⑨王夫之:《古诗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⑩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2页。
11〔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页。
1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6YBWX072)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