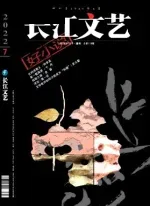像花枝探出浅浅的白(9首)
敬丹樱
暮晚
咬出两个缺口
蛋糕重新摆回餐盘。房间里长脚的
还有秒针和摩卡
每个角落都是撒欢乱窜的香
拉上窗帘前,落日正从容走下山梁
从老梨树上飞起的几只灰尾鹊
躲进南墙边
结满青皮核桃的树冠
歪在床头随便翻翻什么书
台灯下的瓶插
是班上小姑娘带来的白芍,栀子,洋姜花
或教室前简易花台里的萱草
会摘下它们的骨朵,清炒或做汤
那时学校有三两百学生
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
麦秆菊,泰迪向日葵,火焰兰……
瓶插换着换着
就到了怀旧的年纪
最怀念的,还是乡下教书
那几年
栾树下的落花
鹅黄的细雪铺到脚边
如果不是蹲下来
留意到每朵花额间那笔精致的朱砂
这悄无声息的死亡美学
就没那么惊心
被栾树吸引
还是上一个深秋。树梢的累累硕果
堆成彩霞
你拾起一朵递给我
对着光转动这盏浅红色的灯笼
隐约有两粒种子
填充着
它的空旷
替蜻蜓擦拭翅膀
一只红蜻蜓披着月光
别在芦苇枝头
苇秆那么高,踮起脚尖也够不着
但我还是执着地举起抹布
要替它擦拭翅膀
我蹦啊跳啊折腾半晌
睁开眼,已是浑身乏力。女儿还在灯下算题
养育花朵也是一场大梦
十年来我从未停止替她擦拭翅膀
我不了解其他母亲。但我停不下擦拭的手
也腾不出时间来打量
她的翅膀
在雾霭中生活
海面浮出的几座鱼脊
是线索。乳白色的雾霭,有时微微泛青
混淆着我们的生活
仿佛过于久远,细节似是而非
你不时抛出新的线头
提示着某时、某处
浓雾贯穿始终。我开始相信
我们见过
做着一场未完待续的梦:那里辩题无数
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耗尽半生为掌握一门技艺
——在雾霭中生活
玉簪
月亮走得慢
浅浅的白。我们走得也慢
随意找个花坛坐下,烤玉米掰成两段
挨在一起的影子被夜幕渐渐收走
咀嚼替代了交谈
蝉是槐树上的隐形歌手
前方埋头弹吉他的流浪歌手
脸被夜色和长发
各掩掉一半
他并不理会高处的叫板,嗓音里异质的清冷
像花枝从身后探出浅浅的白
后来我只记住了玉簪的名字
你只记住了我的香
绿皮邮筒
刷上墨绿的油漆
邮筒看起来像个树洞,这令她感到踏实
踮起脚把信轻轻塞进去
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不多久
邮递员会来开锁
厚薄不等的一摞
蒲公英般飘远,在指尖着陆。端正的字迹
一朵朵列队闪现……
渐渐地,邮筒面目模糊,锈蚀
作为物证,杵在邮局门口
再后来,邮筒被摘除,通往邮局的路焕然一新
一切越来越好
不再有人记得这件温暖的弃物
她对树洞的歉意成为秘密——
某个黄昏,一根划燃的火柴飞进它的胸膛
光芒映红了
邮筒前,少女的脸庞
凉水攤
镇子上场口第一个陡坡
竹林前,方形玻璃片
盖着红的,绿的,黄的凉白开
玻璃杯里勾兑也很透明:
食用色素、糖精、十滴水
那是一片清凉的竹林
每次赶集路过,都要摸出两分钱
选最喜欢的绿色
掀开玻璃片
手从嗓子眼探出
遗忘从糖精和十滴水起,再是盛夏
小得不能再小的凉水摊,是分币
是雀跃着端起玻璃杯的小女孩
不知荠菜是荠菜
从小学课文里记下
轻捷的步子,嫩生生的荠菜
下在玉米糊糊里
撒上盐花……
课堂上,馋虫从作者笔下爬进我心里
折耳根,马齿苋,野葱,蕨苔
吃过的野菜里
荠菜没挂上名号
有种干油菜,开碎白花
小女孩会折两枝别在辫子上
说是可防蚂蚁往身上爬
茎细细的,风吹来,个头窜得飞快
竹蜻蜓那样擎在掌心轻轻一搓
若干绿三角摇头晃脑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香包
我喜欢叫它香包草
多少年后再蹲下来分辨:
香包状的短角果还没往外冒
碎碎的白花还来不及开
茎还没抽条
嫩生生趴在田坝,趴在山坡
趴在暖融融的春天
干油菜也好,香包草也罢
挖上一提篼
搅玉米糊糊,剁馄饨馅,烙饼,炒蛋
以荠菜之名住进五脏庙
蔚蓝的天空下,更多事物一直都在
我还不知它们是它们,如同我不知
荠菜
是荠菜
你的孤独是哪一种
产生切肤之痛的孤独
是难以适应身边的人突发意外
成年人的孤独
是拼尽全力发出呐喊
却连身边的人也选择听不见
习以为常的孤独
是独生子女多年的磨砺,同空巢老人那种
略有不同
隔海三千里
小男孩把耳朵牢牢贴在螺上
这是令人愉快的孤独,他迟早会
与大海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