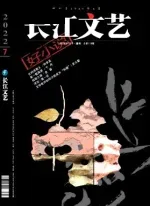近身慷慨
糖匪
那时候,我多希望她能虚晃一枪,不介意随之而来的疾速与坠落,压上自己,一举掀翻这个她笔下开始轻微摇晃的现实。在那个时候,她的章某某差点可以变得身形模糊,在模糊中扩散延展,成为每个人脚底下可疑的影子,成为她们心里被压抑的某个高音。
但是她没那么做。她要是那么做,她就不是马小淘了。
让我来谈马小淘。关于她的名字,关于和她初见的情形,可以杂七杂八说上不少,正确地浪费点字数,最重要是铺垫情绪。但还是算了吧。这种事脑子里过一遍就够了。写出来,她就不是她了。既然马小淘是一个人的笔名,有意识切割出的身份,那么无论出于尊重还是方便,就仅仅关注她的作品就够了。
向显现之物投以目光,仅此而已。提供这样简单的回路令我快乐。当然把文学作为考古或者心理分析也是方法,这些方法也许通向更广阔的世界。但我还是想让自己高兴起来先。
要说的分别是《骨肉》、《章某某》、《有意思的事儿多了》。
一
很难不注意马小淘鲜明的语言风格。要讨厌就更难。明快、流畅、狡黠,贴近日常生活,又出其不意,就那么毫不费劲地从普通碗碟里源源不断地变出兔子。是的,普通,如果你真相信世界上存在普通事物的话。大千世界人间悲喜, 已经被演绎过无数次的种种,用她的话再说一次,突然变得很必要,突然变得有意思。她看它们,有刀刃一样的凶狠和冷,无厚入有闲,游刃有余,卸成一块块,摆盘,还摆得很有她的风格。说私奔,她说:“私奔有什么浪漫的,私奔就是自私自利,自己酒池肉林,把别人扒光了扔到雪地里。”惨有很多种,同一种惨不同作家应该给出特别不同的具体描述。被私奔的惨,马小淘借主人公直接给出。准确有力同时新鲜。直接粗暴的比喻消解了文学作品里常见的悲情冲动。
读者几乎立刻知道自己可以喜欢上这篇小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她不会拉着你老泪纵横。这种敞开了调侃,一视同仁的刻薄——以前叫做臭贫,现在大概叫做增加读者黏性——会让人想起以前一些作家。他们有的成为文学边界的一块界碑,上面布满模仿者们的血渍,有的华丽耀眼一时,高烧般退去。他们的语言同样喷涌而出光芒四射,区别在于真正的界碑们绝不醉心语言的流速和反光。他们不挥霍,或者说,不自恋。
这方面马小淘和他们一样。侃侃而谈泉水般涌出的话,每个字都特别有用。《骨肉》开篇“我十二岁那年,我妈妈和我亲生父亲私奔了。”大白话一句,每个词都普通,放到一块立刻变得诡异,读者的心被紧紧勾住,滞留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现场,和那对被抛弃的父女一起,慢慢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小说就是这样有趣的技艺。比起“发生什么”,“怎么说”更重要。被重复许多次的故事,由不同的人讲就被赋上不同形状。不管作者愿不愿意,他们的故事都暴露出他们的灵魂质地。所以写小说是一件危险的事,尤其是面对聪明的读者。马小淘是她自己聪明的读者。写小说是她的左右互搏。她不写让人一眼看穿的小说,既然从来就没人能一眼看穿生活。
她那些看似不经意抛出的日常语言,没心没肺,全部经由深思熟虑的打磨。
写一个女人私奔的仓促,只说早上的碗筷没有收拾,吃了一半的酱豆腐已经风干,牛皮纸撕得参差不齐,字迹潦草,以及被女儿记一辈子的那个错别字。什么样的妈妈能写错亲生女儿的名字?就这几样,读者就亲临其境,站在台风过境后的一片狼藉中,体会当事人的震荡。于是省去了当事人各自心境的交代。接下去的对话直接进入到小说最重要的部分:被留下来的人怎么面对彼此和接下来的生活。爸爸先是一语道破女儿不是亲生。女儿直接回应——
“我会为你养老的,请别杀掉我。”我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为生存担忧。
“你以为我缺人送终啊?你这种苟且劲儿真像你妈!”他朝我大喊。
“什么叫苟且?这个词我好像没学过。”
“苟且就是,为了活,过一天算一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嗯,懂了,但是我妈她跑了,她没过一天算一天。我才是真苟且。我不跑。你对我动点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我新学的。”
实在是喜欢这段对话。言简意赅地交待前因后果,将一个私奔的母亲置于舞台深处,而灯光聚焦于两个不得不面对彼此互相提醒着对方伤口的人。从“我会为你养老,请别杀掉我”开始,马小淘定下戏谑的夸张的基调,一种喜剧式的失态,赋予下坠人物以轻盈,她的委屈求生和他的轻蔑不忿不再是笔直的加速度下落,而是有了更复杂也更有体面的姿势和路线。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有意思的意思是它耐人琢磨,人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在互相碰撞中发生了游移漂浮,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开辟出向内的悬念。一种让读者将目光集中在人物的悬念。尽管是第一人称叙述,人物并不完全敞开,仅以上述对话为例,半真半假的试探对抗宣泄需要读者自行判断。张力也来自于此。这对没有血缘的父女不仅彼此间需要一定具有形式感的交流,和读者也始终保持着距离。看似没心没肺第一句话上来就交底的那个“我”,始终收着,始终保持在一个叙述者的姿态里。她可以通达到告诉读者“也不是冷暴力,我们只是心情很不好,不知道互相说点什么。好像彼此的伤口都没有结痂,如果非要拥抱在一起,可能粘黏,重新留出鲜血”,她可以让人看到她和她妈用哭声互相回应对方的难看场面,“被命运吞噬的人,却一副要吞噬什么的姿势。我们两个都张着血盆大口,看起来一定非常丑陋。”她也无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洁白的少女,该计较的计较,该算计的算计,丝毫不在意被人发现她幸灾乐祸嫌贫爱富,“客厅不大,有一股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衰朽味道,廉价的空气精华液把那味道吞噬了。但还是残存了一点点,被我捕捉到”。多么坦诚又多么通透,但这些无不都是经过筛选凝练,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演绎。作者拿出最大的真诚藏起一些东西。读者看不到,却能感受到。人物憋着一口气,绷着一股劲,无论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还是故事里的爸爸。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怕那口氣泄了,心里某些东西就真的崩塌了。被命运碾过的人知道怎么狼狈怎么心碎都先放放,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从被碾过的地方爬起来。他们来不及也害怕先检查伤势,最多“短暂地哭一哭”。有些事情要先放一放,等到很多年后才有机会共同面对一个金色桀骜的太阳,坦然直面各自的深情。这个道理,一直幸福的人不会明白。他们充满安全感,他们之间“总要有胡搅蛮缠的瞬间,因为骨肉相连,不会被拆散,所以不必顾忌”。
我常常会想一个作者该如何庇护她笔下的人物?毕竟是我们让他们常常遭遇不幸。马小淘找到了她的方法。为了避免廉价的煽情,为了消解习以为常甚至条件反射的眼泪,她调动出一套语言,创造出一种喜剧式的失态,保持距离——所有人之间的距离,还有真诚——她自己的。她知道人有时候就像搁浅的抹香鲸那样义无反顾地热爱失败和沉沦。作为作者她给了他们不幸,但也给了他们尊严,以及迅速站起来的能力和智慧。
二
和《骨肉》不同,《章某某》中的“我”是个完全旁观者。
作者选择了一个很有趣的位置。我作为章某某的大学同学,不完全见证了她的北京奋斗史,从她刚念大学,到不断地意气风发不断受挫不断改名字不断调整轨道包括爱情的赛道然后继续奋进,到梦醒时分落地结婚举办了一场为所欲为扬眉吐气的婚礼,接着急转直下成了同学聚会上流传的轶事。
故事是章某某的故事,作为讲述者的“我”却渐行渐远——两人单纯地不怎么见面,而不是什么心理疏远,毕竟心理上似她们两个没怎么亲近过,至少作者一开始是通过“我”的口这么告诉读者的。受限于第一人称视角,受限于毕业后大家终将各自飞的社会现实,“我”讲述章某某的故事越来越仓促潦草,一路简化成碎片式对话,在短短一章完成毕业后十年的交代,最后连流水账都懒得写,在同学间相互矛盾的八卦里拼凑出个不那么确定的后续,以及确定无疑的结局。正如小说开头暗示的,章某某疯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故事。不少细节模糊,比如章某某她妈到底怎么回事;许多事掐头去尾起因发展需要靠想象,比如章某某最后是怎么疯的。“我”这个叙述者完全躺平,她不好奇不打听不追究不动情,没有丝毫要把这个故事说得活色生香的企图。她任由故事虎头蛇尾,与章某某泄气的人生高度同步。她像所有聪明人那样预见到章某某下落的轨迹,提前移开目光,为了不那么难受。
所以,她会难受。
或许,可以不那么相信作者,也不那么相信這个叙述者,尽管叙述者毅然而然用冷嘲热讽把自己保护妥当,一副置身事外客观冷静的样子。
小说开头也的确用了全知视角,将章某某在小城里的意气风发写得淋漓尽致。她土气不自知,她的雄心壮志,她脆弱的自信就有了前因后果,有了她的道理。于是,向章某某投去的目光就不能再是那种浮掠而过轻飘飘的目光。叙述者也好,读者也好,很难讨厌章某某和她鸟语花香的世界,甚至多少有点羡慕章某某的信念——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太聪明了,所以,我们不会受伤。当章某某一次次改造自己比如改她的名字时,叙述者就像野生动物学者观察野生动物那样,全程几乎没有介入,保持距离,袖手旁观。随恋爱学业工作全面挫败,小城青年的雄才伟略彻底萎败,连她费尽心思改造的名字都模糊在她努力里。整个过程叙述者一直在那。你不能说她一直陪着章某某,她偶尔也规劝,但不做干预,也没有主动改变过她和章某某之间的距离。是的。她一直待在原地。不远不近。但是十四年的时间让这个距离忽然变得很近。近得会不忍心。叙述者并没有察觉。反而是章某某比她更早察觉到。章某某说“我觉得你还挺懂我的。”
这么多年,她站在近处。而对于一个被孤立的失败者来说,站在身边就是一种慷慨,就是义气。
马小淘为叙述者选定这样的一个位置,为自己选择了写作者的立场。她不走近疯狂,只在外部凝视,并且反身凝视自身的回避。这是她的近身慷慨。
只是,我曾经一度误会以为马小淘会涉险更近一步:在章某某婚前独白里我看到了叙述者的影子,相近的说话风格以及对这个世界运作机制的理解。那时候,这两人差一点互为彼此。要是她们真的是一个人呢?就像我们总是分裂自己一边保有稚气和梦想,同时世故圆滑拒绝献身。那时候,我多希望马小淘能虚晃一枪,让她的叙述者不要那么聪明,让现实感震荡得更外露一些,多希望她不介意随之而来的疾速而坠落,因为在最好的那个瞬间,她和她的叙述者站在浪尖,能够俯瞰深渊般大海和雪白浪花。不过,那样,她就不是马小淘了。
三
这题目像半句话,看着它总想问下一句:是啊,然后呢?
《有意思的事多了》是一篇写开了的小说。不像《骨肉》结构严谨特别正统,也不像《章某某》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形式感。这是一篇特别松弛的小说,仍旧继续着马小淘式的“贫” ,仍旧写身边的普通人。这里面没有输家,没有需要屏住一口气才能撑过去的坎,就,忽然间,开阔了。作者忽然发现她已经什么都可以写了。
故事里三口之家,主心骨“我”妈,学校门口的裁缝“汪姐”。在人们还需要裁缝的时代,她为大学女性提供了最硬核的审美支持,还贡献出一片小小精神飞地,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她热爱生活、能量过剩,时代大潮都没冲垮她。她认清形势,及时转弯,改行开了干洗店。日月更迭,人事变迁,她总能找到有意思的事,认定就做。
“我”爸,体校俄语老师一名,存在感不强,随着文学事业发展,有了能让女儿狐假虎威的资本,但很快碰到了玻璃天花板,回到原来的位置。
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人物沉浮的时代剧,更不是励志职场剧。它好像就在讲一家三口这几年的变化。读的人觉得有意思停不下来,好像在过一个无比快乐的暑假,倏忽间就过完了,一时没想明白时间去了哪里。而她写的恰好是时间——是时间让有意思的标准发生变化。
最早,时间几乎是凝固的。大院里以不变应百变的称呼(全院不管年龄辈份都管看门何大爷叫大爷,管汪姐叫汪姐)代表人际间稳定的情感联结和社会关系。他们之间稳定,可以对抗时间流逝。毕竟那个时代时间流逝很慢,慢到让“我”恍惚,“不确定是进了什么样的时空隧道,还是她们真的就这么虚度了两小时”。
在这里,敏锐的读者受到召唤,他需要辨识出陌生的抒情方式——藏在看似吊儿郎当的叙述里,看起来更像写作者无意流露出的怀念。然后他会被打动,被独特充满个人质地的情感传递打动,被其中的轻盈和不露痕迹打动。《有意思的事多了》里,不严肃的调侃继续着,只是变得不那么凌厉,变得温柔和仁慈。
实际上,不只是在《有意思的事多了》,马小淘对人物始终怀着一种谨慎的温柔。于是她会安插一个叙述者,站在离她真正要写的人物很近的地方。这样即使在作者和叙述者界限模糊的时刻,她仍然不在事件的中心。但她又离那些人很近,近到能感觉她们的温度和气味,近到会和她们的悲喜共振,和她们踏入了同一条时间的河流,感受一去不返的逝去,最重要的是,见证那些人内在光照的时刻——如果不站在那个位置,就捕捉不到的那个时刻。
当《骨肉》里的父亲为他被彻底围剿的生活或者别的什么,在一个陌生孩子坟墓前失声痛哭时;当章某某突然问出“你说我是不是正过着你妈的日子”时;当汪姐鲜有的不仁慈不体贴,拿出“我”的艺术照展开报复时——
所有的大道理、小聪明,属于人世间的智慧统统遁于无形。你破防了,你就像一面被风穿过缝隙的墙。你觉得冷,刺痛,在静止中感到流失。
也就是那个时候,光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