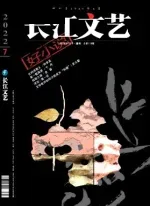革命历史的补白和英雄概念的延展
鄢莉
战争作为人类最激烈的对抗活动,本身具有无限丰富的样态。上世纪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革命战争,在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属性,其影响渗透到各阶层、各民族的方方面面,牵动着亿万人的命运。一部完整的革命战争史绝不单单是军事斗争史,而是一部恢弘壮丽的民族大历史。取材于革命战争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应多种多样、包罗万象,不仅有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有战场外的儿女情长;不仅有军人的壮怀激烈,还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军旅作家陶纯近年有志于寻觅“藏在汗牛充栋的党史和军史的缝隙中”的历史原型,“试图将埋没了的历史挖掘出来,吹去尘埃,擦亮它,让它发光”。通过一批实实在在的作品,他正在成功地实现他的诺言,恰如杂史、方志等别史可佐正史,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走出对“大题材”的迷恋,在被前人忽略的领域开掘题材矿脉,寻觅曾被遮蔽的人和故事;他以历史补遗者的身份,对革命战争的煌煌历史加以填充和补白,通过新颖的叙事模式和强烈的个人风格,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军事文学的“一座营盘”。
历史的缝隙,恰恰就是故事生长的地方。《根》《七姑八姨》《过来》《黄土谣》《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等作品,视角具有“向下转”的倾向,将省察的目光投向了参与战争的普通人。一般而言,革命军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当然主角,而陶纯有意将军人置于次要地位,而将更多革命战争的边缘人物推向前台,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事迹。尤其是,他对传统英雄的概念加以合理拓展和溢出,大力赞颂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平民百姓,对传统英雄谱系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例如本期推出的中篇小说《黄土谣》,将历史的长镜头拉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边区,将浓墨重彩集中于一位闻名遐迩的劳动模范赵有良身上。赵有良本是贫苦农民出身,因为与地主斗气赢得劳动竞赛,方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通过无私的奉献,成长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又如另外一篇新作《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描写了一个编外的抗日奇侠陶校长,他以一介书生身份投笔从戎,拉起一支“钢枪加鸟枪”的民间武装。这支八路军也不愿收编的队伍,勉强命名为“清水县武工队”,与敌人鏖战七年,击毙日本鬼子若干。《七姑八姨》讲述的四位女性中,庞壮英和苏三妹是牺牲和被俘的红军战士,罗秀娥和何四姑连军人都不是,前者是红军团长的前妻,后者是牺牲烈士的未婚妻,《过来》中的外祖母李慧芬是军人包办婚姻的妻子,她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战争,用女性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战争的苦难。
对革命历史的补白与对平民英雄的刻画,并不只是陶纯受经典作品影响下的创作策略,更是一种自发自觉的追求,从认识历史的角度亦可看作是其“人民史观”的充分体现。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本该大书特书。阅读《黄土谣》,能够让读者对陈毅元帅那句“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有直观的感悟: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若不是赵有良们默默支撑起边区经济,为军队贡献儿女,何谈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常言“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看过《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谁敢说抗战的胜利不是哑巴、王七、小眼等这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百姓用生命换来的?至于《七姑八姨》《过来》中的弱女子们,尽管她们不曾做出与男性比肩的功绩,但是她们以女性生命承受的战争代价岂容忽略?这些主人公们穿插在大历史之中,展现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融合共振和对历史的巨大推动力量,更隐喻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决定作用,他们的存在使得革命历史的图卷背景更加饱满,细部无比真实。
人民史观给予了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以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创作空间。战争创造英雄,英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当然的表现中心,然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是随着时代发生流变的。“十七年文学”中以杨子荣、沈振新等为代表的完美无瑕的英雄在新时期被打破,梁三喜、靳开来等有缺陷的英雄在盛行数年后又因为“人性论”的鼓吹,让位于姜大牙、李云龙等浑身是毛病的英雄。在此之后英雄形象逐渐走向固化,乃至陷入某種僵局: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英雄不再受欢迎,但是过于“非主流”的英雄模糊了英雄和非英雄的界限,是否又造成了对英雄形象的认知混乱?陶纯对英雄概念的合理延展,打破了英雄塑造的二元困局和悖论,走出了歌颂英雄的思维定势。在塑造平民英雄时,他的创作是松弛的,是放得开的,是摆脱了塑造英雄的“偶像包袱”的。他既无需刻意为人物添加光圈,也不必迎合人性论而对人物加以矮化。虽然他笔下的平民英雄身姿不那么伟岸,事迹也不那么壮丽,但他就是能够从平淡中咀嚼出味道,从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赵有良、陶校长等形象能最大程度逼近历史真实,正因为生动贴切的故事就是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流淌出来的,而不是演绎加工出来的,温暖动人的情感是从他们的心里满溢出来的,而不是刻意煽情的结果。
战争与人的关系是军事文学永恒的主题,这牵扯到作家对战争本质和人性的终极认知。英雄叙事强调描述英雄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而平民叙事着眼于战争对人的影响、人在战争中的命运。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打造平民英雄的同时,亦从不回避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深重灾难和巨大不幸,死亡、眼泪和创伤在他小说中反复出现、久久回荡。于是这些作品既未脱离主旋律的轨道,却又笼罩着一层惨淡的悲悯的色调,传达出作者对战争多层面的观照,成就了一部只属于作者的战争沉思录。
军事文学对战争的反映应该是多维、立体、全息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写战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也是写战争。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为历史查漏补缺,为平民英雄树碑立传,充分张扬了人民性的写作立场,践行了人民史观的创作理念,讲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国故事。蹚出了 一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持续表达着他“感悟英雄、品味苦难、嗅到芬芳”的情怀。从创作的势头来看,他累积的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或将有更多别具一格的作品喷涌而出,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增添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