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竹工
褚福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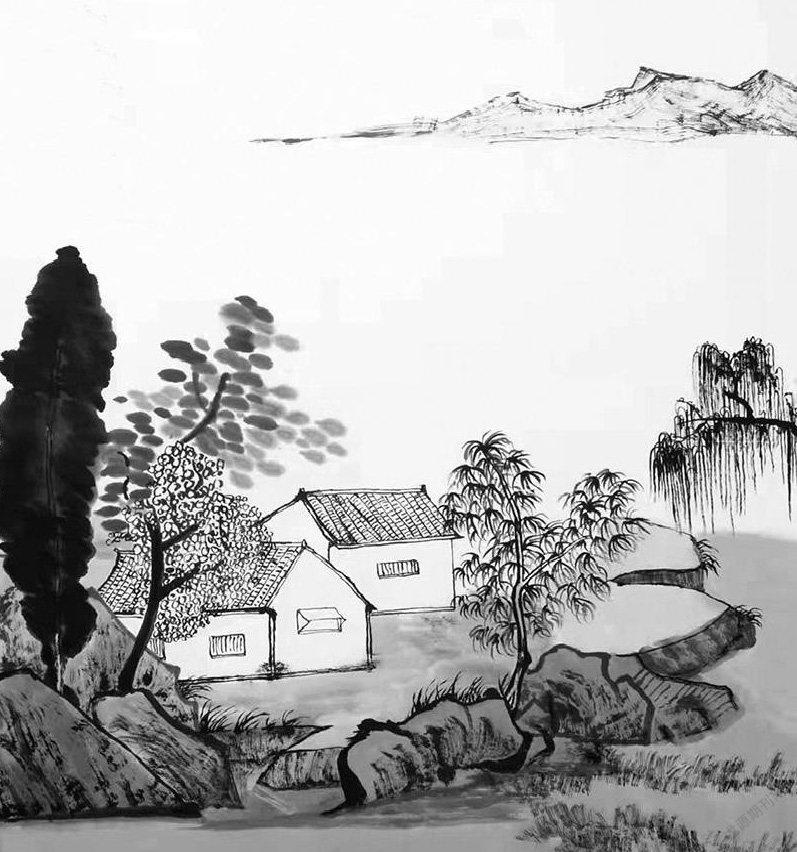
小雪过后,暖冬如春,清雅怡人,宜南山区的毛竹愈发壮实了。
上午十时许,我们正在天目山竹海游玩,忽闻右侧半山腰上传来“哐当、哐当”脆生生的毛竹碰撞声。循声望去,但见一个中年男人肩上拉住捆扎好的竹梢,正佝偻着背,沿着石阶,一蹦一跳着大步往山下俯冲而来,身后十来棵碗口粗的毛竹顺势而下。数秒钟后,抵达开阔平地时,那男子脸色红得如关公,上气不接下气,胸膛急剧地起伏着,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滴答、滴答”滚落,立于山涧那侧,“咕咚、咕咚”灌茶。
首次目睹此情状的我,极为诧异。
不远处,站着一个矮胖的妇女,一看便知是他老婆,腰上围着玫红围裙,正在将拉下来的毛竹调头。毛竹下山时,是竹根在后、尖梢朝前的,而装上卡车时,必须大头朝前,故而需将毛竹一一调过头来。但见她弯曲着肘部,把竹梢捧在臂弯里,倏尔使劲旋转着奔跑,那毛竹乖巧地随她而转,听话地调过了头来。每次两根毛竹,男人拉的一趟,够她旋上五回的呐。
中年男子喝完茶,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呼吸仍显得略微有些急促,右手不住地在脑门儿上揩汗。我趁隙与他攀谈起来。性格直爽的他,先斜睨了我两眼,而后解除了戒心,用浓重的川腔告诉我,他老家是重庆云阳的,来阳羡竹海已有近五年了。虽然伐竹很辛苦劳累,几近卖命地干着他人不愿意干的苦活,可每月上万元的收入,还是叩动了他的心。晴好天气时,他清晨六七点钟便起身,吃饱早餐,脚蹬球鞋,绑好裤腿,腰挂竹刀,像松鼠一样钻进竹林干活。一棵粗壮的毛竹,只消被他“咔嚓、咔嚓”四五刀,便从根部砍断,先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后,颓然顺势倒下了。相对山顶的毛竹而言,砍山脚与半山腰上的,算是轻松的了。最让他惧怕的,是长在山巅上的毛竹,砍下了,一不小心会顺势滑溜下去,跟他玩失踪。偶尔甚至会伤及无辜,所以他不敢懈怠。毛竹砍下来后,他得把它们拢在一块儿,码稳,然后十棵一次,分批拉下山去。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由于石阶较陡峭,下来时稍有不慎就会扭崴摔伤,而且因地势倾斜,毛竹下滑非常迅速,所以,作为向导的他,在前面就得不顾命地狂奔。为防止石阶损伤毛竹,他们每间隔一段距离便横放着一根毛竹,架空竹子,以免毛竹与石块摩擦,同时也使毛竹下山时更顺畅省力。不过,速度快得让他犹如猩猩似的连蹦带跳。那会,时间才十时半许,已缓过神来的他或许是感到肚皮饿了,便问他老婆:“饭送来了吗?”“就在那边撒。”于是,他颇为急切地走过去,蹲下,从手提袋里拿出餐食,先打开一只装菜的快餐盒,再拿起另一盒饭,坐到横卧地上的竹枝堆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午餐是老板免费供的,红烧鸭腿、大蒜炒干丝、炒青菜,尽管简陋了些,可他吃得津津有味,感觉很不错。对质朴憨厚的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奢望,能填饱肚子,不致挨饿,就知足了。他边咀嚼着食物,边嗡嗡地对我道:“伐竹工的活确实累,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急需钱花的地方多着呐。我们每年做一季,少说也能挣上个几万元钱。”
话音刚落,拉毛竹下山的卡车驶近了。他匆忙把剩余的最后一口饭菜扒拉进嘴里,鼓着腮颊,朝我歉意地点了点头,就闪到车旁装车去了。十来米长,直径约有十二三厘米粗的毛竹,一棵少说有七八十斤重,他与他的同伴们,轮流弯腰拎起,吃力地走到车旁,再举到高过他头顶的车厢,递给车上接应的人。一车大约要装二千五百棵左右,也就意味着他俩要弯一千多次腰。劳动强度之大,体能消耗之巨,不是一般的人能吃得消的。待车上毛竹装满了,他像只灵猴般轻盈地爬上去,扣牢紧线机上钢丝绳的一端,再慢慢撬动扳手,“叽叽”将绳收紧。依次而为三次,才算将车上的毛竹稳固好。至此,他阶段性的工作方告一段落。
另一位小伙子,人矮矮的,精瘦精瘦,面色黝黑,湖南醴陵人。他是由亲戚引荐过来的,做伐竹工不到两年,已基本掌握了伐竹的技能。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都要砍伐二三百根毛竹,山上山下得往返跑好多趟,一天下来,有时小腿肚子上的肌肉都在打战,夜里睡觉腿常痉挛,但为了生存,抑或是扭转命运,他选择了来此伐竹。说罢,他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掌,不无幽默地朝我“炫耀”起来:这是生活赏赐给我的奖章。我抚摸着他粗糙的手,除了怜惜,更多的是佩服。
卡车装载着堆得高高的毛竹,一摇一晃着缓慢朝山下驶去,引擎声渐远渐弱,沿山坡拐过弯,便消失在视野尽头。
他们立马转身,利索地在腰际挂好竹刀,手拎大茶杯,又欲上山伐竹去了。我受好奇心驱使,自己都有些意外地断然决定跟他们上山去,真切体验一下伐竹的感受。
走在弯曲陡峭竹海山道上的他们,步履铿锵,脚下生风,发出“嗖嗖”的声响,我几近小跑方才勉强跟上。他们窥见我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便择就近的竹林砍伐。中年男子关切地问:“怎么样?”我佯装若无其事,洒脱道:“不要紧。”接着,中年男子无保留地对我口授:“你马上砍毛竹时,应将刀口对准竹子根上部,发力要猛,下手需狠,晓得撒?”我谦逊地点点头,接过他递来的锋利的竹刀,瞄准一棵成年毛竹,自信地使劲挥刀砍去。一刀,二刀……直至砍了六刀,那毛竹依旧岿然不动。此时,中年男子急了,对我吼道:“你用力砍撒!”我用尽吃奶力气,又狂砍猛砸了三刀,才清晰听到竹子发出了轻微的“吱吱”响,那小青年眼疾手快,毅然伸出手,轻轻一推,毛竹便应声倒地。继而,小青年抽刀把竹枝削净,用带有戏谑的口吻说:“你现在可以扛着下山喽!”素来不服输的我蹲下身子,跨成弓步,先把大头这端架在肩膀上,再前移竹子,平衡好后,便奋力朝山下走去。可山路陡峭,别说扛了毛竹,即便是空手下山仍是很费劲的。故而没过多久,我的腿开始变得沉重起来,走路歪歪扭扭,显然是力不从心了,但依然咬住牙艰难行进着。未过两分钟,我嗓子已欲冒烟,有种行将窒息的感觉,猝然眼闪金星,双腿一软,人一个踉跄,栽在路边的乱石上,毛竹脱离把持,“骨碌碌”地滑了下去。跟随我身后的中年男子惶恐地扶起我,关切地问:“你么(没)事吧?”我歉疚地摇了摇头。
他们见我无大碍,便转身忙去了。我凝望着他们结实的身板,汗渍斑斑的背影,心里蓦地渗出了敬仰之情。
责任编輯:黄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