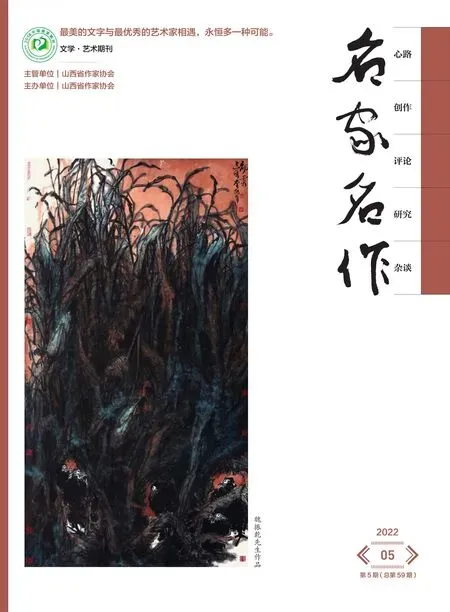浅析《心》中夏目漱石文论之遂行
汪 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小说家,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伟大的人生导师”等,其作品形式自然、寓意深远,长期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作品《心》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主题深远,成为夏目漱石后期代表作品之一。文章发表于1914年,主要讲述在校大学生“我”结识了“先生”,在接触交流当中发现“先生”总是怀疑众人甚至自我,与妻子看似幸福的婚姻也是谜点重重,最终“先生”通过遗书的方式向“我”坦白了他内心的秘密。遗书中主要讲述了他在学生时代爱上了房东家的小姐“静”,但由于此前在父母去世之后受到过叔父一家的欺骗谋害,导致他对包括房东太太在内的周围所有人都充满怀疑。他邀请了同样遭到家族抛弃、一心求“道”的好友“K”一同搬进房东太太家,之后“K”也爱上了小姐“静”。当“K”坦然地向自己倾诉内心情感时,出于嫉妒,“先生”表面痛斥“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是渣滓”,私下里却迅速向房东太太提亲,获得了与小姐“静”结婚的允许,最终“K”不堪多重打击,自杀身亡。婚后“先生”深受良心道义的谴责,始终活在痛苦忏悔当中,最终也选择自杀以求救赎。作品通过对“先生”、青年学生“我”、友人“K”、妻子“静”(小姐“静”)、“我”的父母、房东太太等一众人物形象的刻画,主要塑造了孤独利己的“先生”、好奇单纯的“我”、温柔细腻的“静”、执着堪“道”的“K”等众多人物及人生际遇,表现了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孤独不安与内心探求。整个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故事情节的安排真实自然,体现出作者在文艺创作中崇高的文艺理想和审美情趣。
1907年,漱石在东京美术学校文学会上发表题为《文艺的哲学基础》演讲,其中指出:文艺家永远不是闲人,他们必须解释清楚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人生的意义和理想,他做不到这一点,写作技巧即使再高,也写不出高水平的作品。漱石进一步指出:文艺的理想体现在真、善、美和庄严四方面,而绝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只有实现这四个理想,才能触及人生、感化他人。
可以看出,漱石对于文学中内容与形式、伦理道德与写作技巧的关系等问题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他认为技巧是工具,是表现作家思想的手段。作家创作不能只考虑形式技巧而脱离思想,也不能没有技巧手段只重视思想。在文学作品中只有将这四方面材料合理安排、自然分配,才能最大限度自然真实地呈现出作品,也才能深刻隽永地体现出文章的思想感情,给人以教谕。夏目漱石的《心》自发表一百多年来,之所以一直受到众多读者及漱石研究者的欢迎,与作品中真实自然的人物情节安排以及深刻隽永的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试从漱石提倡的真、善、美和庄严四个文学理想出发,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及主题,体味漱石《心》中的文学之美。
一、内容“真”
漱石认为文学作品的自然,不是对自然界的描写,而是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是否真实自然的问题。在《文学评论》中,漱石指出:“如果要让读者读后觉得从小说中仿佛看到真实的社会,那么不仅仅小说的事件要写得自然,人物性格的发展也必须自然。同时,还必须有背景描写。所谓背景即小说人物出场的舞台或者是围绕人物的四周环境。”
作品中的“先生”是一位孤寂、痛苦、悲哀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是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一点一滴塑造起来的。学生时代不谙世事的“先生”,“不仅相信叔父,还常以感谢的心情敬重叔父,庆幸有这样一位亲人”。为什么感谢敬重叔父甚至引以为豪?文中有交代:叔父是个实业家,还当过县议会的一员,同政党也有交往。父母去世之后,叔父“迫于无奈,勉为其难两头跑”,从东京回乡之后,“叔父把占据我原先所住房间的一个男孩赶走,把我让了进去……我谦让说其他房间也没关系,但叔父不允,说这是我的家”。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未出社会、失怙无依的少年当时对世上唯一的亲人——叔父抱着怎样的心理上的依赖?对貌似务实能干的叔父抱着怎样的敬佩自豪?毫不为过地说就是当时他的全部依靠啊。那么为何当时的“先生”那般“不谙世事”、单纯幼稚呢?一方面当时“先生”还是在校学生,未出社会,另一方面父亲是个“老实厚道”之人,平时以插花茶道自娱,喜欢看诗集,是一个“情趣高雅的乡间绅士”。父亲在世时常说“像我这样继承父母财产的人,无论如何要收敛锋芒”“用不着与世相争”。家底丰厚,又有着这样一位情趣高雅近乎隐士风范的父亲的教导,少年时期不谙世事的“先生”之形象再自然不过。
被叔父欺骗遭其谋夺财产之后,“先生”对周围所有人变得“不信任,有敌视情绪”。“先生”没有独住而选择租房,是因为独住需要请老婆婆,离家在外放心不下。搬到房东太太家,“我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像个“不偷东西的贼”。房东太太有意无意避免“先生”与小姐私下接近,对“先生”抱有戒心。在没有充分了解一个租客的情况下这本是再正常不过,无可厚非。在“先生”和盘托出家庭际遇之后,房东太太了悟心疼“先生”,“就像对待她一个年轻亲戚或者什么人一样待我”,态度有所改变,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防范小姐与“先生”接近。站在房东太太和读者角度,这是在了解事情真相之后的放心、放手,而“先生”却又疑心起来,“怀疑夫人说不定以叔父那样的用心来促使小姐接近我”,怀疑“两人可能凡事都是事先在背后策划好了的”,认定房东太太是“狡猾的阴谋家”而敏感多疑。这一时期“先生”之形象可以概括为一个“疑”字,对周围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充满怀疑。因为有了前面受叔父欺骗的经历的交代,促成了对房东太太和小姐的敏感多疑,这部分可谓“疑”得自然。这种自然合理的情节安排文中处处可见,它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变得立体多面,后面情节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选择也显得真实自然。
二、道德“善”
伦理道德是漱石在艺术审美和创作中的主要美学追求。他主张道德是文学的重要元素,应该作为重要的文学内容,认为“道德也是一种美感”,肯定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但恋爱故事要注意社会效果,不违背道德原则。
“K”与“先生”是同乡,或许是对“K”被亲人无情抛弃之后凄凉无依的感同身受,“先生”将“K”拉入房东太太家与自己同住,想尽可能提供关心帮助。他告诉夫人和小姐,“自己把K接受过来,心情上就好像怀抱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情愿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对方”,拜托她们也务必热情对待,给予关爱温暖。可以肯定,“先生”在邀请“K”同住之初,一定是抱着帮助好友的打算和决心。你可以想象“先生”在受过至亲族人的欺骗、心灵上受到重创之后,还能怀有一颗赤忱之心、愿意帮助他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一直以来,关于“先生”,读者多是以“自私利己”来概括形容,笔者认为实在偏颇不公。很显然“先生”一开始绝对是出于帮助“K”的初心才会邀请其同住,否则当时敏感多疑的“先生”又何必多此一举?至于后来“K”的悲剧绝不是“先生”故意为之,并且也并不认为他是促使“K”自杀的唯一原因,只能说是人物性格使然。
当“先生”发现“K”与自己一样也爱上了小姐“静”之后,“先生”对此前自己因“担心上当上骗”思前顾后、畏首畏尾后悔不已。在“K”向自己坦白心事之后,激发了“先生”的嫉妒好胜之心,私下里迅速在房东太太面前获得与小姐成婚的允诺。对“先生”而言,在这场战斗中虽“用计取胜”、先人一步,“但作为人却失败了”,自此“意识到自己有了伦理上的弱点”。“当时被叔父欺骗,我无疑深切感受到人的不可信赖。但那只是觉得别人不好,至于自己还是地道的,心里边有这样一个信念:世人如何不论,反正自己是正人君子。”然而这一信念在情场争斗中土崩瓦解,“先生”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同叔父一样,是个手段卑劣、毫无廉耻道义的卑鄙小人罢了。“先生”从此前的对别人失望到对自己失望,他体会到了来自他人的恶,也深刻体会到了自己的恶,从此每天活在愧疚与忏悔当中,认为自己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孽,于是在不堪伦理道德讨伐之下而选择自杀。试想一下,倘若“先生”真是一个毫无廉耻之心、彻底道德沦丧之徒,他只会心安理得享受接下来的幸福生活,如何又有了后来青年学生“我”所见到的痛苦、颓废、孤寂的“先生”呢?难道不正是因为“先生”为人品质高尚,才会使自己一直陷入痛苦的自责、忏悔之中,并且最终不堪重负、选择以自杀以求救赎吗?可以说小说虽是一部道德悲剧,却是作者为“先生”安排的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也正是漱石自身通过文学作品展现给众多读者的道德选择。
三、形式“美”
漱石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在创作中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他坚持艺术上的真实,而非科学上的真实。为了使读者感觉作品真实自然,漱石巧妙地运用各种文学创作技巧。
漱石十分重视空间短缩法。他指出,空间短缩法即“使作者的影子完全消失,从而使读者能够和作品人物面对面坐到一起”。为此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读者带入作者角度,使二者站在同一立场;二是作者本身化为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作品主人公,以便读者直接感受作品中人物的气息,减少作家的指挥干涉。很显然这里是说视点处理的问题。漱石十分重视“我”与“非我”的关系,使用第一人称“我”将读者带入作品,跟随作家一起观察感受作品是其常用的手法技巧,《心》中在校青年“我”及“先生”遗书中的自己——“我”都是使用这种方法。化身为在校青年的我能感觉“先生对我不时流露出的看似冷淡的态度和缺少人情味的举止,其用意并非是要疏远我”,好奇“先生”的过往经历,会感受到“先生”的静寂孤独;化身为“先生”的“我”跟着“先生”一起回忆了当时自己的敏感多疑,直面了“先生”对“K”的忏悔以及个人内心世界,对“先生”当时的内心矛盾纠葛有了感同身受的深刻认识。总之,这种“我”的万能视点方便作品人物观察自己和他人,任意抒发“我”对其中人物、事件的看法意见,方便走进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深深感受到故事情节的真实及人物性格的复杂。
漱石认为巧妙地利用自然景物打动人的心灵,是东西方文学作品的共同规律。为了达到情景交融,作家需要将自然风景与故事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装点得天衣无缝,使读者真正能够共情、生情。当青年学生“我”完成毕业论文时,写道:“我以小鸟出笼的心情,纵目四顾辽阔的田地,自由地拍打翅膀……沿途枸橘篱笆黑乎乎的枝头冒出胀鼓鼓的嫩芽,石榴树干巴巴的树干上那珠滑玉润的茶褐色叶片柔柔地反射着太阳光,它们一路吸引我的目光。”此刻,之前寻常的景物都显得美好,那种经过长时间的憋屈忍耐之后,终于甩脱包袱后的“我”的松快欢快伴随着春光春色一下子跃然纸上,让每一位读者都感同身受。作者深刻把握住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巧妙做到了情景交融,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
另外,漱石主张运用一些时事问题增加作品的趣味性,认为如果“不触及人世间的重大事件,其趣味性将会大减”。他所说的“重大事件”,指的是政治斗争之类或者涉及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心》中涉及的时事问题主要有两处:一是“父亲”在病中通过看报得知明治天皇去世和乃木大将殉死的消息,二是“先生”在遗书中交代自己下定决心自杀源于明治天皇驾崩,觉得“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终于明治天皇,受明治天皇影响最深的我辈再活下去毕竟已经落伍了”,因此决定自杀以殉“明治精神”。这里“明治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先生”自杀的真正原因等问题前人也多有研究,作品通过适当插入时事材料,让读者感觉作品叙述的就是自己的身边事一样,贴近日常生活,显得真实、自然、可信,也对小说中心旨趣起到很好的点睛明义作用,而这也是
漱石作品的感染力所在。
四、蕴“庄严”
“庄严”是漱石主张的四大文艺理想之一,他认为文艺家的使命在于如何更好地解说生活,教给平民百姓生存的意义,强调作品一定要有内涵和深意,要对普通民众有教化作用。《心》自发表百年来之所以对其的研读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教诲意义。“先生”落寞孤独、生不如死,“K”尝遍人情冷暖、求“道”无门,他们最终都以自杀终结了生命以求解脱,这种破坏性的结局方式给无数读者以恐惧与震撼。他们代表了日本明治时代新旧交替时期无数迷茫焦虑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从上而下急于求进、囫囵吞枣式的盲目西化消化不良、惶然无措,他们一方面在政府推进引导的西化教育中追求自由平等、个人本位,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东方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挣脱不得,造成了新旧交替时期日本民众精神信仰上的矛盾,即“大我”还是“小我”的问题,“先生”与“K”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纠葛中最终选择了自杀终结生命。而正是这种压倒一切的毁灭性结局才能最大限度给读者以痛苦、恐惧和震撼,而这正是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最“庄严”的个人选择——向死而生。
真、善、美和庄严是漱石整个文艺创作的至高理想和哲学基础。他主张文学作品要真实自然,但绝不赞成自然主义的技巧无用论。他坚持文学创作中技巧的重要性,但也绝不一味坚持唯美主义。他批评自然主义,也绝不苟同于唯美主义。相较于自然主义的无理想,一味地、客观地描绘社会和个人的阴暗面,漱石有自己的道德选择和审美标准,并且可以准确找到其中的平衡点,在作品中表现人生真实的同时,给世人以教诲和警醒,这些正是漱石文学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