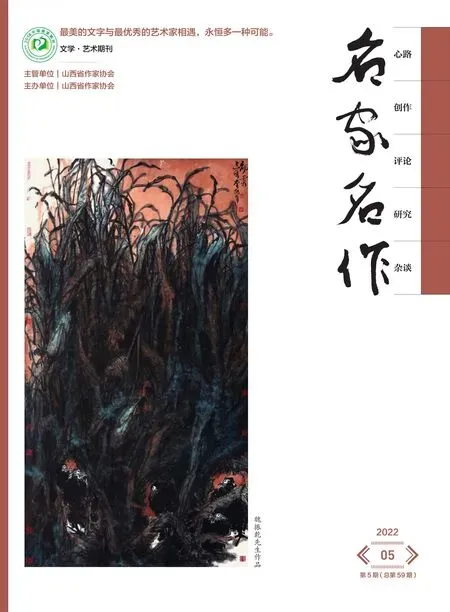从“自然美”的审美角度略谈《湘行散记》
蒲泉伶
一、引言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里提出:“美的本质和根源是自然的人化,主观实践和客观现实的交互作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说认为:“自然形式与人的身心结构发生同构反应,便产生审美感受。”“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作为一本真实记录返乡见闻的散文集,淡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身份,从而营造了一个“比人的世界大得多的文学世界”。因此,本次研究将从湘西的自然景观入手,对其作品《湘行散记》中的湘西世界进行“自然美”的审美角度研究,探讨作品中如何描述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的关系,以阐明自然与人的联结,体现出沈从文作品里有关自然和人性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审美意象:河流生与死的隐喻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直言:“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可见从年少时开始,沈从文的人生就一直受到“水”的滋养;到了中年后,他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还是动情地谈道:“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可以说,水在沈从文的一生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汪水具体而言,就是著名小说《边城》、散文集《湘行散记》中描写的,拥有五条支流、流经十个县并且拥有百个河码头的湘西之源——沅水流域。
沅水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最核心的风景和意象,在某种程度上讲,沅水就代表着湘西。因此,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特别侧重“水”意象的刻画,“水”是湘西景色中的主旋律,沈从文笔下的“河流”是一条生存之河、 生殖之河、 生死之河。 河面上漂流着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痕迹,河中景象是河的两岸一切生命场景的倒映与复指。“街的岁月就是河的岁月”, 街上流动着的人事就是河中流动着的水。因为人们依水而居,所以有“水手”,有“妓女”,有“船”,所以有无数动情的故事发生。水的柔情和残酷也渗透到湘西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中。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野性的湘西人会有一份如水的自在和韧性。这种如水的性格让落后的水手、妓女等湘西人拥有独特的善良和美丽。从宏观上说也是沈从文对城乡文明、历史发展与停滞的思辨性表达。
(一)生存之河
“看他那数钱神气,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为一百钱大声的嚷了许久,我有个疑问在心:‘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不止这人不想起,我这十天来所见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这种事情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希奇的。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
如果说在《横石和九溪》中沈从文还对这样的生存方式有高下远近之别的判断,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历史是一条河》中,他彻底抛却了之前的观点:“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的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的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有趣的是苏童写过《1934年的逃亡》这样一本小说,亦是建构在1934年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逃亡,表达了溃败的农村向新兴的都市逃亡的历史。小说中的新老竹匠与沈从文也有映衬的地方,灵魂似乎都是那么孤独,飘荡在乡村,又沦落在城市,而在心灵最柔软的深处,又不断地频频回首于故乡。这种乡村到城市的轮回,又寄托着逃亡与还乡的记忆。在这种记忆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湘行散记》亦象征着某种意义上的流变与逃亡,到了湘西世界中,沈从文观察劳作的水手如何日复一日与大自然抗争,从最开始的“为生存而生存”的评价逐渐转变为“顺从自然环境的恶劣,但依然与生存环境斗争”。
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拥有一份古朴的情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描写了情欲的人化,“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水手牛保拿到苹果第一时间并不是去撑船,而是送给吊脚楼里的妓女。这份感情在他们离别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份不舍让人格外怜悯。
“陌生人自然也有来到这条河中来到这种吊脚楼房子里的时节,但一到地,在火堆旁小板凳上一坐,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称为熟人乡亲了。”在这样质朴的环境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亲切而自然,陌生人自然成为熟人乡亲,这是沈从文在湘西河流所闻所见,对其生存意义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幸免于其灵魂的流亡。
(二)生死之河
那时的人们根据周边的环境优势来决定生存的方式,湘西的这条河养育了无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其中水手在这条河上奉献了整个生命,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似乎已经注定了的命运。
“至于小水手……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在这样一个地方,有着一座坟茔,上面刻的碑文,充满了水手对河流的依赖,却又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这时的河是凶险的,似乎随时都会把河上的生命榨干或是淹没,此时河流汹涌中充满着哀鸣。
《桃源与沅州》中还提到两处死亡:“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守城兵与特派员所带领的请愿群众发生了冲突。结果站在最前线上的特派员同四十多个青年学生与农民,便全在城门边牺牲了。那个特派员的身体,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
提到屈原之死,或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湘西是巫傩文化的发源地。沈从文从小就受到鬼神的影响并参与其中,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带有鬼神文化氛围的印记,具有神性特征。例如,他经常引用古苗族民间传说作为题材。他的许多小说都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湘西传说和故事,描绘了神秘的楚巫文化和浪漫的古典情调,充满诗意。从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湘西世界存在着狂欢和疯狂。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狂欢状态,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脱离一切世俗的规则。这种神秘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沈从文想要宣扬的“神性”。在作品中让人物无私地追求自己喜欢和想要的东西,展现出巫神的精神内涵,那就是蔑视一切外在的规则,寻求内心的释放。
在这样一条河流上,自然力量以常常激发人的悲哀为特征,其河水汤汤的幻灭和孤独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感,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现原形,本体的探询与感受无处遁形。“屈原”与“特派员”之死,某种程度是类似的,他们的选择都是自我意识的充分显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而非一时的冲动或者迷信的盲从,又如王夫之所说:“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
三、审美表达:语言在自然中的构建与消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美学之谜是各门艺术对我们发生作用之谜。”艺术并非私人的心理,它是公共的游戏。游戏虽无规律,却有参加者必须遵守的规则。而艺术的这种规则,是与一定的生活和文化紧密相连的。维特根斯坦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
在《鸭窠围的夜》中,出现各种描述声音的场景和语句:“钢钻头敲打着沿岸大石头,发出好听的声音。”“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羊还固执地鸣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锣鼓声音,那一定是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音所在处必有火燎与九品蜡照耀争辉。”“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动物声、人们交谈说话声、妇人的歌声、工具声……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鱼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战,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无不交织形成了一首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和谐自然的赞歌。
而《过新田湾》中则有著名的乡野景色的描写:“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小埠头停船处,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A字形,或相间以红萝卜。”通过描写鲜明的绿色、红色,用最鲜明的部分来组成画面,调动感官的知觉,勾勒出湘西的瑰丽,用河岸与田间的景色带给读者视觉上的冲击力和明媚秀丽的强烈的美感,完成用视觉对冲达到新鲜景色个人感知上的真实。
“感知的真实”代替了推理和感觉,使人思考性的痕迹,主观的情感甚至也不见了,完全融合在客观的景物之中。
这样的自然景色中,沈从文给夫人写的信当中曾表示语言无法抵达那样的场景,即使是声音也无法用文字比拟,“使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想用一组文字去捕捉那点声音,以及捕捉在那长潭深夜一个人为那声音所迷惑时节的心情,实近于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正是王夫之所说的“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语言可以建构感知的真实,但无法捕捉意境的灵动,在宏大的自然景观之中,语言的意义被消解。
四、审美意义:“人的自然化”的消解与融合
通过对河流意象的解读和《湘行散记》中对自然景致的语言描写鉴赏,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沈从文作品里提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的关系,二是把自然景物和景象作为欣赏、欢娱的对象。
在湘西世界中,地理的偏隅使得人们没有办法跟随时代的脚步,与自然的抗争仍然是日复一日的生存主题,但反而保留了质朴,人与人之间古朴的关系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悲哀与苦乐之中。
而对湘西隽秀景色的大量描写也是《湘行散记》的亮点之一,但是沈从文自己也坦言,无法尽兴描绘景色之幽深旷然,语言在自然中消解。
“我纵有笔有照相器,这里的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捉来让你望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
这里的“生存”“生命”则是沈从文散文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第三个层次,人的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而达到与天合一,或者说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在的现代语境下,沈从文试图重建人物精神与自然精神的深度契合,他笔下的人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自然的存在。但在自然中,体悟到景色的优美,人与自然的联结,消解了自我的社会意义,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与自然同在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