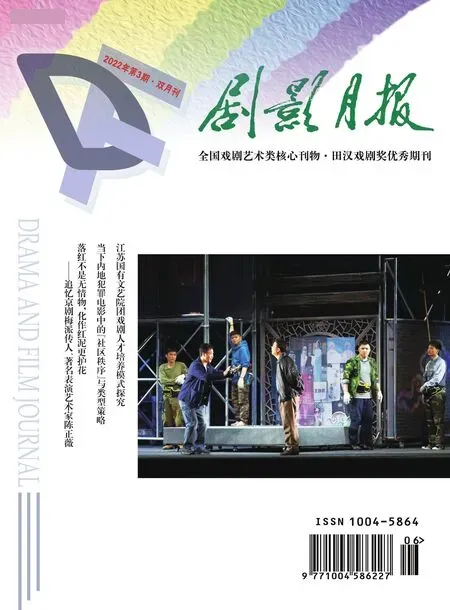漫谈启东洋钎书
■陈燕
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启东洋钎说书,它是以启东二字命名的。所以,启东人倍感荣幸。以前,他被广大的民众,称为“小镗锣”,后称“钹子书”“洋钎书”,解放后,被称为“启东说书”。他和“海门山歌”同根同源,都是从启海的方言来演绎的。之所以被称为“启东说书”,是因为他走了苏州说书的道路。山歌剧之所以后来被称为“剧”,是因为他走了舞台表演的道路。正如东北的二人转,演绎成了龙江剧。纵观江南的地方戏曲,其起源是:农民在农闲之时,外出唱山歌,以贴补家用。后来逐渐发展扩大,大部分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念宣卷,劝人为善,说因果,谈报应,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它以唱的形式来讲故事,教化大众。庵堂的尼姑,佛婆,本没有多少文化,也许识字也不多,靠口传心授,难免日后舛误颇多。但没有关系,基本的故事还在,就像涓涓细流,处于一种原始状态。启东的洋钎书,多以教化民众的宣卷为卷材,又以讲故事的方法,说一段故事、唱一段宣卷、再来一段社会新闻,在宽松的环境演出,譬如打谷场、破庙、田头,后来在茶馆。
启东洋钎书的源,还有一个可贵的创造性。就是他用启东的方言作为基础语言,聪明的艺人,还会运用其他方音,术语叫乡谈。如:县官老爷的太太,一定是扬州人;师爷一定是绍兴人;小皮匠一定是苏北人;鲁莽大汉一定是山东人;师生公子讲北京官话等。这就给这门艺术带来更多的创造空间,用语言的差别来演绎生动活泼的人物和情节,所以,他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他在表演的程式化方面和苏州说书、扬州评话等有些相似,有同样的语言基础,这样,他的活动范围就走出了破庙、田头、打谷场,在茶馆里站住了脚。启东说书艺人,大多能掌握口技,如刮风、下雨、马嘶、鸡鸣、马蹄声、虫鸣声等。
98年我调团部任职主抓业务,当时我父亲已经着手编写收集,“评弹北调”“洋钎书”只有三二个小段,从2000年开始收集、整理、挖掘,“洋钎书”在这过程感到困难重重。首先,走访几个老先生,发现他们记忆力严重衰弱,记不起唱段了。好几次我用录音机给他们录音,唱了几句,实在唱不下去,只好作罢。他说:兄弟啊,从1966年到1996年,整整三十年,我在家里都不敢唱一句,生怕被人听见了去报告我放毒,我是心有余悸啊。1979年后,虽然启东评弹团恢复,但年老不上台或很少上台。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乃是真知灼见。
启东洋钎书后继乏人,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哗众取宠。在那个时代,唱戏的是弱者,被称为“戏子”。因为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铁的,裁缝,被称为师傅。就连瞎子算命,也被称为“算命先生”,因何搞这个行当,就这么下贱?历史自有公论,后来,说书的被称为“说书先生”。地位似乎升了。其实不然,这只是民间的叫法,没有官方的委任状。是老百姓给了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小茶馆里,惊堂木一拍(术语叫醒木,区别于知县老爷的惊堂木)。茶客顿时鸦雀无声,倏然起敬,且听老生侃侃而谈。但是,也有麻烦。先生们对我说起他们父辈的经历。某书里有一个大麻子的坏蛋,他说得入木三分,听众会心大笑,老先生不明就里,煞是得意。第二天来了二个穿短打的,摇着黑扇子,说:滚蛋!再要看见你,打煞勿关!茶馆老板也不敢挽留。问其缘由,只因为得罪了当地乡绅,该人物是个大麻子。于是,老先生只好卷铺盖走路。以后学乖了,每到一地,先问有何忌讳,省得半途卷铺盖。
启东说书不死不活地苟延残喘了十多年,突然,在60年代后期,有了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当时王洪涤紧跟形势,编创一段“珍宝岛”不容侵犯,在灯光球场万人大会上一唱,轰动全场,当时启东县有线广播连续播了一个月,文工团才延续下来,直至70年代初期,王洪涤再次创编了“评话故事”《装御史上创奇迹》再次轰动,把剧种剧团保了下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走了过来。奇怪,原来启东说书的“说”和“书”却不见有人去关注。这也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平心而论,排一个表演唱形式的作品,十天半月也就可以了。要在舞台上说十分钟书,说、表、念、白、乡谈、口技、身段、卖口、关子、包袱等等,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成效。可见,专业和业余区别就在于此。
所以,由源而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不可抗拒的人为因素。一个训练有素的艺人,能救活一个剧种,一种强大的势力,也能摧毁一个艺术门类。所谓好事多磨,命运多舛,就是这个意思。老先生们也搞过改革,剧团恢复后招收演员,也搞了一些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之类的曲目,向评弹靠拢,但小小的钹子声,就是没有人继承,敌不过三弦琵琶来得悦耳,唱腔也是曲调陈旧无法拓展。以后偶尔在书场说一段,观众见了久违的“洋钎书”,十分来劲,再来一个!可惜,老先生们已是力不从心,后继乏力。就这样,启东“洋钎书”一时走到了死胡同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