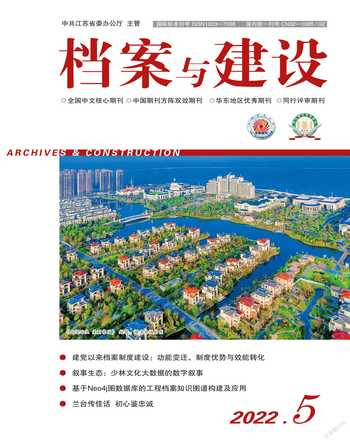“档案行动主义”:内容、实践与实质探析
苏立
摘 要:“档案行动主义”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孕育于社会和文化运动推动、后现代档案学兴起与媒介行动主义发展,主张档案职业需要推动问责和变革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文章认为,强化认同与维系情感、推动问责与揭示真相、谋求变革与伸张正义三方面是“档案行动主义”的主要实践表现;网络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对档案功能的重新认识、对档案职业的重新定位是“档案行动主义”诞生的实质。
关键词:档案行动主义;档案职业;社会正义;社群档案;身份认同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Practice and Essence of Archival Activism
Su Li
(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Archival activism originated in the 1970s and it was nurtur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he rise of postmodern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activism. Archival activism argues that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needs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and change in order to pursue social justice.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of archival activis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dentity and affec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ruth-revealing, and change for justi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are the essence of archival activism.
Keywords: Archival Activism; Archival Profession; Social Justice; Community Archives; Identity
受當代社会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行动主义话语逐渐走进国外档案领域,“档案行动主义”(Archival Activism)成为近年来国外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档案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档案行动主义”的相关话题,自2013年起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近年来国内围绕该话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1-4],但现有研究仅针对“档案行动主义”主要理念进行梳理或与某一具体视角相结合以对其表示赞同,缺少对“档案行动主义”发展脉络、相关实践和实质等的深层次探究,为此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与案例,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反思,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个观察档案实践的视角。
1 “档案行动主义”的内涵、提出背景及发展
1.1 “档案行动主义”的内涵解析
行动主义(Activism)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可指一战后一批表现主义者的文学批评话语和原则[5],也广泛指个人或集体为改变社会而采取的实际行动。[6]在社会治理中,行动主义关注的是多元主体于治理网络中共生共在的行动者系统的形塑。[7]“档案行动主义”从字面上理解即“档案”+“行动主义”。广义上看,“档案行动主义”就是用行动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现象、档案学理论并指导档案实践;具体来看,“档案行动主义”因其涉及到诸多行动主体并受不同的思想指引,难以达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也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讨论,如Andrew Flinn和Ben Alexander[8]认为“档案行动主义”的内涵有三方面:一是拒绝档案职业的被动与中立,主张档案职业的主动和参与;二是要求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以社会正义为目标并采取行动,收集和记录与政治、社会运动和活动团体有关的档案;三是认为“档案行动主义”的实践是社会运动活动的一部分。而Joy Novak[9]认为“档案行动主义”难以定义,需要在“档案行动主义”的6个核心概念中来考察其内涵:(1)社会权力;(2)中立性/档案透明度;(3)多样性/包容性;(4)社区参与;(5)问责制;(6)开放政府。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档案行动主义”发现和承认了档案、档案职业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主张拒绝“中立”的态度。其通过主动参与记录团体、社群或社会议题等相关档案的实践,以推动问责和变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由此,“档案行动主义”核心内涵可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档案和档案保存系统是被建构的非中立之物,故无法反映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开放给多方参与以体现多元与包容;其次,档案是认同、问责与推动变革的工具,追求社会正义是档案职业需恪守的信条;最后,倡导身体力行的行动,而非笔尖上的论争。
1.2 “档案行动主义”的提出背景
第一,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与文化运动的推动。二战后人权意识逐步觉醒,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新社会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些社会与文化运动给档案界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其促成了关于个体身份认同与族群自豪感的反思,档案学也积极回应,开始关注如女性、同性恋、少数族裔等一系列课题。[10]而在实践层面,各种社群建档实践的开展也声势浩大,那些一直以来为主流档案机构所忽视、被边缘化或被误述的群体发起了他们自己的档案项目,以此作为自我陈述、身份构建、权力赋予的重要手段。[11]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在民众的族群认同、民主观念和社会价值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档案作为证据、历史、记忆、遗产,是推动问责、还原真相、纠正不公、强化认同的重要工具,档案的这些特性也让人们的反思延伸至档案职业层面,反诘档案职业伦理,并要求作出回应。
第二,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后现代转向。Jacques Derrida在《档案狂热》中曾云“没有对档案的控制就没有政治权力”。[12]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档案学理论质疑和挑战现代档案学理论,并言明了档案和档案职业的权力属性,档案职业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在此时也屡遭质疑——档案工作者在按照程序对档案进行收集、编排与描述、保存、鉴定的过程中就不断在对档案施加着主观影响。Gerald Ham、Terry Cook等人倡导的档案后保管模式,则强调档案管理职能的拓展,主张档案工作者从“消极”走向“积极”,在塑造档案文献遗产中发挥主体地位和扮演积极角色,摆脱档案实体管理的窠臼并与广袤的社会网络相联结。
第三,媒介行动主义的发展。媒介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指“那些引导集体行为以批判主导媒体和(或)建立资讯生产替代机制(Dispositifs Alternatifs)的社會进步运动”[13],也指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手段来促进社会变革的行动主义。20世纪80年代,媒介行动主义从批判西方大众媒体文化霸权转向保卫本社团的权利、语言、文化等层面,同时,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地改变着信息的生产机制,大量社团涌入计算机通讯网络,互联网平台成为这些社团传递信息的首要阵地。“档案行动主义”意图将特定档案收集起来,建立一个有别于官方档案机构的档案库并加以保管和利用,以保存社群记忆并表达自我主张,而当前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也为其开辟了新的空间,不仅大大降低了档案保存和传播的成本,也极大地增强了其参与性。综上,当前“档案行动主义”实践案例,多数都将网络平台作为其信息传递和动员的重要媒介。
1.3 “档案行动主义”的发展脉络
国外档案学界通常将“档案行动主义”的发轫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彼时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各种民权运动与文化思潮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有力的影响,在档案行业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也在此时开始浮现。1970年,历史学家Howard Zinn于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上主张档案工作者要反思“中立”的概念,并敦促档案工作者成为“行动主义者”(Activist),投身于有社会意义的工作。Zinn认为“档案工作者甚至比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更倾向于谨慎地保持中立……但这种中立是一种虚构”[14],这被视为是“档案行动主义”思潮的肇始。
Zinn的讲话在北美档案界掀起了热议的浪潮,由此引发的思想和实践上的变革也影响到了档案学和档案实践的发展。1971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会议上成立了“档案促进变革委员会”(Archives for Change Committee),由此开始着手进行行业内部的改革。同年,一些自称“行动主义者”的档案工作者组成了“档案工作者行动小组”(Archivist for Action)以响应Zinn的呼吁,冀望创造一个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平衡的历史记录。[15]曾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Ham也对Zinn的批判表示赞同,认为档案界缺少对传统档案之外的关注,呼吁要使档案典藏能反映人类社会之“边缘”。[16]20世纪70年代正值公共史学在美国兴起,公共史学将对历史的研究深入到族群、性别与家族等层面,并主张历史学者运用其专长来推动公共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广泛的公共利益与有限的档案资源成为档案实践中的一对矛盾,关注更广泛的社会性的档案也成为档案学和档案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美国档案界的思想碰撞与现实困境也在西方其他国家得到了回应,如加拿大提出的“总体档案”就主张档案馆应收藏所有类型的档案,从而反映出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20世纪90年代以降,后现代档案学者从更深的层次剖析了档案本体。Joan Schwartz和Terry Cook就直言档案具有特权化和边缘化的力量[17],并主张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权力应开放给质疑和问责。这一时期将维护社会正义作为档案职业伦理之追求备受推许,成为国外档案学界热议的焦点。Verne Harris是“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极力推崇档案工作者应当以追求正义作为档案事业之发展目标。Randall Jimerson也指出,“档案工作者可以利用档案的力量来促进问责、开放政府,推动多样性和社会正义”。[18]
至此可以看出,“档案行动主义”在前期强调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收集、管理和鉴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主动参与档案文献遗产塑造中充分尊重和维护档案的多样性。有学者就指出史学和档案领域的“行动主义者”有两种含义:一是有意识地选择,使其收集范围多样化的人;二是试图实现社会变革的人。[19]而在后期“档案行动主义”显然更加呼吁后者的出场,提倡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促进社会变革、推动问责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
2 “档案行动主义”的相关实践
当前“档案行动主义”相关实践多以社群为纽带,以社群档案项目为依托,希望通过收集、存储和传播与自身相关的档案来达成其目标。根据其动机和目标,“档案行动主义”实践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2.1 为强化认同与维系情感的实践
“档案行动主义”主张通过档案来维系社群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正视社群历史,凝聚社群力量。“档案行动主义”通过大量的社群档案实践以强化身份认同、传递社群情感、保存社群记忆、促进包容理解。[20]譬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有多个由社群成员创建的少数群体社群档案馆,其不仅是保存记录的重要地点,也对研究、收集和学习社群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1]社群档案记录了社群的行为和身份,构建了群体的身份认同。[22]
2.2 为推动问责与揭示真相的实践
“档案行动主义”主张通过运用档案来问责、纠正或赔偿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典型案例就是利用档案促成对日裔美国人的赔偿。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拘禁了12万多名日裔美国人,将他们视为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战后,历史学家和行动主义者利用拘留期间形成的档案证明拘留是非必要的,成功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为被拘禁者争取到了赔偿。[23]原本用来控制日裔美国人的档案成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不公的证据,让惨遭囚禁的日裔美籍公民不再是沉默的受害者。
2.3 为谋求变革与伸张正义的实践
“档案行动主义”主张通过积极参与、主动记录来推动社会变革,呼唤公平正义。例如Rosa Sadler等[24]研究了英国谢菲尔德女性主义档案项目,指出女性主义者们将这些积极参与建档和收集社群记忆的活动视为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希望这些档案能够帮助改变公众对妇女、妇女权利和性别关系的看法。除公共议题外,“档案行动主义”也主张档案工作中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如Sue McKemmish等[25]和Rose Barrowcliffe[26]在考察了澳大利亚的档案工作实践后都观察到,澳大利亚的档案工作实践深受殖民化及其遗留问题影响,虽然在实践中开始关注到弱势群体与公平正义,但其做法仍然严重偏向殖民者的视角,亟须对档案工作进行去殖民化改造以弥合“叙事鸿沟”。
“档案行动主义”有诸多表现形式,以上的归纳方式实际上也未能完全穷尽其所有的实践形式。Vladan Vukli 与Anne Gilliland[27]曾提出“档案行动主义”的四种形式:(1)社群档案(馆);(2)在政府资助的档案馆和其他“主流”档案馆内,通过提升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能力,开展有社会责任感的(Socially Conscious)工作;(3)基于研究的行动主义;(4)体制外的档案工作者进行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作。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复杂得多。具体的实践动机呈现出较大的复合性,且动机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实践形式呈现出多样性,既有基于网络的数字档案馆,又有实体的档案存储空间;实践方式呈现出合作性,非官方的社群档案和官方档案馆进行合作也不是个例。此外,一些实践中的新思想也推动着传统档案管理思维的变革,如档案“共同形成者”(Co-creator)、“档案自治”(Archival Autonomy)、“参与式档案馆”(Participatory Archives)、“档案多元观”(Archival Multiverse)等,也可纳入“档案行动主义”的体系之下,这些思想也进一步丰富了“档案行动主义”的实践。
3 “档案行动主义”的实质探析
“档案行动主义”孕育于社会变迁和学科范式转换的背景下,背后有更为具体的推动逻辑,其实质可从信息权力、认同建构以及档案功能、档案职业的角度来考察。
3.1 网络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
传统社会权力结构表现出对信息的控制。而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社会成员皆拥有了信息生产和传递的能力,信息存储也从集中走向分布,与此同时档案的来源、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愈发广泛和多样。Cook曾指出,利用网络,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档案工作者。[28]这体现出网络社会中信息权力的下移。信息权力的下移促使当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结构性的变迁,在传统权力结构中嵌入了新的信息权力,权力的运行表现出自下而上的路径。
信息权力通过人们的认同展现出强大的力量。Castells认为认同的构建总是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并提出了认同的三种形式: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29]合法性认同是有社会制度引导或规制的认同;抗拒性认同是处于社会底層的社会成员为抵抗社会主流意识而产生的认同;规划性认同则是社会成员重新确认自己的地位、伸张自己要求、构建某种制度并寻求社会转型的认同。纵观社群运动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些社群运动正在从抗拒性认同走向规划性认同,而各种行动主义的社群建档活动,正是从抗拒性认同走向规划性认同的手段之一。在“档案行动主义”的倡导下,档案工作者、社群成员或公民广泛收集和存储档案资源,这些档案资源的社会价值、情感认同价值有着强大的能量。而信息权力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或心灵的权力,通过符码影像的直接呈现,建构社会成员的观念和意识并影响其行动。种类繁多的社群档案实践,也是为了将信息权力牢牢地攥在社群自身手中,维护自己的叙事权。
3.2 档案功能的重新认识
“档案行动主义”的思潮与实践,从档案本身来看是源于对档案功能认识的改变。自20世纪中后期起,档案文化功能、记忆功能逐渐被人们重视,档案被视为是判断一个国家文化底蕴丰厚与否的重要资源,同时也认识到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以及身份认同中的独特价值。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加强,加之网络空间中虚拟社群的涌现,社群建档运动的兴起和壮大,档案在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备受重视,社群希冀运用档案留存社群记忆、构建身份认同,以增强社群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运用档案可以纠正或问责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认识到了档案在推进社会正义中的独特贡献,档案被用作是记录以往的斗争与问责过去的罪行的证据,被看作是支持伸张社会正义和疗愈社群创伤的资源,亦被视为是理解过去、审视当下、塑造未来的工具。如此看来,这是档案政治价值的“重新发现”,只不过此时是作为社群成员“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的工具。
3.3 档案职业的重新定位
长久以来,档案工作者被视为是消极被动的档案保管者,而“档案行动主义”倡导呼吁档案职业走出故纸堆。档案职业曾长期依附于历史学科,Ham在20世纪就疾呼道,若不改变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的现状,档案工作者只不过是随编史兴趣变化而改变的“风向标”。[30]后现代档案学者更是激烈批判档案职业是在规则之下被裹挟的“傀儡”,是不光彩的“帮凶”。种种批评激荡起对档案职业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档案工作者果真是“帮凶”?还是历史的守护者与正义的捍卫者?“档案行动主义”给出的回答是:摒弃在原有档案实践中所持有的“精英主义”观念,关注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人群,积极参与到各类文献的收集与保管中,转型为积极的中介人和社会活动家,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Cook等档案学者曾多次号召档案工作者应成为“积极的档案工作者”,从被动的档案保管者转为主动的知识服务提供者。但“档案行动主义”显然更进一步,主张档案工作者超越“积极的档案工作者”成为行动主义者,将档案工作视为是社会、文化和政治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综合上文对“档案行动主义”相关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档案行动主义”所倡导的实则是实质正义观视角下对档案职业伦理的呼唤,易言之,“档案行动主义”主张档案工作必须要与人类道德观念、价值诉求中的正义追求相呼应,并将推进公平与社会正义视为是档案职业伦理之愿景。
4 结 语
“档案行动主义”要求档案工作反对中立、积极行动的初衷固然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这一崇高目标,但这也并非毫无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若档案职业“一旦丧失了中立立场,档案工作者就要在并不明确的正义呼唤中艰难挣扎,这将让他们的工作陷入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困惑状态”。[31]Mark Greene直言不讳地批评档案工作需反对中立的观点,认为追求社会正义尽管听起来高尚,但有可能对档案职业造成多重损害,并担心这会削弱档案职业的道德地位和权威。[32]档案工作作为一个与社会事务紧密结合的职业,自当融入社会事务的各个环节,其实践性必然要求不断反思职业伦理与社会的联系,然而社会正义的取向具有动态性,一味反对职业中立很可能酿成立场先行、纷乱繁芜之局面。
现阶段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档案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相较于制度主义治理,行动主义治理的多主体参与、积极行动及强烈的现实关照等思想内核,其对当前机构改革背景下档案职业积极走进社会,充分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如近年来开展的精准扶贫档案工作正是对档案职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呼应,也是我国档案职业立足国情的积极行动。“档案行动主义”作为舶来品有其特有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实践土壤,如何批判借鉴,书写立足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是未来需探索的方向。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潘未梅,曲春梅,连志英.国际档案学界十大热点研究领域——基于六种国际档案学期刊论文的分析(2017—2020)[J].档案学研究,2020(6):128-138.
[2]于英香,张雅颉.“档案参与”科学数据监管:缘起、现状与动因[J].档案学研究,2021(2):104-110.
[3]张珊.新时代中外档案合作交流研究——实践探索、理论基础与新模式构建[J].浙江档案,2019(12):26-28.
[4]聂勇浩,黄妍.“积极参与”的档案学:档案行动主义探析[J].档案与建设,2021(12):12-16.
[5]张黎.表现主义的社会批判倾向[J].外国文学评论,2002(4):128-134.
[6]钟声扬,徐迪.行动主义3.0还是懒汉行动主义:关于网络行动主义的文献评述[J].情报杂志,2016(9):55-61+23.
[7]柳亦博,玛尔哈巴·肖开提.论行动主义治理——一种新的集体行动进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8(1):81-91.
[8]Flinn A,ALEXANDER B. “Humanizing an inevitability political craft”: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archiving activism and activist archiving[J]. Archival Science,2015(15):329-335.
[9][15]Novak J R. Examining activism in practice:A qualitative study of archival activism[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3:2+27.
[10]李娜.檔案为人人:美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J].史学理论研究,2016(3):53-63+159.
[11]连志英.欧美国家社区档案发展评述与启示[J].浙江档案,2014(9):6-9.
[12]Derrida J. Mal d’Archive :Une impression freudienne[M]. Paris:Galilée,1995:15.
[13]多米尼克·卡尔顿,法比安·格朗荣.媒介行动主义者[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
[14]Zinn H. Secrecy,Archives,and the Public Interest[J]. The Midwestern Archivist,1977(2):14-26.
[16][30]Ham F G. The Archival Edg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1975(1):5-13.
[17]Schwartz J M,Cook T. 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2002(2):1-19.
[18]Jimerson R. Archives for All: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2007(2):252-281.
[19]Yaco S,Hardy B.B. Historians,archivists,and social activism:benefits and costs[J]. Archival Science,2013(13):253-272.
[20]Flinn A. Community Histories,Community Archives: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07(2):151-176.
[21]Wakimoto D K,Bruce C,Partridge H. Archivist as activist:Lessons from three queer community archives in California[J]. Archival Science,2013(13):293–316.
[22]Platt V L. Restor(y)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the archive of Ken Saro-Wiwa[J]. Archives and Records,2018(2):139-157.
[23]Hastings E. “No longer a silent victim of history”:Repurposing the documents of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J]. Archival Science,2011(11):25-46.
[24]Sadler R,Cox A M.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archive:documenting women’s activism a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Sheffield Feminist Archive[J]. Archives and Records,2018(2):158-173.
[25]Mckemmish S,Bone J,Evans J, etc. Decolonizing recordkeeping and archival praxis in childhood out-of-home Care and indigenous archival collections[J]. Archival Science,2020,(20):21-49.
[26]Barrowcliffe R. Closing the narrative gap:social media as a tool to reconcile institutional archival narratives with Indigenous counter-narratives[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2021(3):1-16.
[27]Vukli V,Gilliland A J. Archival Activism:Emerging Forms,Local Applications[C]//FILEJ B. Archives in the Service of People-People in the Service of Archives. Maribor:Alma Mater Europea,2016:14-25.
[28]Cook T. 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J]. Archival Science,2013(13):95-120.
[29]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
[31]陆阳.档案伦理与社会正义关系研究的深层解读——基于实质正义观与程序正义观的冲突[J].档案學通讯,2020(6):22-30.
[32]Greene M A. A Critique of Social Justice as an Archival Imperative:What Is It We’re Doing That’s All That Important?[J]. The American Archivist,2013(2): 30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