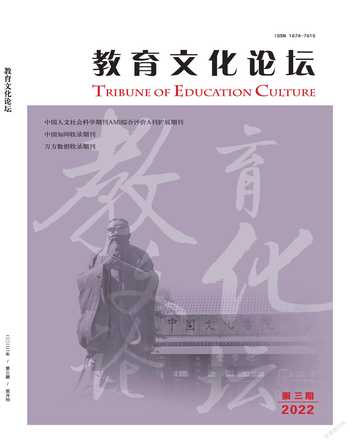《苗族史诗》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周杰 杨敏
摘要: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领衔翻译的《苗族史诗》充分体现出阐释学所提出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该书不仅是苗族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经典文献,也为日渐成为国际显学的苗族古歌学搭建了译作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文以阐释学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为框架,探析《苗族史诗》英译本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文化阐释等方面的具体体现,以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苗族史诗》;阐释学;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3-0044-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3-008
“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是苗族的口传经典,叙述了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万物生成、洪水滔天和族群迁徙的神话故事,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和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1]314,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苗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早在1952年就已开始,著名苗族古歌研究专家马学良、今旦、田兵等先后整理出版了《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完成了苗族史诗这部苗语口传文化经典的汉语书面转换。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译是培育文化竞争力、展现中国形象、宣传中华民族价值观和扩大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手段[2]。2006年,“苗族古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苗族古歌”的外译也得以实现。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将马学良、今旦于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进行了英译,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译名为Butterfly Mother: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3]。2012年,马克·本德尔又与吴一方、葛融合作,翻译了吴一文、今旦以汉语译注的《苗族史诗》,后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4]。该书被认为是“苗族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经典文献……为逐渐成为国际显学的苗族古歌学搭建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①。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苗族古歌以及苗族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使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传播。本文拟以阐释学的翻译“四步骤”为理论框架,探讨《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中的译者主体性,以及译者在阐释古歌中呈现的民族内涵时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等,以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应用。吴一方以苗族古歌翻译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为案例,从文化背景、诗歌韵律、文化事象等视角探讨了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5];王治国从民族志视角分析了该译本在翻译民俗事象时使用的深度翻译、置换补偿等策略[6];朱晓烽基于民俗学的表演理论,从语境重构的视角解读了《苗族史诗》英译本的副文本翻译[7]。上述研究为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多维度的翻译策略参考。
二是翻译模式与译者素养。刘雪芹梳理分析了《苗族古歌(苗汉英对照)》的英译概况和翻译模式,特别论述了通晓苗、汉、英三语的合作译者吴一方在该译本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译者素养和团队合作在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8]53-82。吴一文、刘雪芹详细分析了该译本在苗—汉、汉—英以及苗—英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阐述了合作翻译模式的成功之处[9]。吴一文表示,本德尔翻译过旧版《苗族史诗》,对苗族文化有深入研究,是最理想的外方译者人选;但在将苗文译为汉语再转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语言和文化的过滤,所以,通晓苗、汉、英三语的吴一方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准确性的把握也非常重要[9]。刘雪芹认为,在翻译团队中,若“至少有一人精通口传文学源语,一人精通目标语,在转述时至少有一人精通中介语言,那这个团队亦可担起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翻译的重担”[8]72-82。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过程中,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质量,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翻译模式和译者素养方面,但鲜有学者关注该译本的翻译主体,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典籍英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不可或缺。
二、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四步骤”与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译自英文“Hermeneutics”,也可译为“诠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及其方法论的学科。阐释学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哲学思潮。从古希腊的古典阐释学到近现代以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乔治·斯坦纳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颠覆了人们对“文本至上”的认识,并在较早时期就开始讨论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1813年,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二元翻译论”(即读者接近作者或作者走向读者),认为只有发挥译者主体性,才能使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理解成立[10]141-166。译者在翻译时要把握文本和作者的思想,而这个依靠译者的主观选择来重建客观文本的过程,就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必须到场。翻译和阐释学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语言是理解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理解的途径就是解释;而翻译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斡旋,是最能体现阐释学观点与方法论的学科和手段。海德格尔把“解释”和翻译等同起来,认为每一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是翻译[11]181。阐释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概念,认为译者翻译原文,实质上就是理解原文之后的再創作。他将翻译的过程视为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划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12]287。简言之,“信任”指译者认为需要翻译的作品是有意义的,有翻译价值的;“侵入”表示译者打破源语的外壳直达内里,将核心意义抽离本体并尝试将其融入译文;而“吸收”则表示将“抽离”的内容经过同化、安置并最终接纳的吸收过程。译者的翻译在前三个步骤中会经历两次失衡:一是在译者和原文建立“信任”后,二是在“侵入和吸收”后。从而,第四步的“补偿”就是指为恢复原、译作之间的平衡而进行的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处理。
不难看出,斯坦纳强调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在阐释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阐释学翻译思想突出译者的个人体验、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对原文的浸润,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再创造。”[11]170首先,译者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上选择想要翻译的目标文本,这让译者需同时具备“原文读者”和“译文阐释者”的敏感度。“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情感和想象力等文学能力来解读源语文本中的留白,阐释的多元化就在不同译者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中产生;身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13]在翻译中,译者需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全面把握原文的语言、思想、审美和文化,并在译作中合理诠释,展现原文内涵和语体美感。最后,译者应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平衡。译者每一次的解读和阐释,往往使得译文和原文之间出现矛盾、冲突甚至产生变形,为此,译者需要通过进一步调整文字、风格等作出相应补偿来平衡两者,以使译本能够更好地展现原文,或使原文升值,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沟通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表现出来[13]。译者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13]。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在对原著的理解分析、语言转换以及译文创作的活动中,能动性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举足轻重的,因为翻译也是一种阐释。“当把注意力放在翻译的主体——译者身上时,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翻译结果,而是整个翻译过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翻译主体及其能动性对翻译活动的决定性作用。”[14]
翻译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转换的成果——译作则展现了译者对源语的理解和阐释。现代阐释学首先对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探讨,指出了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也为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这个议题引来了更多关注。从译者、原文和读者三方互动的角度出发,译者解读原文形成译作,而读者通过阅读译作去了解原文。译者在翻译时必然要经历阐释这个阶段,从而将译者、原文和读者联结成一个闭环。因此,可以说,正是阐释让翻译的目的得以实现。从阐释学派的诠释来看,译者的经历背景和阅读环境等皆会影响其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进而对其翻译活动产生一定影响,这恰好体现了阐释学强调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三、阐释学视角下《苗族史诗》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探析
《苗族史诗》和其他的长篇叙事诗一样,在搜集、转录、编辑、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都经过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过滤”[15]。从译者和翻译过程的角度出发,本德尔提出了“Processing”(加工、处理)这个概念[15],认为口头文学正如天然的食材或纺织原料需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产品,译者在翻译处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也是《苗族史诗》文本化传播的固有特点。乔治·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四步骤中,每一步都解释了译者的主体性,都有译者主观因素的参与[16]144。本文从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维度探析《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中的译者主体性。
1.信任:译者对原著作者及源语文本的态度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需要对翻译材料进行主体性判断和忖量。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肯定是翻译的前提,只有在译者认为原文是严肃的、言之有物的、具有翻译价值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自我专业背景和经验认知来阐释原文。
苗族史诗整理与研究项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苗族口头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以书面化的形式完整地保留下来,借此弘扬苗族文化[14]。《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领衔英译者马克·本德尔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文学博士,其主要研究兴趣和方向是中国传统表演及相关文学,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本德尔还讲授东亚文化和东亚传统表演课程,并多次组织主题涉及少数民族史诗、中国说唱文学、口头和书面民族诗歌的研讨会。本德尔到广西大学任教后,逐渐开始了解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对翻译文本的挑选也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17]。不管是出于专业需求还是兴趣使然,像苗族史诗这样兼具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风俗、歌舞等价值的口头文化经典,本身就对本德尔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意识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也在不断席卷与影响着苗族文化,在思考如何对这一少数民族“活的历史”进行保护和传扬的问题时,本德尔将目光转向了苗族史诗的翻译和研究[18]。
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民族文化的外国学者,本德尔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译介方面建树颇丰,对中国民族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贡献良多。今旦、马学良的《苗族史诗》出版后不久,本德尔就主动联系编者希望将其英译[9]。1985年,本德尔在贵州省贵阳市和《苗族史诗》编者之一的今旦见面,并走访了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了解了诸多包括古歌传统表演方式、苗族神话、礼仪、纺织、银饰制作等苗族文化知识[4]。在这一过程中,苗族史诗在本德尔的心目中分量渐增。2006年,美国哈克特出版公司(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了本德尔翻译的名为《蝴蝶妈妈——来自贵州苗族的创世史诗》(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China)一书。从出版译著这一视角来看,这是本德尔第一次和苗族史诗建立信任关系。他根据苗族史诗的特殊文化价值和地位,结合自身專业、兴趣,搭建起了和苗族史诗“信赖”的桥梁。因而,当2008年今旦和吴一文为最新修订版的《苗族史诗》寻求与本德尔的英译合作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4],促成了第二次“信任”的建立。本德尔表示,由于苗族古歌歌手日渐减少,苗族的这一口头传统和其传承人即将离开曾经的舞台,《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也将变成当下这一时代的丰厚遗产[18]。在源语文本的选择上,本德尔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与原作以及原作者之间建立信任的过程,是其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2.侵入: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过滤性阐释
当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遇到语言障碍时,之前建立的信任便逐步瓦解,此时翻译进入第二步“侵入”。它指的是译者的认知和思考会不可避免地侵入原文[12]282,剖析并重新审视原文的一系列过程。这一过程进一步体现了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和碰撞。在此过程中,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主观理解、文化知识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都会不由自主地“渗透”到源文本中。这一阶段对原文的剖析和重新演绎也是对阐释学派“翻译即理解”的力证。翻译不是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单纯的逐字翻译,而是译者根据自身的认知经验对源语文本进行“过滤性阐释”。在“侵入”的过程中,译者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对原作进行归化或异化处理。本德尔对中国文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带着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学素养去“侵入”原文本,在苗族史诗的英译中对原文进行增补删减,以便使译文更贴近读者,从而消减译本与译入语文化间的隔阂。以下几例即可为证:
例1
原文:穿着花鞋来踩鼓,
花鞋舞动轻轻摆。
译文:Wearing embroidered shoes they’d drum dance,
With the embroidered shoes dancing lightly.
此例中对“花鞋”一词的处理值得关注。如果不考虑文化背景,一般来说“花鞋”可以直接译作“flower shoes”,指鞋面上有花朵图案的鞋子。但在苗族史诗中,“花鞋”并不是简单指有“花”的鞋,而是采用苗族刺繡工艺,绣有花卉、禽鸟等苗族经典图案的鞋。苗族刺绣是苗族源远流长的手工艺术,是苗族服饰主要的装饰手段。刺绣及其图案色彩鲜艳,构图明朗,朴实大方,具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几乎每一个刺绣图案或纹样都有一个来历或传说,是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是苗族历史与生活的展示。蝴蝶、龙、飞鸟、鱼、圆点花、浮萍花等图案都是《苗族史诗》传唱的内容。一般来说,苗族刺绣多译作Miao Embroidery。本德尔曾深入苗家,对上述背景文化知识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并未简单将“花鞋”直译为“flower shoes”,而是对其进行了“过滤性阐释”,将其译作“embroidered shoes”,直截了当呈现苗族刺绣的本质。
另外,在“打杀蜈蚣”一节中有“雷公穿的花花衣”一句唱词,讲述的是雷公身披彩霞去处理天下纠纷的情景。文中已说明雷公是执掌人间公正的神,而神仙在中国神话故事中总是以“脚踏七彩祥云”的形象出现,译者将此处的“花花衣”也处理为“embroidered clothing”,并在注释中说明花花衣指“rosy clouds”。这一处理既着重体现了苗族独有的刺绣特征,又兼顾了读者的普遍理解。译作的生命是译者赋予的,“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它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决定如何使它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19]可见,译者主体性决定了译作的独立审美品格和译入语文化特征。
例2
原文:鸡讲儿郎万百千,千把姑娘同游方,
村西树下好谈情,柳荫侧畔诉衷肠,
译文:Dlib Jangl had countless boys,
And countless girls to play courting games,
Meeting beneath trees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village,
Revealing their feelings beside the shady willows,
“游方”是苗语音译,旧称“摇马郎”,指的是黔东南苗族青年男女的谈情择偶活动,多在节日和农闲时进行[20]1102。“游方”至今仍是贵州省黔东南、黔南地区苗族青年男女公开相亲、社交和交友的活动方式。为了便于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每一个苗族村寨都有一处谈情说爱的地方,这种地方在当地叫“游方坡”或“游方坪”。每每节日一到,女孩子们穿着母亲做的花衣,带着父亲买的银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游方。“游方”文化蕴含着深厚的苗族文化内涵,表现出苗家人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反映了苗家人的民族文化价值。可以说,游方”是苗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意象,内涵丰富,译者如何处理可以看出他对文化传译的立场和态度。“游方”一词在《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中首次出现时,本德尔已在译文中加注,说明这是一种在未婚青年之间进行的社交活动,包括唱歌、跳舞、谈情等环节。但这一解释实际上进行了过滤性阐释,未能充分体现“苗族有自己的婚姻圈,‘游方’是受婚姻圈控制的”[21]这一内涵。此处,本德尔没有选择“游方”在2006年版《苗族史诗》英译本中的音译加注,而是采用归化的手法,将“游方”译为court。《牛津词典》列举了court做动词时的两条解释:(1)if a man courts a woman, he spends time with her and tries to make her lover him, so that they can get married,即求偶求爱、求婚之意;(2)to have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before getting married,即恋爱之意。可以说,达到了原作和译作上的功能对等。
文化类翻译的再次创作是译者凭借自身文学素养去领悟和诠释原作的过程,极具主观性。但由于译者身份的特殊性,在翻译过程中即使选择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其译文也会或多或少地带着个人风格和特质,因此,要想完全抹掉译者的翻译痕迹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意味着译者对原作的忠实是相对的。另外,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时,还“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感受进行再创作,使其成为译语文学的一部分,为译语读者所普遍接受,使自己的再创作扩张为社会活动,与时代、社会等产生共鸣”[22]。
3.吸收:译者对源语与目标语语言及文化的融合
“侵入”原文后,便进入到“吸收”以将源语信息输入译语的阶段。吸收,即通过“移植”的方法,将原文中的形式、含义等传送到译入语中。这样既能摆脱原文的阻碍,又能补充译文中的盲点。“吸收”的整个过程也是译者在寻求最恰当的译入语表达方式来展现原文本内容的过程。斯坦纳坚信,“没有一种文化集合能够在没有被改造的风险下进行传播”[12]283。因此,在处理“输入性”信息时,译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按照翻译目标和策略进行选择性吸收,以保持译入语语义场的“稳定”。这也是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打破冲突和矛盾的过程,更是实现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过程。本德尔也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比较困难的是苗族史诗中的隐喻和重复的处理,以及如何在符合英文的语法和词序等规范下重现简洁的苗、汉文本,实现跨文化的对等和可译[18]。对于“吸收”阶段,斯坦纳认为,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语言同化类型,有的语言完全归化且被文化历史视作进入本土文化的核心,但有的始终处于异化和边缘化的位置[12]283。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文化和语言背景优势,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原文的内涵、意蕴能够表达得更加准确和生动。
例1
原文:来看造月亮的事,造太阳挂在云天,倒在塘里死绿藻,倒在坡上死树木……
来看造太阳的事,造月亮挂在天上,倒在塘里死青苔,倒在山坡死茅草。
译文:Come and see the creation of the moons,
Creating the suns to hang in cloudy heaven.
If smelting waste was dumped into ponds, all the algae would die;
If smelting waste was put onto hills, all the trees would burn.
……
Come and see the creation of the suns,
Creating the moons to hang in heaven.
If smelting waste was dumped into ponds, all the moss would die;
If smelting waste was put onto hills, all the grasses would burn.
此例選自“铸日造月”一节,述说神人们将金银运到西方后铸造日月的情景。在原文中,两行歌词中的前一、二句讲述铸造日月,第三、四句讲述铸造日月后对废料的处理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译者在“侵入”理解源语文本、“吸收”源语文本隐含的背景知识后,融合源语及目标语文化,在译文中增加了原文中隐含的内容smelting waste,即倒在塘里或山坡上的是铸造日月熔化的废料。smelting一词很好地照应了苗族“融金银,造日月”的这个主题。同时,译者将后两句处理成条件状语从句,不仅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同时也和后文中神人进入山岩深洼、石槽岩旮旯去铸造日月形成逻辑关系,使得译文表达得更清晰,忠实再现了原作含义。
例2
原文:枫木已经栽完了,枫树天天往上长,
树梢直入青云里,扫拨天边一阵阵,
千山万岭可遮阴,千沟万谷能乘凉。
译文:The sweet gum trees were all planted,
And they grew taller every day,
Their branch tips reached straight to the clouds,
Their branches like big brooms sweeping in the edge of the sky,
Thus, the myriad mountains could enjoy the shade,
And the myriad valleys could relax in the coolness.
此例选择“播种植枫”一节,叙述神人香两播种、育枫的过程,反映出苗族的营林知识。《苗族古歌》中唱道:“我们来看妹榜生,妹榜出生在远古。妹榜出生在哪里?妹榜出生枫树心……妹榜长大要谈情,她与水泡沫谈情,谈情谈了十二夜,妹榜生下十二蛋。”[23]192-195这一段解释了为何枫木在苗族人心中为万物之始,因此,如何处理枫木片段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对枫木之于苗族文化的分量的思考。汉语多无主句,例2原文第三句主语实则和第二句一致,为照顾译入语读者习惯,译者在第三句的翻译中添加了主语Their branches,帮助读者理解。其次,原文多重复,增译主语可与原文修辞手法形成照应。再者,第四句将“扫拨”名词化,在译文中以big brooms和sweeping呈现,既让读者感受到枫木映天蔽日的磅礴连绵之势,又为下文第五、六句提供了逻辑前提,体现出译者在文意和结构上的考量。最后,译者将“千山万岭”译为the myriad mountains,将“千沟万谷”译作the myriad valleys,虽无法复制原文的诗语形式,但译文也尽可能在达意的前提下做到文内对仗。译者在充分吸收原文原意的前提下发挥其主体性,使译文以更加贴合英语读者语言与文化习惯的方式呈现。
4.补偿:译者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找平衡
斯坦纳把“补偿”看作是译者道德的一种表现,在译者对原文进行“侵入”和“吸收”的理解再创作之后,源语、译语的两种视界必然会丧失原本的平衡,因此,第四步的“补偿”不可或缺。补偿还有另一层意思,即翻译是增强原文文本力量、影响的行为,通过翻译可以让原作增值[24]220。在此过程中,译者会针对前三个步骤中因语言、文化等差别而出现缺失或偏差的部分,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再次进行改动、补偿。注释性翻译能够弥补直译和音译的缺陷,常用于诠释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如地名、人名、事件、谚语、历史典故等。本德尔在翻译时多处采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并通过添加解释或注释给予补偿,以达到传达原意的目的,避免读者出现理解偏差。现举两例具体说明:
例1
原文:将它存放在何处,
把它放在神庙里,
官府衙门里边存,
苗人汉人得纪念。
译文:Where were they put?
They were put in temples,
And put in the local yamen,
For Hmong and Han people to remember.
Note: Yamen, in imperial times, was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官府舊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衙门是旧时官员办公的机关,两者同指“机关”这个意思,译者舍其一,只留下“衙门”(yamen)。“衙门”一词富含中国古代文化意蕴,且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对等表达,于是译者选择用音译加注的方式将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对对应的译入语文化空白加以说明以完成“补偿”这一翻译步骤。这样不仅便于目标读者阅读,还能呈现源语文化底蕴;既考虑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补足了文化空白以避免造成阅读障碍,保证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是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的体现。此外,在“溯河西迁”一节中,译者对“乌纱”一词也采取了加注的翻译方法。“乌纱”指中国古代官员戴的乌纱帽,泛指官职,因在苗、汉文化中都有这个意象,汉译只需直译即可。但西方文化中并无相关对等表达,因此,译者在语义翻译的基础上,加上注释“The black cap, wu shamao in Han, indicates an official post”,既体现了“乌纱”的汉语发音,又将原作中的意象植入译文中予以保留。
例2
原文:谁来当金银舅父,舅母要吃外甥钱,
……
谁来当金银舅母,舅父要吃外甥钱.
译文:Who would be gold and silver’s maternal uncle?
His wife would receive the dowries from her nephews
…
Who would be gold and silver’s maternal aunt?
Her husband would receive the dowries form his nephews.
对苗族人而言,舅权广泛存在于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舅权来自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平衡机制,抑或是这种机制的遗留。”[25]173母亲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为了与父权抗争,移权给自己的男性血亲,也就是娘家兄弟,舅舅因此在苗族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身份。《贵州通志》载:“清江苗婚嫁,姑之女定为舅媳,倘舅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否则终生不得嫁。或招少年往来,谓之阿妹居。”[25]122其中所述姑舅表优先婚和外甥钱都集结于“舅权”这个中心,体现了血亲上归还舅家的婚俗。因此,外甥钱实则是外甥女未嫁母舅之子从而给舅舅的一种补偿。译者将外甥钱译为“the dowries from her/his nephews”,并通过加注“In accord with old custom, if a girl was to marry, the son of the bride’s maternal uncle was first choice as a marriage partner. If this did not work out and another groom was selected, his family had to provide money to the bride’s maternal uncle”来说明当姑妈家女儿要出嫁时,舅舅儿子具有成为其丈夫的优先权,以及外甥钱是外嫁后需要弥补给舅家的钱财这一苗族特有的文化。此处的加注“补偿”体现出译者对该表达背后深厚文化内涵的认知,这样处理较清楚地交代了该文化意象的基本特征,使原、译作实现了表层平衡。
四、结语
苗族史诗是苗族人民原生态的文化百科全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要对其进行准确、生动的英译实属不易,由马克·本德尔领衔翻译的《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充分体现了阐释学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的主观理解和文化意识会不自觉地渗透到源文本中,从而使两种文化的差异或被弥补或被隐化处理,再以最切近译入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将文本信息传递给译入语读者。译者既是原文解读者,又是苗文化传播者。本德尔通过增译、添加注释等翻译方法,充分展现出苗族的文化、民俗和自然环境,助力苗族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苗族史诗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进行苗族文化的译介时,译者只有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准确领会其文化背景之下的深层含义。通过在翻译中妥善处理和表达,才能更有效地对外推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让少数民族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刘汝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与翻译的多维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14(2):123-128.
[3]BENDER M.Butterfly Mother:Miao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China[M].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6.
[4]吴一文,今旦,马克·本德尔,等.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
[5]吴一方.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苗族史诗》三语翻译刍论[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12.
[6]王治国.《苗族史诗》中民俗事象翻译的民族志阐释[J].民俗研究,2017(1):116-121.
[7]朱晓烽.《苗族史诗》英译的语境重构——基于副文本的解读[J].外语电化学,2019,(8):19-24.
[8]刘雪芹.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她们从远古的歌谣中走来[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9]吴一文,刘雪芹.《苗族史诗》汉译与英译的若干问题——《苗族史诗》汉文译注者吴一文教授采访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7):30-36.
[10]SCHLEIERMACHER F.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In A.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2.
[11]高圣兵.譯学刍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12]STEINER G.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287.
[1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14]刘云虹.选择、适应、影响——译者主体性与翻译批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4):48-54.
[15]BENDER M.Hmong Oral Epics: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an Epic Master-text[J].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3(Z1):306-317.
[1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7]马晶晶,穆雷.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本德尔教授访谈录[J].东方翻译,2017(5):47-51+67.
[18]BENDER M.Co-creations,Master Texts,and Monuments:Long Narrative Poem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J].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2019,38(2).
[19]LEFEVERE A.Introdu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J].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5,47(1):1-10.
[20]陈永龄.民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21]刘锋,吴小花.苗族婚姻制度变迁六十年——以贵州省施秉县夯巴寨为例[J].民族研究,2009(2):38-46+112.
[22]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21-25.
[23]胡廷夺,李榕屏.苗族古歌[M].燕宝,整理译注.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11.
[2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
[25]彭兆荣.西南舅权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mong Oral Epics
ZHOU Jie, YANG 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Hmong Oral Epics is a book translated by Mark Bender, an American scholar, and his team. It fully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posed by translational hermeneutics. As a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Miao culture, the book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translated works for the study of the Miao epic songs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iscipline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Based on the four stages in the hermeneutic model of translation, namely, initiative trust, aggressive intrusion, incorporation and restitution of bal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Hmong Oral Epics in terms of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ethnic classics.
Key words:
Hmong Oral Epics; hermeneutic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收稿日期: 2022-02-28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苗族典籍英译研究”(19GZYB29)。
作者简介:周杰,女,四川乐山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杨敏,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参见《贵州日报》2014年5月17日第12版的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