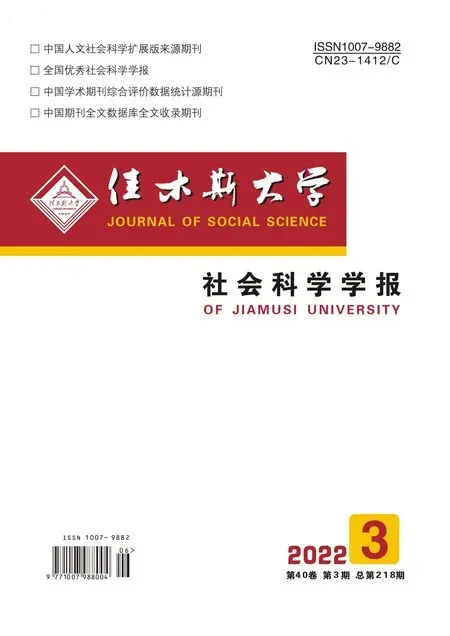文化正确迁移:许渊冲英译《西厢记》魅力探源*
张浩元,朱慧敏,张秀梅
(1.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廊坊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西厢记》乃我国传统经典剧目,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其创作的原始素材来自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会真记》,不过《会真记》仍受封建思维诸如男尊女卑、“女性祸水论”思想的桎梏,因而存在诸多弊病。在后世的流传、改编中,细节得到了不同幅度的调整完善,最后王实甫创作出杂剧《西厢记》,成为中国剧作史上第一部篇幅最大、描写人物性格最细腻的作品,由于其反对封建礼教、门阀婚姻的主体具有深刻而普遍的意义,于是立刻就在剧坛风行,而且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1]。在其后的明清时代更是出现了多达60余种的刊本,最为时人认可的为金圣叹点评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许译本便是以此为源文本进行翻译。
《西厢记》主要有5个英译本,最早译本是熊式一(S.I.Hisiung)的TheRomanceoftheWesternChamber;第二个译本是哈特(Henry H.Hart)的TheWestChamber——AMedievalDrama,1936年出版;第三个译本是West Wing,杜为廉(W.Dolby)译,1984 年出版;第四个译本是1992年由许渊冲译前四本十六折,1997 年,许渊冲对照《大中华文库·西厢记》对全文进行订正,并同时增译了第五本共计二十折完成了全文英译。
《西厢记》的遣词造句继承了大量《诗经·国风》的典故,其他的典故更是比比皆是,加之文风内敛含蓄,读者若无较高的文化素养,阅读原文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哈特其译作的序言中承认‘原文本有些例子晦涩难懂,对文本造成理解性的障碍……典故太多,甚至对中国读者也毫无意义。’显而易见,基于此背景下,哈特在译作过程中未能就博大精深的原作来做一番严谨考究”[2]。五位译者中,国人译者仅有熊式一与许渊冲叔侄两人,且二者扎实的双语实力和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鲜有人能望其项背,加之其长期从事与中国典籍的翻译,其对原文理解之透彻,翻译之精妙广受认可,而许渊冲又算得上是熊式一的传承者,遂选取许渊冲译本进行剖析。
一、文化迁移的意义
汪榕培曾评价自己的所译《牡丹亭》:“我的译文应该是创造性地准确再现原著的风采。字对字的翻译当然不等于忠实于原文”[3],其译文做到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意象和特点,独白和散体对话翻译得简明易懂,唱词和诗句则尽力还原原文的风貌。李正栓主张忠实对等的翻译原则,强调“忠实对等的文化迁移”“既然是对外介绍中国文化与文学,笔者赞成用异化方法,让英语读者通过阅读有异国情调的译文而了解那个未知的世界,增加心理与文化张力而产生阅读兴趣。”[4]在其翻译的《毛泽东诗词精华》之中补充了相关常见词牌英译的附录,另外其《河北戏曲名剧选译》中也以此原则为基准进行了文化的保留与传递。上文提及哈特译本中删去了一些自认为晦涩之处,但尽管如此哈特译本也是尽力保留《西厢记》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根据郭亚文、张清菡(2019)的研究,《西厢记》多种语种译者之中也不乏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进行文化迁移的译本,并引起了各国读者对中国戏曲以及中国文化的关注。
许渊冲提出“三美”的翻译主张,对译文提出了音美、形美、意美的要求,2021年其又从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出发对译论进行了阐释,认为“从心所欲的目的是求‘美’,不逾矩的目的是求‘真’。”[5]虽然这两条理论并无明确对文化迁移作出说明,但可以发现其对文化的态度,译文若想从音、形、意三方面保留原文的美,那么原文所蕴含的文化特点必然会由原文迁移至译文,而求‘真’求‘美’的译文亦是如此。在许渊冲所译《西厢记》中,虽然存在有着大量的意译痕迹,但也是为了保证译文可读、可理解而作出的取舍,整体来看,译文中还是保留了大量的典故、意象。由上可见,诸位知名的当代翻译家都认识到了文化迁移的重要性,并在践行着文化迁移策略。而中国特色文化外译应当整体以异化为主、注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才是宣介中国文化的最佳翻译方式。
文化迁移主要从形式、意识形态两方面展开,例如:诗词的翻译需要讲究韵律、音节、诗行长度等,此为形式类的文化,能够传递形式类传统文化的译文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到源语中诗词的形式特点;而原文中影射出的思想感情则是意识形态类的文化,能够传递意识形态类文化的译文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到源语中常见的文化元素、人文特点,从而更好地认识异域国度。对于同为传统文学形式的戏曲,其翻译要做到文化迁移也应当从这两方面出发。
二、形式类文化迁移
1.曲牌名的翻译
曲牌,俗称“牌子”,我们耳熟能详的【念奴娇】【醉花阴】【天净沙】等皆属于曲牌。在古代戏曲之元杂剧中,“一本杂剧通常分为四折,每一折都是由宫调相同的若干曲牌组成一个有引子和尾声的套曲,多数情况下是第一折用仙吕【点绛唇】套曲,第四折用双调【新水令】套曲,第二、第三折对宫调的选择稍自由。”[6]在《西厢记》中,曲牌的应用也符合这个特点。曲牌决定了唱词的配乐,是戏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曲牌与词牌极为相似、渊源颇深,同时,“曲牌渗透于宫廷、文人、宗教、民俗等各文化体系之中,通过研究曲牌有利于我们认识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诸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7]可见,曲牌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而曲牌名在英语之中没有与之对应或相似的存在,因而这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属于语际翻译之中较为特殊的现象,王洁认为词牌名的翻译应当做到,考究词牌的典故、区分中英相同意象的不同含义和避免目的性过重导致译文生硬难懂。“在英译词牌名这个包含了互为异质的多民族文学的文化场中,译者应该对词学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特色、来源、形成和发展趋势,还要对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有所认识和理解”[8]类比可知,曲牌名亦是如此。
许渊冲所译的英汉对照《西厢记》中,保留了戏剧的这一大特色,每处曲牌名皆译出,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化特色、异域风情。下面列举书中部分实例:

表1 英汉对照《西厢记》中许渊冲所译曲牌名部分实例
译文中对于词牌的翻译较为灵活,并非一味采用意译或者直译,上例之中,【新令】【赏花时】【满庭芳】均为直译,【油葫芦】是对一种蟋蟀的民间称呼,因其爱吃油脂类植物而得名,将其译为“Field Cricket”也算作是意译。其余,【四煞】【三煞】【二煞】【煞尾】其字面虽为“四、三、二、尾”,但实质是倒数第四、三、二、一的意思,译文则是按此顺序进行的翻译,以帮助大家理解,而【六幺序】则指代唐代著名的舞蹈“绿腰”,此处也进行了意译。此外,“仙吕”“双调”等在原文中与曲牌一起出现的宫调,许也在译文中一并保留。再看同为许渊冲翻译的《宋词三百首》亦是考究词牌名的渊源,例如:【念奴娇】译为Charm of a Maiden Singer,【江城子】译为River Side Town,【卜算子】译为Song of Divination。根据典故详细考究词牌名,最后根据其含义进行选择是进行直译,还是阐释其深层含义进行意译。虽然上述译文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意译的痕迹,但终归都是以一种异化的策略将美好的意象亦或是流传的典故以英文的形式书写,将曲牌这个独特的音乐文化宣介到英语世界中。
2.唱词的翻译
唱词相比折名和曲牌名所占篇幅更多,是承载戏曲文本艺术性的重头,也是做文化迁移的主力军,而唱词的翻译与诗词翻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韵律、意象、意境、诗节数量、译文长度等。每个唱段有对应的曲牌,唱词长短不一,句数也不尽相同,可见唱段更像是词,而以上特点也是体现戏曲唱词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许译本中可以看出译者在尽力去维持原作的唱词长短,但是《西厢记》中极为古朴精简的用词却大大地限制了译者的发挥,例如:“偷花汉”一词,短短三个字却很难以三个英文单词来进行翻译,即便是能做到,在音节数上“flower”一词就已有三个音节,“因为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之间存在着天生的简繁差别,汉诗在英译的过程之中,其诗行不可避免地要拉长。”[9]所以笔者认为在追求译文长度方面实难完满,亦不必苛求。以上现象也必然引起唱词句数的差异,在许译本中大部分唱词的译文与原文句数相等,但也存在译文进行扩展的部分,例如:“满纸春愁墨未干”,若要将其繁复的含义整合在一句译文中,难免要使用定语、状语得出一个复杂的长句,这就破坏了原唱词简练的音韵,同时还将意象的渲染空间拉长,得出不一样的体验。对此许渊冲的处理方法是过于繁杂的唱词进行拆分处理,以上唱词译文为:“The ink is not yet dried, Like grief of rainy spring at rising tide.”译文虽在句子数量上做出了让步,却将原文满纸愁思的意境迁移至译文中,也称得上忠实。而在韵律方面,许译文可谓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为译文读者带来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韵律盛宴。
整体上来看,许译文中唱词的翻虽然在长度以及句数上未能做到尽善尽美,却做到了传递原唱词的意境,同时其得出的译文具有唱词参差、押韵的特点,若说“汉语古典诗歌多为齐言诗,也就多具匀齐之美”[9]那么唱词就算得上是独具“参差之美”。许译文很好地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英文中的十四行诗区分开来,确实从文化层面做到了对戏曲唱词的宣介,是文化迁移的典范之举。
三、意识形态类文化迁移
1.戏曲情景的还原
能够流传至今的戏曲,必定在情景上有着过人之处,而我国独特的文化便蕴含其中,是文化迁移不可忽视的一环。《堂前巧辩》是《西厢记》中演出最多的一折,在这一折中,矛盾激烈,剧情急转直下,红娘和老夫人的斗智斗勇广受观众的欢迎,其言辞的考究之处也比比皆是,这无疑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因此挑选该折的精彩之处进行剖析。
此出中,红娘与老夫人二人进行激烈的唇枪舌战,试想丫鬟与当家主母的斗智斗勇,丫鬟先是害怕,之后“反咬一口”,最后胸有成竹地拿下一城,二人无论肢体、神态还是内心都有着丰富的变化,应当尽力还原原文中措辞的风貌,这绝非是通过单纯的直译或是意译能做到的,而是应在脑海中还原场景,充分体会源文本词句的含义,并再转化到目的语中。例如,红娘受到拷问回复老夫人时所答:“非干张生、小姐、红娘之事,乃夫人之过也。”此处,红娘将罪责反扣回老夫人头上,心中难免有底气不足,但又要说服老夫人因而需要话语强硬、底气十足,若按字面译为it is not Master Zhang, Miss Oriole or Rose’s guilt.It is mistress’s fault.句式单调毫无节奏感不说,且很难还原出人物心理动态,许渊冲将其译为It is neither Master Zhang nor Miss Oriole nor Rose who is to blame.The fault is yours, Madame.首先使用强调句,坚定地撇开三人的罪责,之后使用普通句委婉的说“乃夫人之过”,将红娘的心理活动和言语措辞都生动地以英文再现出来,译文之巧妙令人赞叹。而透过译文展示出的蕴含在红娘这个人物身上智勇双全的优秀品质和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希冀,便是我国文化向上向善的最好体现,这便是最佳的文化迁移。
2.含蓄表达的翻译
中英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与两种语言的使用者成长的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关联。汉语中经常使用含蓄的表达,以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态来展示语意,这在典籍之中更为明显,《西厢记》中,张生爱慕莺莺却说是见月思人,莺莺心许张生却道才子应当怜惜佳人,这是我国语言的一大特色,根据语义学的划分,也就是联想意义之中所属的含蓄意义在中文行文中较多。在翻译时我们应当保留这种差异,使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换言之,也就是要在能够正确的传达含蓄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地保留中文的含蓄表达方式。由于含蓄意义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就给翻译中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稍有疏忽,就会望文生义,误入歧途,使原文的信息和美学功能丧失殆尽,稍有不慎又会 得 ‘意’ 忘形,意得而神丧,使原本可以体现的美学功能荡然无存”[10]。
此处具体将含蓄的表达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为散体对话中的含蓄表达,即为日常内敛的说话方式,这一类话语仅需直接进行直译,读者便可稍加推敲的到期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例如:老夫人拷问红娘崔张二人是否有夫妻之实时,红娘回答:“他两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虽未正面回答,但是两心相悦的才子佳人长达月余共宿一室,答案为何自不必多说,诸如此类的含蓄表达无论英汉读者都能够理解,因而直接直译为They’ve slept together over a month。其二为包含典故的含蓄表达,这一类的源文本相对较为晦涩,即使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译者自身也要查阅平行文本才能理解,此时如果仍采用直译,会对读者的阅读产生较大的而影响,因而不得不放弃互文性带来的多重美感来保证译文可读性、可理解性。例如:原文中“绸缪”(仇牟)出自《诗经·唐风·绸缪》,本意为纠缠,捆束,后人用其代指男女欢好、缠绵不断,因而可直接译为their heads were close together like two flowers,也就是纠缠在一起的花朵,就显得十分传神达意。不过这样的翻译手法删去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负载词,降低了文章的异域风情,如果这类较为晦涩的意象,能够通过附录或是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特色文化的保留度将更上一层楼,可能会达到更佳的效果,但纵观译文中国古典美学中所钟爱的内敛、含蓄之美确实得到了迁移,展示在英文读者面前。
综上所述同,许渊冲凭借其高超的语言功底、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灵感才思成功地推动《西厢记》走出了国门,其译文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不仅仅来自于许渊冲精湛的翻译技巧,更离不开其对于宣介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意识。而其在文化迁移方面的尝试不仅仅聚焦于形式上的内容,更放眼于意识形态文化的传递,这样的翻译方式不仅仅对于戏曲翻译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对将中国文化推出国门,树立积极的中国形象也极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