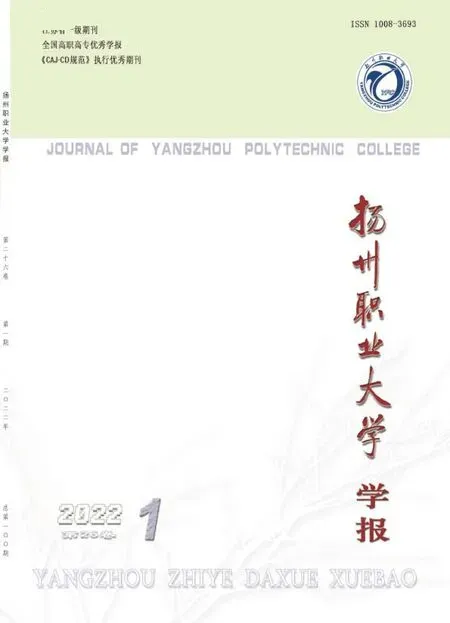清代扬州学者对方志学理论的探讨
晁 胜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7)
清代是地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数量堪称历代之最,这一方面得益于官方的鼓励和提倡,清代统治者曾经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诏令地方编修本地方志以供史馆采选,“诏督抚下郡县,于是天下始知志为国家所重”[1],雍正皇帝又下令各地方志应每六十年一修,这直接促进了方志编修的兴盛。另一方面,方志的价值也逐渐被学者们发现,使得各大名家也参与到了方志的编修中,这其中不乏章学诚和戴震这样的学派巨孹。扬州素来为东南巨邑,经济的繁华促进了人文的兴盛,发展到清代有“文人志士半于海内”之誉。这是清代扬州地区方志兴盛的坚实基础。有清一代扬州地区共修有方志约78部之多,存世有67 部,平均每三年就有一部志书面世,其盛可见一斑。在编纂过程中,扬州学者彼此交流探讨,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方志学理论,在其指导下扬州地区佳志频出,在中国方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 编纂理念
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2]。方志的性质决定了方志编纂一定要实事求是,内容务必求真求实,一秉大公。扬州学者们的编纂理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1 公心修志
很多有过方志编修经历的学者们都曾坦言修志要比修史难,原因在于志书多由本地人编修而成,不免会有失公正。汪士璜在《雍正高邮州志》中写道:“古人论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史,予谓三者固难,而尤难者一,出之以至公之心盖史可以传信也,一有顾忌而史伪矣,一有护惜而史伪矣,一有阿曲而史又伪矣,中怀顾忌护惜阿曲之私,则虽才学识之俱优,所以长其浮夸,而反足为史累。作史固难而修志尤难,地不越比闾族党之近,不外群萃州处之伦。”[3]他认为修志比修史更难的地方在于以至公之心参与编修地方志,方志为地方所修,修志之人又多是本地人,编修人员难免会困于私心而有碍志书的权威性。尤其是县一级的志书,由于官府经费不足,修志费用常常需要募捐,富家大族便借此机会笼络修纂人员。在修《道光泰州志》时,修志者多为当地富室高銮,没有秉持公心,在人物志一门中,为高氏家族立传者竟然有十几人之多,志书刊印以后,舆论大哗,结果不得不另修《道光新志勘谬》二卷。伊秉绶在主持编纂《扬州府志》时,为了表示自己不徇私情,取信于古,府志内容全是其他书籍抄录而来,以至于“无一言无出处”,完全不涉及时事。虽然伊秉绶的修志方法不可取,但也表明了其在修志时能够处以公心。
1.2 重视地图绘制
地图在方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扬州学者的代表人物,阮元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不但有《十三经注疏》这样的经学大作,更有《考工记车制图解》《畴人传》等科技著作。阮元所编修《广东通志》,将地图在方志中的使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但主张每县一图,而且在其编修的方志中经常能够看见插图,这在其他方志中是非常罕见的。“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为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4]2鉴于古代绘图技术的欠缺,阮元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了便于绘图,他认为可以“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5]408,这样一来“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5]408,这种化整为零的办法实属便于大区域的地图制作。在《广东通志·海防略》中,就有附图20张,这些地图不同于普通地图,对重要的两地之间会标注精确的距离,例如“急水门至石笋八十里”“鸡啼门至大金七十里”[6]36,这不但能够精确地反映两地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起到比例尺的作用。地图中对战略要地也进行了特殊的注解,例如“崖门东西炮台外俯汪海内通新会大河,为商船出入冲要之区”[6]37,甚至从这些地图注解中可以窥见官方的海防政策,例如“沙角炮台坐落镇远南门之外,后夷船出入粤省冲要海道扼截尤需要紧”[6]37。阮元对于这些海防地图也颇为得意,“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6]3。从这些海防地图可以看出,清代官方对于海防的重视,并非传统看法中清代海防疲敝不堪,也为今天了解鸦片战争前夕的广东海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刘宝楠私撰方志《宝应图经》用14张地图描绘出宝应地区从汉代到清代的历代县域,被誉为“清代方志奇书”,该方志所绘地图精于水道,从地图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历代宝应地区的水域变迁,针对扬州段大运河提出了“邗沟十三变”的观点。为撰此图经,刘宝楠考证各代书籍达78种之多。他在《宝应图经·序》中总结道:“《宝应志》有三难:唐人撰集地志,平安、安宜,前后相袭,稽其旧邑,在今境西南。唐初安宜,实迁今治,其地东兼射阳,西跨东阳,三境牙错,并为一县。而欲考城邑于邱墟,辨封疆于桑海,此一难也。典午东迁,侨立郡县。一隅之地,分为数州;一丸之城,立为数郡。瓜剖豆分,朝更夕变。或以宾夺主,但擁虚名;或以寄乱真,全无实土。而欲条析蜗疆,缕分蚁壤,此二难也。境内运河纵纬百里,诸湖纡远,本非直渠,或东或西,十有余变。岸边谷屡迁,失其故道。而欲寻川于陆,问水于陵,此三难也。”[7]461

有扬州学派“殿军”之誉的刘师培也曾论述过地图的重要性,他认为旧志图表过于简陋,厕立于序目凡例之间。并指出“今编地志,宜县各为图,城厢四境,复各为分图”[9]251。清末,西方地图学的传入,对扬州方志地图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清末扬州方志中,地图大多绘作精美,而且引入了比例尺和规范的图例,并标出南北方向,实用价值较传统地图提升很大。扬州学者们编纂地方志能够如此地重视地图的绘制和收录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修大清一统志时,雍正帝曾下发上谕称:“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10]这表明官方认为方志应当重人文而轻地理。
1.3 重视实地考察
闻见为虚,眼见为实。扬州学者们在编纂志书时,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很多官修志书专门设有采访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多者可达数十人,他们负责访民俗问民情,考察各地的碑刻、遗址、遗迹等,直接影响方志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刘赞勋编纂《咸丰重修宝应县志辩》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编写《咸丰重修宝应县志》没有聘请采访人员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导致志书的讹误之处颇多。刘赞勋在此志书中,根据自己的实地采访,针对旧志记载的讹误之处一一纠正,其考证详实备受后世学者称赞。刘宝楠在私撰《宝应图经》时,为了理清宝应地理变迁,“考城邑于丘墟,辨封疆于桑海”“寻川于陆,问水于陵”[7]461,《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赞此书为:“有益于地方文献者实巨,非第文章淹雅,采录宏博已也。”[11]焦循在《上郡守尹公书》中也认为,纂修志书,重在实地考察,“访于时人,询请故老,不厌于详,不嫌于琐”[12]12,如果志书所载内容非作者耳闻目见,则实难令读者信服。
2 志书体例
体例在志书编纂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扬州学者们也多次强调体例对志书的先导作用。焦循认为方志应当依照史记的体例,“国史宜本《汉书》,郡志当依《史记》”[12]12,为此他解释到:“何也,《汉书》断代则前不连古,后不及今国史之例也,《史记》上及轩辕下终汉武,郡志之例也。”[12]12并且十分赞赏《史记》“按事立格,依文树义”[12]12的体例原则。在他自己所私纂的《北湖小志》中,便是用此原则来划分类目,全书共计六卷,分为叙水、叙农、叙渔、传记、叙人瑞等十六个类目,体例清晰,一目了然。阮元对于志书体例同样看重,他在奏请重修《广东通志》时,首先便表达出对旧志体例的不满之处。他在奏折中写道:“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4]2他对谢启昆所纂修的《广西通志》大加赞赏,认为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4]2,后来其重修的《广东通志》体例便以《广西通志》体例为蓝本有所增损而成,全书共计分为训典、表、略、录、列传、杂录六类,共计二十四门,并比《广西通志》增加了“杂录”一类,杂录中多记载一些奇闻异事,因真实性有待考证,所以阮元将其编为一类,这也表示出阮元“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学思想。
刘师培曾论道:“今宜用伯益书例以志山,用郦氏书例以志水,用宋氏书例以志城厢。若台榭陂池,府寺宫观,名城巨邑,夥颐莫殚,即学士大夫登高览古,一觞一咏,动成故实,履綦莫寻,孤简斯寄,咸是增美山川,今宜援地类记,不复各自为编,以具条贯。”[9]249刘师培认为应该设立“方言志”,指出设立方言志颇为有益,一是有利于读古书,并称不明白荆楚之方言,不能读懂《楚辞》,不明齐鲁之方言,不可以读《论语》,并称方言志应该效仿《尔雅》篇目撰写。二是有利于考古音古义,刘氏认为古人各以方言为韵,后人以近代之通语为韵,时过境迁,虽然今天的方言和古人的方言不一样,也与古人的雅言不一样,但是方言中会夹杂一些雅言,深入了解各地方言对考究古书有所益处。
3 志书内容
3.1 方志应讲求实用
自清初顾炎武开启经世致用的朴学学风以来,清代学者一直砥砺于考据经史等实用之学,对方志的编修也力求功用。阮元在其所编修的《广东通志》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地理情况等内容占去全志的半数以上,足以可见其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焦循在参与编修《扬州府志》时,认为对于人物传的搜列应该主要参考其功业和文采,“无功业文章,但有科第者,虽宰相状元,仅列一名于此表,不必别为立传”[12]14。选入“政略”的官员,必须在官任上做出相当大的政绩。他还主张对于一些正史中所没有记载的事情,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求博取而丛拾,以便集腋成裘,酿花为蜜。刘师培认为编修方志的目的便是推进乡邦政教以及促进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地方自治。他主张创编“新方志”,他认为方志必须有利于地方自治,推进本地的政治治理和教育,认为编写人物志就是为了达到教育后人的目的,对于那些为本地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要立“专志”,以表彰他们的功绩。新方志要汇编地方风物,以供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参考,应当反映地方民俗,“宜当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9]249。他还对旧志内容重政治轻经济有所不满,认为方志应该注重实业,对于那些地方工匠也应该立传,以振兴实业。
3.2 方志应详今略古
在方志内容的收录上,向来有两派,一派称为厚古派,他们主张厚古薄今,花费大量的篇幅记载古代情况,当代的情况却很简略。主张厚今薄今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戴震、洪亮吉、孙星衍这样的大家。而扬州学者们却属于另一派,普遍以详今略古为原则。焦循参与编修《扬州图经》时,扬州知府伊秉绶,为了表示自己“取信于古”[12]10,主张新编方志“仅用纂录,不易一字,而标以出处”[12]10,要求修纂人员仅仅将历代志书以及相关文献中有关扬州的资料抄录成册,然后汇编成新修方志。焦循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此诚取信于古,恐有整空证伪志病也”[12]12。“天下政治随时措宜,史志县志可变通而不可拘泥”[12]12,他认为方志编纂应该紧随当下所发生的时事进行记述,应该“书其实迹,不厌与详,不烦于琐”[12]12。对于一些无法求证的传闻应该免于收录,他批评到:“稽之册籍,询诸故老,是为所闻异辞也,事远年湮,咨询莫及,既不可见,复不可闻,无可奈何。”[12]13“以传闻为本,闻见为虚,是舍实事求是之路,趋无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为然也。”[12]13焦循认为对当代亲眼所见之事弃而不载,反倒记载那些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之事并不是明智之举,后人读者也不会相信书中内容。在其所拟定的方志门目中,古代沿革事迹仅占一目,其详今的编纂原则可见一斑。
4 续志理论
续修方志由来已久,降至明代,还并未形成科学的续志方法,尤其是对待旧志的保存上,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扬州学者的重要特点之一,阮元认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而旧志遂废,古法不复讲矣”[13]234。对旧志的破坏表现出极大的惋惜。清代奉行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扬州学者们认为对前人所修旧志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存。在颜希源纂修《嘉庆仪征县续志》时,阮元劝其“但续新志而旧志不必更张”[13]234。道光年间,王检心任仪征知县,在续修仪征县志时,主张新旧各志,一律重修,阮元又劝其“欲得新志之善,必须留存旧志”[14]21,并且主张在方志各门之中,先次列前志,最后再列新修志书。新旧志书有异之处,应该详细注明,发现旧志中有缺漏的地方,要另立校补一类。而且可以为后人读者保留旧志,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详略合宜,同时“学者读此一编,即可见诸志之崖略,其有裨益于掌故,岂不伟哉!”[13]234刘文淇也参与修纂《道光重修仪征县志》,他曾和阮元讨论过续志的问题,并十分认同阮元存续旧志的续志观点。“余尝馆于太傅(阮元)处,亦尝论及修志之事,谓不可掩蔽前人,此次修志拟推广其意而变通其法”[14]18,并具体指出这样做的优点有五个,一是可以保留旧书,二是可以对比各部志书的得失,不至于“空言某志善某志不善”[14]19,三是可以避免重复遗漏,认为“修志之法贵精密而戒复漏,聚则易精易密”[14]19,条列各志于前以求精密。四是可以事半功倍,节省时间和经费。五是可以为后世做出表率,以便于后世续志时,也能保存现在所修的新志。但是在如何编修新志,刘文淇也有和阮元不一样的看法,对于“新增有为各志所无”的监法、事略一类,应当“不妨照府志等书新立一门而注明其故”[14]19,这样一来,新修志书不拘泥于旧志体例,不但对旧志所无之处予以补充,也能顺应时代变化,推陈出新,更好地记录地方情况,并列举后汉书也有补遗前汉书的例子,仍“能各自为编,不相牵涉,则时代之说亦不过于拘也”[14]20。
此外,清朝统治者要求方志每六十年一修,但是扬州学者们主张修志周期更短,例如焦循便主张四十年一修。这样才能完备地记载时事,不至于“日愈多而事愈烦矣”[12]14。扬州学者们主张在旧志之后续接新志,但这并不是完全放任旧志所有的内容于不顾,对于旧志中缺漏存疑之处,也要在新志予以考辩和纠正。李宗孔在《重修扬州府志》序中写道:“史之成也,一定而不移。志之作也,随时而更定。”[15]12他认为史书和志书的区别之一便是志书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
5 对史志关系的理解
入宋以来,地方志的地理属性逐渐降低,逐渐从属于史学,许多史家学者也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章学诚把地方志定义为“一方之全史”的主张被广泛接受,方志编纂者强调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纵观清代方志序跋,“国之有史,郡之有志”,将地志比之国史的主张已经成为修纂者的滥觞。“志乃史体”的编纂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将方志提升到史学的层面上来,这在古代的学术风气下,无疑是有利于方志学的进步和发展的。但扬州的学者们却并没有因此而使得方志完全成为“地方史书”,反而借助史书的性质,将志书的地位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清代扬州学者在方志的纂修中,仍然能够从地方志的发展演变中看到其不同于史书的根本特征,主张独立的方志学。尹会一在主修雍正府志时论道:“夫史有纪、有表、有传、有志,而邦国之志自昔通名曰志,夫志识也,志其地,志其时,志其事,三才之道备焉。”[15]《嘉庆扬州府志》的主纂德庆认为:“夫作志之道与作史异。褒贬予夺一秉大公以为天下后世龟鉴,此史氏之体裁也。举山川形势之要,胪风俗人物之盛,去短寻长,彰善隐恶,此志家之流别也。”[16]《宝应图经》的作者刘宝楠也认为修志与修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尤其是修志的要点在于历代舆图以及建置沿革演变的考证上。在修纂目的方面,志书不仅仅同史书一样供后世借鉴治乱得失,志书更多地扮演着正民风教的角色,志书中有大量的风俗志、礼俗志,人物志中含有大量的“节妇”事迹。扬州学者们认为志书并不等同于史书,是记载一个地方各种情况的书籍,是国史的材料来源。汪懋麟在《重修扬州府志序》中曾言:“统天下之志,上之天子付之太史,采择而书之,即以成一代之史。”[15]27李宗孔在《重修扬州府志序》曾系统的论述道:“郡邑之有志也,尤方舆之史也。其人物臧否,尤史之世家列传,其山川、形胜、云物、吉祥尤史之天官、河渠。其物产、土宜、风俗、好尚,尤史之平准、货殖。而人文之盛衰,制度之兴废沿革,尤礼乐儒林艺文诸书其事。”[15]10后人称章学诚为“方志学的奠基人”。诚然章学诚作为方志学家,其本人也参与修纂了《和州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方志学的理论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学界的研究深入,章学诚以外的其他方志学者,例如戴震等,颇有一种为其正名的趋势[17]。古代方志的纂修源远流长,方志理论的发展必然是在方志纂修的实践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的,清代扬州学者投身于方志的纂修中,其数量庞大,而名志也不在少数,对于方志学理论的贡献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