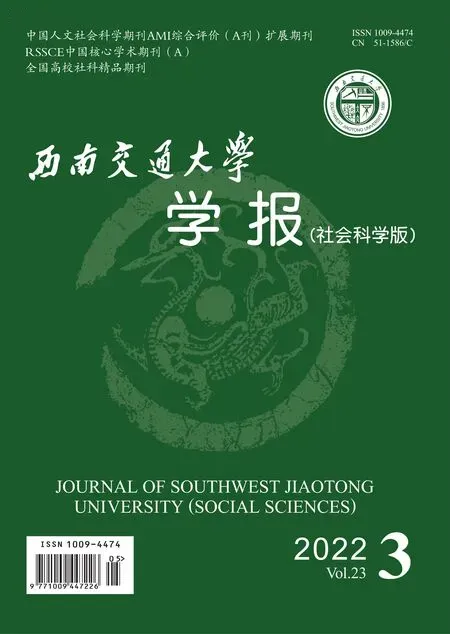胡瑗的仁学思想浅析
张爱萍, 张培高
《吕氏春秋》把儒学的本质概括为“贵仁”〔1〕。这一总结无疑是恰当的。孔子有“求仁”“依于仁”(《四书章句集注·述而》)〔2〕之论,孟子更是认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四书章句集注·梁惠王上》)〔2〕。正因如此,韩愈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即是“仁学”。“仁学”从汉唐至宋明经历了明显转型,即对“仁”的论证由以宇宙生成论为主转变成以宇宙本体论为主,由以“性三品论”为基转变成以“性二元论”为基。
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理学先驱,其仁学既有继承汉唐仁学的一面,又呈现出理学的特征,明显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虽然学界关于胡瑗经学或儒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并未对其“仁学”给予应有的重视。即便偶有研究〔4〕,也因不了解其仁学的理论基础而不能把握其特色,进而无法确定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全面了解理学先驱对仁学的贡献。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胡瑗的《周易口义》《中庸义》《洪范口义》为主要文献,力图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其仁学的特色及不足。
一、“仁”的界说:“广爱无私谓之仁”“博爱之谓仁”
胡瑗用两种略有不同的说法来界定“仁”:一者是“博爱之谓仁”〔5〕,一者为“广爱无私谓之仁”(《礼记集说·中庸》)〔6〕。这两种说法在先秦实有不同的来源,前者系儒者之说,后者则出自道家的概括。
从儒家本身来说,据许慎《说文解字》可知,“仁”字有三种写法,字形虽异,然含义则同,许慎曰:“仁,亲也,从人从二。忎,古文仁,从千心。,古文仁,或从尸”〔7〕。而“亲”之本义为父母,故此,“仁”之本义为“爱双亲”。这可在先秦文献中找到依据,如《国语》云:“为仁者,爱亲之谓仁”〔8〕。此义在《孟子》中也有所体现,如云:“亲亲,仁也”(《四书章句集注·告子下》)〔2〕。然而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学者们发现“仁”在先秦还有别的写法,写作“”或“”〔9〕。由此引发了对“仁”之本义的争论:或谓对自己的爱〔10〕,或谓对他人的爱〔11〕,或谓两者皆有之〔12〕。这些解释皆异于传统,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从儒学思想史上整体观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仍然是传统的解释,即随着对“仁”认识的深入,到孔子时,“仁”已由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所以孔子说:“爱人”(《四书章句集注·颜渊》)〔2〕。这一界定得到了后人的继承,如《中庸》云:“仁者,人也”〔13〕,《孟子》曰:“仁者爱人”〔2〕。而《郭店楚简》中有不少语句则直接支持了许叔重的观点。如《唐虞之道》曰:“爱亲而忘贤,仁而未义也”〔14〕,又如《六位》云:“仁者,子德也……仁,内也。义,外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14〕,《五行》云:“爱父,其继爱人,仁也”〔14〕。这些引文都说明许慎关于“爱亲”为“仁”之本意的解释是符合先秦儒家主张的。
既然“仁”所指的对象是“泛爱众”(《四书章句集注·学而》)〔2〕或“亲亲而仁民”(《四书章句集注·尽心上》)〔2〕,那么此“爱”必然是普遍之爱。《孝经》之基调虽在于弘扬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但也强调普遍之爱,甚至认为能爱他人必然能爱双亲(“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15〕)。西汉的董仲舒进一步把“博爱”与“仁”作了密切的关联:“先之以博爱,教以仁”(《春秋繁露义证·五行之义》)〔16〕。在此基础上,唐代的韩愈直接提出了“博爱之谓仁”〔17〕的说法。邢昺认为“博”为“大”之义〔15〕,所以“泛爱众”即是“博爱众人”〔18〕,此亦是“仁”(“泛爱济众是仁道也”〔18〕)。由此可知,胡瑗以“博爱”释“仁”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说法。
在先秦,与“广爱无私谓之仁”最为接近的说法是《庄子·天道》的“中心物恺,兼爱无私”〔19〕。此虽不能确定是孔子所说,但《庄子》的这一概括仍可在儒家文献中找到依据。如《荀子》亦以“兼爱”形容之:“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20〕。受此影响,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也以此作为儒、墨核心价值之共称:“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21〕。在儒家、墨家看来,“兼”之义实在于通过“视人如己”而爱他人,如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又如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22〕
既然如此,胡瑗为何不完全采用《庄子》之概括呢?究其原因有二:(1)遵从孟子之说,即虽然“兼爱”已经出现在《荀子》中,但孟子曾对墨子的“兼爱”之说有严厉的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2〕),受其影响,故而不说“兼爱”,而是改为“广爱”。(2)因不完全认同道家的根本主张,故对《庄子》之概括作了儒家化的改造。“道法自然”是老庄共同的主张,《庄子》为了表达此主张,把孔子及其弟子作为相当重要的人物。从《庄子》全文来看,《庄子》虽有时把孔子塑造为“得道者”的形象,但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上述所引《天道》之语便系孔子对老子陈述其主张时所言。在孔子看来,“仁义”是“十二经”的要义,并且是“真人之性”,而“兼爱无私”系其实质。孔子话音一落,老子立即表示反对,进而陈述了其“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之“自然无为”的主张。对此,胡瑗只是部分赞同,即只认为天是自然无为的,而圣人与天不同。他说:“天地以生成为心,未尝有忧之之心,但任其自然而已,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若圣贤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忧虑万物之意,是以其功或过于天地。”〔23〕由上可见,胡瑗并未完全采用《庄子》之说,而是对其作了相应改变,即用《论语义疏》中的“广爱”(1)皇侃释《论语》“泛爱众”云:“泛,广也。君子尊贤容众,故广爱一切也”,又释“君子敬而无失”曰:“敬而无失,是广爱众也”。见氏著、陈苏镇等点校《论语义疏》,收入《儒藏》精华编104第221页、4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代替“兼爱”,以示与《庄子》相区别。
二、“仁”的来源:“圣人法之”“人禀天地之善性”
阅读《国语》《左传》等文献可知,作为儒家核心观念的“仁”“义”“礼”等在西周春秋时期已相当流行,但当时的“仁”只是众多德目中的一个,并未成为特别重要的概念〔24〕。这种状况到孔子时有了改观,孔子在《论语》中不仅谈“仁”达百余次,远高于其他德目的频次,而且开始把“仁”作为其他德目的基础与实质,如云:“人而不仁,如礼何?”(《四书章句集注·八佾》)〔2〕对此,杨伯峻先生指出:“春秋时代重礼……《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25〕。孔子虽充分肯定了个体求“仁”的主动性(2)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述而》,第100页。,也看到了大众求“仁”的急切性(3)孔子说:“民之于仁,甚于水火。”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卫灵公》,第169页。,但并未对“仁”作哲学上的论证,尤其是对“为人由己”(《四书章句集注·颜渊》)〔2〕“推己及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未作形而上的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易传》《孟子》实际上是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前者由天至人,后者由人至天,即前者先预设天的道德属性,以此作为道德人伦的哲学依据;后者相反,先预设人性之善,然后推人及天,以“天”作为道德的根据。
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善性”,其具体内容是“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四书章句集注·告子上》〔2〕),这同时也是“推己及人”的基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四书章句集注·公孙丑上》〔2〕)。《易大传》则从宇宙生成论上加以论证,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26〕。“仁爱”之可能、人之“善性”之形成皆源自“天地”。在《十翼》中,《文言》还把“仁义礼智”与“易”之四德“元、亨、利、贞”相匹配,其中“元”与“仁”相对应(《周易正义》卷一《乾传》)〔26〕。《乐记》与《系辞》类似,也从宇宙论的高度上对“仁义”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13〕《乐记》中的思想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汉人把“五常”与“五行”“四时”“阴阳”合在一起论述,其中春对应的是“阳”“仁”“木”,如《白虎通》曰:“木者阳,阳者施生……藏于木者,于依仁也……木王即谓之春”〔27〕。
《乐记》《白虎通》从宇宙论高度论证“五常”之来源的思路对后世文人学者影响甚大。胡瑗即是其中之一,他在《周易口义》中说:“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圣人法之,以仁而生成天下之民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四者在《易》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28〕,“木主春,春为施生,故为仁恩之令也”〔29〕。
汉人之所以把“春”与“仁”相配,关键在于看到了“仁爱”万物的前提必须是肯定物的存在。即虽然孔子以“爱人”释“仁”,后孟子进一步扩大了“爱”的对象,主张“仁民而爱物”,但他们都未进一步追问仁爱“对象”的来源问题。或许由此,《系辞》的作者在以“生生”界定“易”及肯定“生生”是“天地”之“大德”的同时,也认为“仁”是圣人“守位”的保证(《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26〕。不过,《易传》并未直接认为“易”或“生”即是“仁”。汉代的董仲舒则直接指出“生”即是“仁”,他说:“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义证·王道通》)〔16〕。在此问题上,《白虎通》更加细化,以五行之木配春、配阳而主“生”,“仁”在其中。
与上述说法不同,胡瑗不仅把“阴阳五行”与“四时”合论,还与“四德”共析,但可能是受制于《易传》之本义及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并未像董仲舒那样认为“天”就是“仁”,而是说“圣人法之”,因为圣人效法于“天”,所以能够与天地合德。他说:“夫天高而覆,地厚而载,故其德曰生。圣人亦能以仁爱生成于物,故与天地合德。”〔28〕圣人效法天地而“仁爱”万物。然圣人可行,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亦可行。因为圣人在传统中都被视为最高的理想人格,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4)如胡瑗说:“夫圣人得天地之正性,继天地之行事,故无所不知,无所不明。”见胡瑗《周易口义》卷十一,第373页。。为避免因“主体”单一而影响“仁”的普遍化展开,胡瑗认为其他人也具有此能力。他说:“天以一气降于地以施生万物,……君子以仁义宽爱而恤于下。”〔30〕在此,胡瑗通过强调人与自然具有“生”之共同特征而论证天人合一,从形式上看当然算是有效的论证,但问题是若不对天地之“生”作善恶属性的界定,那么由此得到的“圣人”具有“仁爱”的品质或能以此生成万物之结论就经不起检验。因为尽管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如果“天地”之生只是一种自然行为而并无伦理可言,那么圣人所效法的就仍只是天地之自然生成的规律。如此一来,天人之间其实还有距离,即圣人之“善”与天地之纯自然规律不相对应,故未能达到真正的合一。可见他的这种论证与后来的理学家相比,层次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说胡瑗从“生生”的宇宙论上论证“仁”之来源主要是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的话,那么他从“人性”的内在性上论证“仁”的来源则有重大的创新。孟子的“性善论”在汉唐期间,除了孔颖达、李翱等少数士人外,鲜有知音,然而却在宋人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响。胡瑗便是其中的先驱。
首先,胡瑗认为人性皆善,并非只有圣人的性才是善的、普通人的性全是恶的(《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三)〔6〕,换言之,之所以人性皆为善,在于人皆有“五常之性”(《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三十三)〔6〕。这一主张可谓是宋代“性善论”之滥觞,因为后来的理学家在人性论上的论证逻辑正是沿着此论开出的方向前行的〔31〕。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此论只是继承了孟子、孔颖达和李翱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因为孔、李也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如孔颖达曰:“凡人皆有善性”〔32〕,李翱亦曰:“圣人知人之性皆善”(5)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四部丛刊本。。
其次,胡瑗对“性善”进行了宇宙论上的证论,他并未以人之内在本身的“五常善性”作为人性善的唯一依据,还以为此“善性”源自“天”,即“元善之气”〔33〕和“天地之善性”(“夫人禀天地之善性”〔33〕)。能否就此判定胡瑗认为“天地”本身是“善”的呢?此问题暂时不论,下文言之。在此需要着重强调两点。
第一,与孟子、孔颖达和李翱相比,胡氏的论证具有重大创新。李翱与孟子一样并未从宇宙论角度对“性善”进行溯源,只是认为其是天所赋予的。孔颖达与他们有所不同,即他在“人性皆善”上虽无形上的证明,但从元气论上论证了“性九品”说的合理性。孔氏认为,气有清浊之分,圣人所得全为清气、愚人所得皆为浊气,而清浊之气泾渭分明,故两者不可变化,并引孔子之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礼记正义·中庸》)〔13〕作为论据。如此一来,孔氏《中庸正义》中的说法便与《洪范正义》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也坚决否定了普通民众为善和成为君子圣人的可能性。既然普通百姓不能通过后天的修养改变人性,由恶至五常之善,那么哪有实施“仁爱”可能呢?即人没有内在的仁义之善性,自然就没有实施仁爱的意识与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胡瑗的认识与孔颖达有根本的不同:一方面,他主张人皆有善性,断然否决了孔氏“愚人”全为恶且根本不能变善之论;另一方面,他也从宇宙生成论上对“人皆有善性”的论断做了论证——任何人皆禀有“天地之善性”。从仁学上看,胡瑗之所以如此“断然”,旨在为普遍推行儒家核心价值观作哲学的论证,因为唯有在此前提下,广大民众才可能成为推行“仁义”的主体。所以他认为,天地在生人的同时,也赋予了众人践行“仁爱”的可能,正所谓“(天地)立仁义之道以本于人”〔34〕。
第二,在胡瑗看来,由“元善之气”或“天地之善性”所赋予的“人性”具有“至明”“至正”和“至公”的特点,而圣人禀有的“善性”最全,故自然能够“仁爱”他人。他说:“元善之气受之于人,皆有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圣人得天地之全性……以仁爱天下之人,以义宜天下之物。”〔33〕圣人所禀有的天地“善性”是“全性”,而此善性之“全”体现为最高、最大的公正,如此就完全摆脱了私利与邪恶,故而圣人自然就有实施与推行“仁义”的自觉与能力。此处胡瑗提及的主体是“圣人”,但若将主体换为贤人或普通士人乃至普通民众,那么他们之间在推行“仁爱”的能力上有区别吗?胡瑗认为是有区别的,首先在于圣人与其他人在所禀“五常之性”的量上有较明显的区别。他说:“性者,五常之性,圣人得天之全性,众人则禀赋有厚薄”(《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三十三)〔6〕,“夫圣人得天性之全,故五常之道无所不备。贤人得天性之偏,故五常之道多所不备”〔33〕。不管是把贤人与众人合在一起说还是单独突出贤人,胡氏皆在强调圣人、贤人和众人在禀有“善性”的量上具有递减的特征。依照上述逻辑,“全性”与“至正”“至公”的品质相对应,贤人与众人在“正”与“公”的品质上也不如圣人完备,因此在推行“仁爱”的自觉程度上也就有了差距。其次,在胡瑗看来,众人、贤人与圣人的差异还体现在才智上。圣人因为“全性”故才智最全,称为“至明”,而其他人(包括贤人)则是:“贤人才智有所偏”〔35〕“天下百姓、常常之人,得天性之少者,故不可以明圣人所行之事”〔33〕。才智上与圣人的距离也就决定了众人推行“仁爱”的能力要受到诸多限制。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并无质的不同,所以胡瑗依然肯定了所有人具有推行“仁爱”的资格。如此,就与孔颖达的主张区别了开来。如前所言,受孟子“性善论”的影响,胡瑗认为人皆有善性,但不同的人所禀有的“善”性有偏全之别,这与孔颖达所说的“性九品说”似乎有相似之处,但细究起来则不同,即“九品说”认为其中有一类人完全不具有善性。不过,胡氏虽肯定了善性人皆有之,但同时也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善性的区别。而此区别若是先天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间必然有张力。对此,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表明胡瑗的思想不成熟、逻辑不融洽,甚至自相矛盾。二是胡瑗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维度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即从先天的普遍必然性上肯定人性皆善,从后天的偶然性上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两者并不矛盾。相对来说,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对于前者,胡瑗用“天地之性”作概括:“性者,天所禀之性也。天地之性……然而元善之气受之于人,皆有善性”,这是从整体上论述人的善性。对于后者,胡氏则基于现实生活中贤人君子少而常人多的考虑,认为他们之间的差别恰恰是后天所禀有的“五常之性”量的不同所导致的。从仁学史上说,胡瑗在整体上肯定人人皆有实施“仁义”之能力的同时,又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推行“仁义”能力的个体差异。尽管胡瑗没有直接提出“性二元论”,但他的这些论述中已经蕴含了后来理学家所主张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模式,无论从思想史、心性论史角度看,都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一种崭新的人性论在此已经露出了端倪。
三、“仁”的培育与实施:“必须仁义道德遍及于天下”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常识上看,有推行“仁爱”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其付诸实践。可能与现实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但胡瑗认为圣人不仅有此能力,还必须把此潜能变成现实,这是圣人必要的担当。所以胡瑗说,圣人虽然富有天下,但必须仁爱天下,使天下之人乃至物都得到关爱〔36〕。换言之,仁爱天下、经世济民是“圣人”的宿命,对于普通士人来说则是终极的价值追求。胡瑗说:“(君子)则怀仁义……其志在于佐君以泽天下之民物而已”〔37〕,“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37〕这不仅是对孔子“修己以安人”思想的弘扬,也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念的承继。
范仲淹对当时儒家“仁义”核心价值观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认为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儒家价值观。他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四民诗》)〔38〕“回此天地力”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儒家的“仁义”之道。范仲淹不仅以“乐道忘忧”(《睦州谢上表》)〔39〕“进退惟道”(《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39〕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也以此要求士人“当崇德而无倦”(《临川羡鱼赋》)〔40〕。作为范仲淹门下贤士〔41〕,胡瑗对范仲淹的思想及其所担心的社会问题自然是相当了解的,所以继承其思想也在情理之中。他认为士人无论贫、富,不管是在顺境、逆境,都必须始终怀有“仁义之心”“以道自乐”。他说:“(君子之人)推仁义不忍之心,独立特行,挺然而无所惧惮……如此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业也……苟不得已而不可为,当韬光遁迹,养晦仁义,以道自乐,不与世俗混于衰弊之中而无所忧闷也。”〔37〕因心中有“仁义”之道,所以在任何处境中皆不会丧失人生的追求和内心的宁静。即便在逆境或不可为之时,也只是“隐其身而不隐其道”,即“韬光遁迹,养晦仁义,以道自乐”,耐心地等待机会,一旦有机会便会及时“施仁义之术生成天下,以益天下之民”〔30〕。他还对“隐身于山林”的思想与行为作了严厉批评〔23〕,从而与佛道的价值观划清了界限。
胡瑗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乃基于思想是行为之先导这一基本逻辑。他说:“君子之人,先求仁义以益于身。身既益,则其仁义之道可以推及于天下。”〔5〕通常只有在价值观的引导下,士人才会自觉地追求“仁义”,并主动地施“仁义”于他人。但另一方面,士人即便有思想或价值观的引导,也不一定就能把“仁义”很好地落实到实践中。现实生活中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时常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找不到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如何“施仁”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在施“仁”的方法上,孔子、孟子曾有不少论述,如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四书章句集注·卫灵公》)〔2〕,孟子则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术”“同情”的思想(《四书章句集注·梁惠王上》)〔2〕。胡瑗则更进一步,一方面将《中庸》的“尽性”之论和《孟子》的“性善论”及“仁术”“同情”之说有机融合在一起。《中庸》“尽性”说的关键在于推“己性”及“人性”和“物性”,而孟子的“同情”也有此意,因为除了“老吾老、幼吾幼”之论外,他还有“君子远庖厨”之说(《四书章句集注·梁惠王上》)〔2〕。胡瑗指出:“夫圣人禀天地之全性,五常之道皆出于中,天下有一物不被其赐者,若己内于沟壑。由是推己之性以观天下之性,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33〕,“圣人将尽物之性,设为制度,定为禁令,不使失其生育”(《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三十三)〔6〕。“五常之道”“若己”源自《孟子》,而“推己之性”“尽物之性”则出自《中庸》。但与郑玄、孔颖达相比,胡瑗不仅解释了圣人为何能推“己”至“物”的原由,而且解释了“己性”“物性”之所以能够统一的依据,即圣人有“仁爱”之心、懂“生生”之理。同时,他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和王弼的“圣人有情”论也做了有机整合。在《论语》中,孔子明确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释“恕”,于是“恕”便有“视人如己”的意思,后人通常也是如此解释的,如王弼释曰:“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皇侃亦曰:“恕,谓忖我以度于人也……以己测物,则万物之理皆可穷验也”(《论语义疏·里仁》)〔42〕。“反情”就是“忖我以度于人”,即“移情”。“移情”的前提是肯定情感的真实性,王弼对此毫不怀疑,甚至认为圣人也不异于众人(《论语义疏·泰伯》)〔42〕,这与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有明显区别。胡瑗继承了前人的“重情”思想,并以此作为推行“仁爱”的基础。他一方面认为禀有天地之“全性”的圣人能够与天下之人共喜、怒,故可“以仁爱天下之人,以义宜天下之物”〔33〕,另一方面又认为因为人皆有爱欲之情感,故可以推行“恕”道而实行“仁爱”(《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七)〔6〕。表面上看,胡瑗从“恕”及“情同”上推行“仁爱”似乎只是继承了前人的思想,但其实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唐代的李翱在回应佛教的挑战时,特别重视心性论的建构,提出了“灭情复性”说。“情”之所以要“灭”,乃在于他受佛教的影响而侧重强调了“情”之消极面(“情者妄也、邪也”(6)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中》,四部丛刊本。),但这一思想违背了先秦儒家重情的思想,所以胡瑗从圣人、众人皆有情的角度强调“仁爱”,不仅使“仁爱”的推行具备了可操作性,而且在批评李翱“灭情”的同时恢复了先秦儒家重情的传统〔43〕。
如上所述,“圣人”因禀有“天地之全性”,故而能自觉“仁爱天下”。但仅就“圣人”来说,在周公以前,圣人与圣王是统一的,但自周公以降,圣人与圣王开始分离,其结果便是随着“天子”权威的下降,诸侯逐渐掌握实权,能把“仁爱”具体落实到天下人身上的责任实际上主要由君主担任了。君主集权建立后,春秋战国时的“君主”就成为了“皇帝”。但在先秦,民重于君是儒者的共同主张,如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四书章句集注·尽心下》)〔2〕。这里的“重”“轻”不仅意味着民、君之重要程度,也蕴含着君为民之意。
胡瑗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主张,也坚决认为“仁爱”天下是君主的基本义务〔44〕。孟子认为“仁心”是推行“仁政”的基础,换言之,在孟子看来,“仁政”其实是君主“仁心”的具体落实。而“仁政”的基本宗旨在于保障老百姓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之必需。胡瑗在其基础上作了推进,他说:“盖以仁义之道,务农重本,轻徭役薄赋,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财用丰实而又安其所居,使各得其所”〔23〕。胡瑗论述的重点虽也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上,但与孟子所论主要是使百姓免于饥寒交迫相比,胡瑗则推进到富足程度了,由其“充足”“丰实”之语可知。在“薄赋”上,胡瑗对“什一税制”高度赞同,认为此“为万世中正常行之法”〔30〕。按理,在财富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统治者对“百姓”“薄”了,就意味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用于君主个人及其家族消耗的财富就减少了,故鲁哀公有“二,吾犹不足”(《四书章句集注·颜渊》)〔2〕之叹,但这在胡瑗看来,是理所当然之事,正所谓“益者,损上以益下,损君以益民,明圣人之志在于民也。”〔30〕
对于“仁爱”天下的圣人或君主而言,要把“仁政”推行至天下,除了制订“轻税”等良政之外,还必须选择“贤者”加以具体落实。因此,选择“能臣”是推行仁爱的又一个良方。《论语》曰:“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四书章句集注·卫灵公》)〔2〕虽然从表面上看孔子是要求子贡向贤者、仁者学习,但其实意在强调只有贤者、仁者才能达到“仁”。《孟子》亦曰:“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四书章句集注·尽心上》)〔2〕因此对于普通士人来说,要想在实施“仁爱”方面有大作为,让自己成为圣贤是必要的前提。基于此,胡瑗把“存心于圣贤以自任”〔45〕作为普通士人的追求。从推行“仁爱”于天下的维度上说,原因有三:一是贤人具有“仁爱”优先的意识,这是“推己及人”的重要前提。所以他说:“圣贤之人仁义道德……而蕴畜其心,然后扩而充之天下”〔23〕,又说:“圣贤之人皆以仁义为先……使天下罔有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圣贤之用心也”〔35〕。二是贤人往往能够得其位,这也是“仁爱”天下的前提。胡瑗说:“有圣人之行,有仁义之道……苟不得其位,则无兴天下之势,无居天下之资。是则虽有仁义之道,安能有所为哉?”〔46〕自隋唐以来,尽管普通士人获得“位”相对于汉唐容易得多,但能获得“位”之人往往都是有学之士。贤士获得“位”后,才有“势”与“资”落实“仁爱”。三是“贤人”具有“仁爱”天下的才能。在前论中已提及,贤人虽不如圣人,但因禀有较多量的“善性”,故更有能力推行仁爱。
既然成为“圣贤”是士人的价值追求,那么方法有哪些呢?胡瑗从内在的心性修养和外在的格物致知的角度做了论述。
第一,抑邪复性。在胡瑗看来,虽然任何人皆禀有“五常之性”,但普通士人与圣贤相比,不仅禀有量较少,同时受“好逸恶劳”自然之情的影响,所以本有的“善性”自己认识不到或有所损失。对此,可以通过“明心复性”的办法加以恢复,其关键在于邪恶之意刚萌发时就把它抑制住,进而恢复“善性”〔23〕,而这是为“仁”的首要前提,所以他说:“君子之人,始能治其心,明其性……至此可以为仁,可以为义”〔29〕。
第二,积善成圣。通过抑邪于未发之际来“复性”的方法属于“事前”的方法,然而若恶已形成,此法就无效了。此时,便可采取“积善”的方法。此法的要义在于使“善”的量持续不断地增加,积小善以至大善,聚小贤达到大贤,进而成为圣人〔44〕。
第三,格物致知。关于胡瑗培养学生成材的事例,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如《二程语录》《朱子语类》等,但记载较为详细的还是《宋元学案》,曰:“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47〕由此可知,“格物”包括“经义”“治事”两方面的内容:前者的任务在于通晓儒家义理,可归为“格物”之“体”;而“治民”“讲武”等主要属于实用技能,可归为“格物”之“用”的方面。胡瑗采取“体用兼备”的教学方法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仁人志士以经世济民。如胡瑗弟子刘彝擅长水利,在赣州为政时,其所主持修造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泄洪作用,造福了一方百姓,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参观该址时给予了“防洪排涝,造福百姓”的高度评价。而从儒家“仁”的角度看,“造福百姓”实际就是士人“以仁爱天下之人”的具体落实。
四、结语
在北宋时期,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士人对胡瑗的人品、教法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较早对其学术作评价的却是朱熹,曰:“教以安定之传,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47〕,薛季瑄非常认同此说〔47〕。
对朱熹的评价不能盲从,要辩证地分析。若说安定之学“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因为仅从现存的《周易口义》即可看出其并非“章句诵说”,而是“义理”之作,不仅对汉唐的注疏多有批评,还有不少根本性的创新,对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稍加对照便不难发现,《程氏易传》即受其影响。说胡瑗之学“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言过其实了。所谓“有一定的道理”是指胡瑗的学术思想与后来的理学家相比,确有不少尚需完善之处。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胡氏的性论,从表面上看就存在矛盾。因为他一方面认为“人皆有善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善性”有“偏”“全”之别。前者意在强调人性的平等,后者则意在强调人性的差异。因此,若不对这两者间的不同作出说明,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相矛盾。此中的矛盾或模糊之处,后来的张载、二程的“性二元论”才真正给予解决,即从体上说,人性是平等的,皆是善的,从用上说,人性是不完全平等的,是有差异的。
所谓“言过其实”是指尽管胡瑗的学术思想还有不足之处,但要说“远不相逮”则不仅过分夸大其不足,而且抹杀了其理论创新及对理学家的深刻影响。首先,以性论来说,胡瑗的性论对理学家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胡瑗在前人尤其是孔颖达的基础上,初步创建了“性元二论”之模型,即在主张人皆有善性的同时,又以禀气之偏全解释恶之来源,尽管表述有模糊不清之处,但仍不乏思想的创新,不然不会有后来理学家成熟的“性二元论”。其次,从仁学上来说,胡瑗的“仁学”对小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二程的仁学因为皆受到其师周敦颐的影响(周敦颐明确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48〕),故不乏有共同之处,如都讲“大公”,又如皆认为仁者的境界是“无私无我”的一体境界,大程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49〕“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49〕之言,小程亦有“圣人无私无我”〔49〕“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49〕之说。但两人的仁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如在对“仁”的界定上,大程倾向于以“体”训“仁”,而小程则偏重以“公”释“仁”,有“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49〕等言论。其原因何在?除两人的气质、性格相异外,还与两人的思想来源不同有关。从渊源上说,小程以“公”释“仁”深受胡瑗的影响。因为胡氏明确说,圣人禀天地之全性,自有“至公”“至正”的品质,从而能够自觉“仁爱天下”(见前)。胡瑗的理由很简单,即一个人的精力、时间与财富是有限的,若不是出于“公”意,那么其“仁爱天下”之自觉必然会受到限制。对于与其师胡瑗“知契独深”的小程来说,必然是极为熟悉该思想的,所以也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49〕,“公则一,私则万殊”〔49〕。不过,小程与胡瑗仁学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如胡瑗以“博爱”界定“仁”,而小程则认为“仁”是“性”、“爱”是“情”,小程的这一思想影响了朱熹。因不是本文的主旨,只能另文再详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