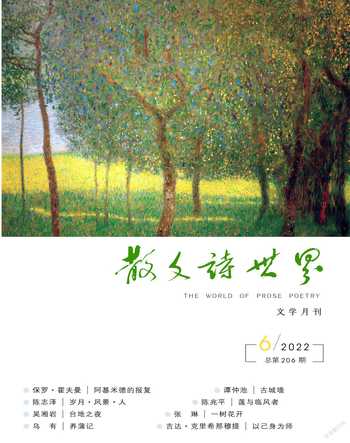一树花开 组章
张琳
簌簌衣巾数枣花
鲁迅先生在《秋夜》中曾写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正如鲁迅先生一样,老家的房屋前也栽了两棵枣树,一棵结长枣,细小微长像冬瓜,青果木红果甜,叫冬瓜枣;另一棵结圆枣,圆圆胖胖像灯笼,青果脆红果蜜,叫灯笼枣。两棵相距不到3米,冬瓜枣树细长紧凑挺拔,灯笼枣树矮粗歪脖蓬松。
“四月八,枣树芽儿麻”。当惊蛰的雷声轰降隆地响过之后,暖暖的春风伴着点点雨水从村头麦田地里吹了过来,墙院外头已是桃红李日的树却才从夜的沉睡中渐渐醒转。起初,它一点儿也不忙于抽枝发芽,而是先静静伸张开它春天的信息,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现,两个树枝围着的权节骨之中,似于在一夜间,长出了一片片翠绿的新叶,簇拥在冬天那些枯枝周围,和着细柔的春风在尽地舒展着。
站在树下,静听那春雨流汤在枣叶上的砰砰敲击和春风吹过叶边的沙沙摩擦声,你会惊呼平日里看起来干枯的躯干竟能孕育出如此的绿意,在这些叶子中间,生了许多像小米粒一样的东西,绿油油的带着点嫩黄,犹如刚刚长成的少女,不施粉黛也自然动人。而枣花,它却隐藏着自己,全无怨言,任由枣叶出尽风头。它知道,痴心的小蜜蜂会找到它,采集它的粉去酿蜜。据说枣花的蜜有很多功效,枣花花期很短,没有几天便结出一个尖尖的小青枣。枣花竭尽全力地孕育果实,等到秋风乍起,颗颗红玛瑙般的果子将会挂满枝头。
清代诗人潘内召在《咏枣花》中说“忽忆故乡树,枣花色正新。枝迎馌饷妇,香惹卖浆人。纂纂飞轻雪,离离缀素珍。只今秋渐好,频扑任西邻。”枣花,它没有美丽的外表,也没有钻心的香氛,它无法张扬自己。它的花蕾小得可怜,青青的,而又瘦黄,好像米粒般大小。它的长相貌似桂花,可没有桂花的香气,也没有桂花的傲气,一切都无可比拟。尽管如此,它并不自弃,它知道自己足以让人喜爱,让人陶醉。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我想说的也许就是枣花的这种品性吧。
枣花盛开的季节,我喜欢在一场雨后的清晨,静静地站在老屋门前枣树下。叶子青翠欲滴、碧绿闪亮,那或许是对落花深情地凝视和抚慰吧?枣树开花,香气缭绕。“簌簌衣巾落枣花”,一朵、两朵、三朵……直至数不过来。一阵风雨吹过,枣树下已铺成一层黄毯子,不由的出双手接住,不忍落在地下。
离开故乡很多年,每每想起那些年,那些在枣树下,抔起一抔枣花,随风洒向小伙伴身上,互相追逐嬉闹的日子,总是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这份无虑和开心,或许只留在了一次次的梦中。
槐花郁纷醉万家
“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尺”。洋槐,树体高大,叶色鲜绿,春季花开时呈洁白色。每年立夏前后,在春雨的滋润下,洋槐树便开始吐出嫩芽,在春风中风情万种的摇曳着,如含羞的少女,甚是楚楚可怜。
不多久灰褐色的枝条便披上了淡绿色的外衣,绿色遥看近却无,紧接着淡绿便变成浓绿,更为欣欣向荣了。不知哪一天,一串串肥硕诱人的槐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偷偷长出,散发出醉人的清香。一小朵一小朵的对开着,整齐而精致,如亲密无间的姊妹,一串一串地相互簇拥着,推着挤着喧闹着,好不热闹,给春天带来了些许生气。一串串的洋槐花咧开小嘴,吐露着芬芳,引来无数蜂蝶。槐花呈串状,花朵白而晶莹,一串串、一簇簇,堆满了枝头,压弯了槐枝。远远望去,仿佛落了一树厚厚的白雪,只不过这层层叠叠的白雪更富于生命的律动。
初夏暖暖的阳光下,似乎每一片花瓣上都闪耀着一张清新的笑脸。微风拂过,那颤动的满树槐花,纷纷洒洒,似一群雪白的蝴蝶,展翅欲飞。如此时,在树下微闭双眼,用心静静感受这份久违的清香,整个人便陶醉其中了。蜜蜂是最勤劳的,他们或是在枝头呼朋唤友,或是在花丛翩翩起舞、或是在蕊间勤劳采蜜,生怕错过了这短暂的花期。
我们小孩子自然不会闲着,三五成群,挎着竹篮,拿一根长长的竹竿,上边绑着一把割麦子的镰刀,在树下用力把细枝和花桠拉下。大多时候我们会麻利地爬上高高的洋槐树,骑在树叉上面,将竹篮子挂在树枝上,这时候必须要小心,因为洋槐树上面会长很多三角形的刺,稍不注意,就会在手上、胳膊上留下一个长长的划痕。小心翼翼地伸手拉起一枝槐花,看着刚有苞蕾的花,就用手轻轻地捋下一把,有时候来不及放到竹篮里,便迫不及待的塞入口中,满口清香。在那个时候,一把绽放着花蕾的洋槐花就是我们的眼中的人间美味
槐林五月漾槐花,郁郁纷纷醉万家。洋槐花,既可以作药材,又可作食材。历史记载杜甫喜欢吃槐花,又喜欢吃槐叶的传闻,因而留下“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的诗句。我最喜欢吃娘做的蒸洋槐花,她把槐花用清水洗干净,沥干水分,拌上一些面粉,加上鹽和调料,找一个笼布铺在篦子上,把拌好的洋槐花均匀摊铺好,在锅里蒸熟。出锅后,用姜蒜蓉汁和芝麻油一拌,香香软软,丝丝甜甜,既是主食也是菜,伴我度过了童年太多美好时光。有时候娘还把槐花做成馅,包包子或者饺子吃,或者干脆做成槐花汤,出锅时候点几滴芝麻油,槐花的清香和着芝麻的鲜香,常常是还没端起碗,就已经把口水咽下了。
小小的一树洋槐花,从花开吃到花落,从童年吃到少年,直到我打起背包走进军营。蓦然回首,转身已过了不惑之年,故乡的一树洋槐花,留下了我童年的梦,记载着家乡的情,凝聚着娘的爱。
汪国真在《我知道》诗里写到:槐花正香,月色正明。我想幸福如果有味道的话,应该就是洋槐花这样的味道吧:淡淡的、纯纯的、甜甜的、暖暖的……
杏花雨落杨柳风
“压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当故乡槐花香还在唇齿间弥香逗留,满树的青杏就一天天变着颜色,早早穿上黄色外衣,酸酸甜甜引诱着过往行人的味蕾。
记忆里邻居院子里有一颗老杏树,树径很粗,约有六、七米高。老树把漫长岁月凝成了厚厚一层龟裂的黑色树皮,树冠形如巨伞,密不透光,纵容着那些深绿色苔藓,在块状树皮上肆意疯长,一部分枝干伸展到房屋顶上。远远望去,树干如同披了一件铜锈斑斑的盔甲,寒往暑至,春去秋来,老杏树承受着四季的风霜雪雨。
每年春天一到,院子里的杏树就开始结花骨朵,露出了它那饱满的脸颊,胀得粉红,没几天就按纳不住激动的心情,便绽放开了幸福的笑脸。放眼望去,一簇簇竞相吐蕊、如雪似玉。从远处俯瞰,洁白的杏花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如同一朵朵漂浮在空中的白云,给初春农村院落增添了一丝勃勃生机。而微风拂过,一朵朵花瓣随风飘落,又像是回到了冬天那个大雪纷飞的季节。不禁令人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到“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古诗词中穿越。
杏花的开放时间仅有十天左右,身上厚厚的衣服还没来得及减退,杏花便开始落下,褪去了春的美丽。不久,便有拇指甲盖大小的小青杏挂在枝头。紧接着,杏树便开始抽出新的叶子,慢慢地由抽出的新节变成硕大的叶子。小青杏掩映在绿叶中间,好像新的生命在颤动,好不诱人。有时禁不住诱惑摘一颗放在嘴里尝尝,涩涩的,酸酸的,眨巴着挤住眼睛,嘴里不住地吸溜,不忍再尝;有时会捡起被风吹掉到地上的杏,杏果肉咬掉,把杏仁用力一挤,苦苦的杏仁汁液便溅得满脸都是,小伙伴们便哈哈大笑起来。
细雨轻风落楝花
“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那一树树紫色的小花,犹如年少的梦,编织着整个夏天,萦绕在心头眼底。
老家院墙子里有一颗高大的楝树,自童年起,它就陪伴着我,我长它也长。这棵楝树笔直,有碗口粗,皴裂的褐色的表皮上星星点点。枝干疏朗有致,树叶细长、稀疏,给人简约、清欢的感觉。
“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光到楝花”,二十四番花信风上说,所有的春花中,楝花扮演的是殿后将军的角色,楝花开罢,整个春天的花事也就结束了。宋代何梦桂在《再和昭德孙燕子韵》中说:“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后楝花风。”楝花一开,夏天也就不远了。每年暮春时节,在故乡绿阴如盖的村庄里、小路边、河渠旁,楝树静静地伫立着,微风吹来,它自由地舒展着枝叶,浓化着春意,暖暖的,柔柔的,像亭亭玉立的少女,沉静、含蓄、宠辱不惊。在清瘦的楝叶丛中,别致、文雅地挂着一团团、一簇簇淡蓝色的楝花,是那样的文静淡雅、柔美细碎,犹如情窦初开的少女。
苦楝花比较特别,圆锥花序,细细小小的紫色花儿,伶俐地靠在一起,开在枝头一丛丛一簇簇。而每一朵小花极富特色,花萼五处深裂,花瓣淡紫色,苦楝花是单体雄蕊,花药完全分离,而花丝彼此连结成筒状,包围在雌蕊外面。花柱细长,不伸出雄蕊管,花的中心形成一个漂亮的紫色管状体。紫色的小花开满枝头,像紫云英,繁密,细碎。花茎细长,虽土里土气,却也身材窈窕,透着村姑般的纯朴,让人怜爱。
小而美且多的楝花,春末悠然地开着,风雨吹落一地,又开一树,蔚为壮观。散落在地的花瓣清新唯美,散发出阵阵香气,犹如南方紫色的蓝楹花。俯身捡起一朵,捏在指间,看着,看着,眼前便浮现一片姹紫嫣红,单调、枯燥的日子一下子变得灿烂多彩起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有人说楝树花的花语是望向遠方,只为一眼就能看见,人海中你温暖的笑颜。雪小禅在她的散文《苦楝的树 苦恋的心》中说:“苦恋的人,一直在低处——低微的心呀,只有爱上一个人,才会万转千回的低,还不嫌低,把心低到尘埃中去。那么凉的心,只有自己知道,只有那棵苦楝树知道”。楝树在她的文字里变得那么痴情,痴情到甘愿付出所有,而不求丝毫回报,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模样吧。我们眼里看到别人的光鲜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蛰伏和奋斗。
“紫丝晕粉缀鲜花,绿罗布叶攒飞霞。”这是宋代梅尧臣赞美楝花的佳句,花开无人赏,独自露芬芳的楝花在诗人眼中,竟然也有了别样的风姿和韵味,大概楝花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这般欣赏它吧?普通如楝花的我们,何妨在纷繁的世事中,在沧桑的岁月中静静地绽放呢,哪怕无人欣赏,无人喝彩,只要不辜负这时光,不辜负这生命,楝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