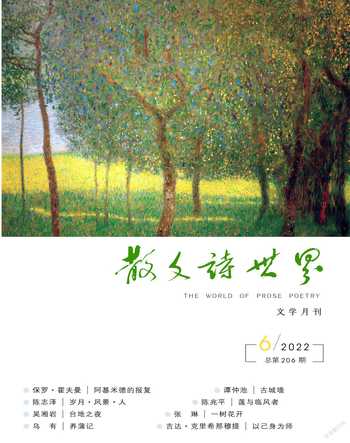台地之夜 外二章
吴湘岩
暮色开始收拢阳光的羽翅,天空仿佛一张硕大的毛边纸,墨汁一样的夜开始从它的边角晕染开来。
落日像个孕妇,即将分娩出璀璨的群星。寨子里的灯盏渐次被摁亮。它们全部都亮起来后,夜空里的星星仿佛顽童一样,陆续从家门蹦跶出来,很快,就占领了整座天穹。
从云贵高原吹过来的风,带着晚秋的凉意,吹动着星星,吹动着窗外的那几棵毛白杨。寨子里的灯火像眼睛,注视着大地,注视着我的窗口。
往事,风一样吹过青石板路。夜精灵悄悄地爬上了梦的屋檐,吐着炭黑的舌头,舔舐着窗户,以及天黑之后每户点亮一盏灯的寨子。
我知道,不需多久,夜色又将把一粒一粒灯火和睡梦中孩子们的呓语,一一拣拾,扔进黑暗的樊笼。彼时,璀璨的群星将成为寨子里最亮的灯盏,照彻茫茫的人间。像冬天的柴火,台地的夜愈深,火就愈大,灯就愈亮。
草木深深
世上本来有许多路,走的人少了,便成了荒野。自从乡村路改道,修通了水泥路,原来村里的古道马上被荒草占领,成为野生动物们的家园。
春天,山上的草木像野孩子一样疯狂地生长,而人迹一年比一年稀少。除了灰兔子、野猪、山雀,以及各种昆虫的鼓噪,整座山林没有丁点人的烟火气,空旷得像座被吸去了精气的废旧古庙。
到了清明,那个独自住在村头、常年蜗居屋里的哑巴老人,仿佛潜伏在岁月深处的地下工作者,被这个季节从暗处逼到了明处。
只见他握着一柄磨了一宿的镰刀,站在春風里,虔诚地守候在进山的路口。一直等到落坡的夕阳,把他的身影照得更加清瘦,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像头劳作了一天的老黄牛,踏上归家的路途。
草木深处,躲藏着一个与他失散多年的儿子。
一个人的下落
漆黑的夜,包裹着瘦骨嶙峋的你。车子在峁梁沟谷间,兜兜转转,颠簸得比你的一生还长。
来到你的村庄,只为打听你的下落。是心里的暗疾,将你吞噬?抑或失足,将你葬身于水腹?答案影影绰绰,像个该死的耽溺于捉迷藏的调皮鬼。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你曾经的阳光和自信全部都淹没在寨子里的漆黑里,它们黑洞一样,将你的青春吞噬。就像回不来的童年,以及村庄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鸡鸣犬吠,被时间无情的吞噬。
当初,为了摆脱命运的羁绊,你兜兜转转,走了三十年的路,如今都被荒草和夜精灵一一占领。转了一个圆圈,你又回到起点,回到草木的根部,被命运廉价的收购。
瓦檐上的半爿月亮,像天堂溃烂了的伤口,不停地朝着尘世倾泻暗夜的毒汁。现在,你让我又一次领略到了生活里的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