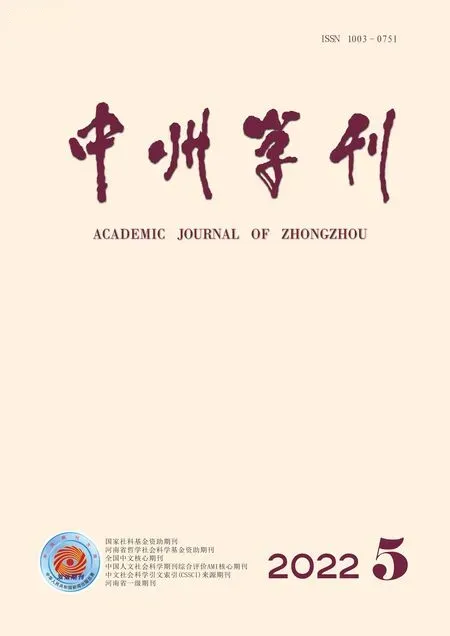古医论视角下《文心雕龙》刺文论*
桓 晓 红
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着以医喻文甚至以医事、医理论文理的现象,这种论文方式不但增强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形象性、生动性、理论性、生命性,更丰富了文学理论建构的视角和理论阐释的话语内涵。《文心雕龙》蕴含了古人所普遍认同的诗书乐舞等艺术治疗思想,不但提出了“言以散郁陶”“吐纳文艺”“志于文也,申写郁滞”等文学治疗主张,而且将医事、医理与传统诗文谏刺主旨进行整合和理论创新,发展出较为系统的诗文谏刺理论思想。
一、《文心雕龙》对谏刺传统的继承
“刺”作为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尚书》所强调的从谏如流、忠直谏刺和“诗言志”。《国语·周语上》载召公谏厉王弭谤,向厉王强调了广泛纳谏、倡扬谏刺的重要性,指出天子听政,要听取“师箴”“百工谏”“瞽、史教诲”。汉代出现了诠解《诗经》的四家诗,汉儒常引用《诗经》以述往讽今、劝谏帝王从而实现讽谏,“刺”在汉代诗评标准中具有至高地位。《毛诗序》提出了谏刺的原则:“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谏刺原则,与受崇尚的“直刺”“死谏”精神对立统一于中国古代士人风骨和古代文学发展中。正是基于统治者对纳谏的重视,魏晋六朝时期甚至刮起崇尚忠直谏刺的“骨鲠”之风,并反映到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中来。
刘勰秉持“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的原则,继承古圣贤与明君忠臣所崇尚、所高举的匡谏讽刺传统,并对其加以融合、创新和发展。《文心雕龙》在《明诗》《铭箴》《书记》《奏启》四篇中,着重论及了几种具有谏刺警戒功能的文体,并对不同文体的功能、写作规范、文辞特点、文体风格等进行了诠释、总结,使《文心雕龙》贯穿全篇的谏刺精神由史的线到关键的点和面的具体化、理论化、系统化。
《明诗》开篇指出“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强调诗歌对诗人情思志意的表达,并进一步指出诗歌具有扶持匡正人的情性品格的功用。刘勰秉持传统的“美刺”观,特别强调诗的“匡谏”功能,在《明诗》篇历数了它的发展轨迹:肇自《尚书》等圣人典谟,从怨愤而作的《五子之歌》到《诗经》,到怨刺之作《离骚》,再到汉代的“继轨周人”,到魏国正始文学、魏晋风骨,都遵循着“神理共契,政序相参”的诗歌谏刺传统准则。
《铭箴》篇指出,“箴”是用于官员对君主讽诵的,“铭”是题写于器物上供谏戒或赞颂的,二者名称用途不同,“而警戒实同”。刘勰更注重“箴”,将“铭”视为一种别样的谏刺形式,其功能和“箴”相同。他列举了先圣贤君重鉴戒、匡谏的事迹:黄帝刻字于车子和矮桌上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大禹在乐器架上刻字以招谏,商汤《盘铭》写“日新”的规诫,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题写有“必戒”的训条,周公在《金人铭》中告诫要“慎言”,孔子于周太庙见到具有警示作用的欹器而脸色顿时变得严肃庄重。
刘勰认为:“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针”是中医一种常用的治疗方式,具有神奇的功效:不用毒药,不用砭石,只用微针便能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使血气在经脉中逆来顺往、出入会合、通畅运行,从而达到祛病或养生全神的目的。刘勰用针刺治病防患的功能来喻论“箴”对帝王君主具有匡错防过的谏戒作用。刘勰不仅对“箴”的名称、功用进行了解释,还梳理了“箴”的兴衰演变:“箴”兴盛于夏商周三代,周代《百官箴》留存下来的《虞人之箴》体义已较完备,至春秋,微而未绝,尚有晋国大夫借《虞人之箴》中的故事讽谏晋悼公,楚庄王以“民生在勤”的箴言告诫国人,战国以来箴文几乎绝迹,到了汉代,扬雄等模仿《虞人之箴》进行箴的创作,东汉补写而成《百官箴》,成功地实现了“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建安以后的后继之作很少有写得恰到好处的。在此基础上,刘勰阐明“箴”所包含的“警戒”的要旨、博引深刻确切的论说、简约的文辞等写作规范。
《书记》篇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古代医学经典认为,针刺可以疏通人体气血经脉凝结阻滞不通之处,使气血在经脉内通达流畅,濡养润泽全身,进而使人形神健旺。刘勰指出,《诗经》多“刺”,观诗以知政、知民情民风;《周礼》中讲的审理民间诉讼案件时,要广泛询问群臣、群吏、万民,全面了解事理民情,以有序有效地处理矛盾问题,就好像用针刺可以通达人体阻滞之处实现人体通畅乃至健康长生一样,“刺”必须能够使百官通过广泛询问世情民风、征询民情民意并使之达于君王,从而使事情得到有序解决、民情民意得到有效传达和伸张,通达政道、畅通政令,使君臣民上下通达和谐一体,政权永昌。刘勰用针刺的效果与原理解释“箴”“刺”文体名称的由来及其功能,只不过“箴”偏重工具名称及谏刺匡正的整体功效,“刺”偏重工具的使用及谏刺匡正机理。
《奏启》篇论及了“奏”这种可供谏刺的文体具有下情上达的作用。在陈述“奏”的发展轨迹时,刘勰着重述及汉代以来奏文重骨鲠、讲骨气、忠直尽节而“绳劾愆谬”的一面,用大篇幅论及奏文的体制规范和写作要求,即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有“笔端振风、简上凝霜”之气、深刻严厉之意,做到理有轨范,辞有法度,有法家的决断、儒家的文辞,不放纵伪善欺诈之徒,让声威震动于弹劾文之外,实现端直方正地“纠恶”的目标。
二、刺文的体制规范与要求
《文心雕龙》中反复出现“警戒”“规诫”“忠规”“讽怨”“怨刺”“纠恶”“匡谏”“攻疾防患”等词汇,这些是刘勰所认为的“刺”用的具体表现。刘勰所指诗、铭、箴、刺、奏、表等具有谏刺作用的文类,可以用“刺文”概括指称。综观《文心雕龙》,重点剖析与“刺”密切相关的《明诗》《铭箴》《书记》《奏启》《比兴》诸篇,可以发现,刘勰为使刺文“理有典刑”“辞有风轨”而进行了立范运衡的理论建构。
刘勰认为,“得其戒慎”是刺文的为文宗旨,即刺文应具有警戒、匡恶、规谏、谏刺、绳愆纠谬、攻疾防患等作用,刺文创作应围绕这个宗旨来进行。他进一步确立了谏刺论理的思维方法和原则:折衷。他以“折衷”为标准评鉴潘勖的《符节》“要而失浅”,温峤的《侍臣》“博而患繁”,王济的《国子》“引广事杂”,潘尼的《乘舆》“义正而体芜”,并指出它们的继作“鲜有克衷”。在《奏启》篇中,刘勰批评世人为文多失折衷,强调文章刺劾要遵循折衷原则,用中和的思维方法公允地指出问题,进行严厉正直的批评,而不是吹毛求疵、尖刻辱骂。对照《序志》篇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可见刘勰将“折衷”的方法、原则贯彻于其整体理论的自觉性。
在语言风格方面,刘勰强调刺文要简约、婉转、疏通、雄健有力。《铭箴》曰:“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在论及《杂箴》时,刘勰以文辞的简约扼要为标准进行评判,认为其“约文举要”的特点是对周武王时期铭文的很好效法。在谈到奏文时,刘勰一方面强调奏文文辞要有法家的决断,有“笔端振风,简上凝霜”的声势和威严,另一方面要“秉儒家之文”,“声动简外”“婉转附物”“辞谲义贞”,“环譬以托讽”,“‘兴’之托谕,婉而成章”,“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强调奏文要委婉巧妙、典雅合宜而非尖刻谩骂丑陋地表达正直严厉的内容。
在刺文的语言风格上,刘勰不仅吸收了传统的“主文而谲谏”,而且以针刺的解结、疏通作用进行类比。他提出“奏”以“辨析疏通为首”,一方面指出语言的明辨剖析和疏畅通达是“奏”这一文体的首要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奏”具有通过明辨剖析来疏通君王施政或信息传达方面的阻滞不畅的目的与功能。在评赞贾谊《务农》、晁错《兵事》等奏文时,刘勰又指出文辞的“通畅”是奏文的基本“风轨”。《铭箴》篇评鉴秦始皇命李斯在泰山等处做的近于铭文的刻石时,称其“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比兴》篇强调通过“比兴”的手法使文辞具有流畅通达的美感,并借“《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强调“刺道”和“兴”的密切关系。《文心雕龙》广泛地透露出天人合一、万物感应、同类相感相契以及感应兴发的理念,尤其在文辞疏通之美上,凸显出刘勰所具有的从作家之才到文辞之美的同类感应传递和兴发调节观念。
《才略》篇在辨析作家之才与作品创作关系时,针对比兴托义的诗赋,刘勰指出:“张华短章,奕奕清畅”,“潘岳敏给,辞自和畅”。他对刚毅爽迈、不畏权势、直言劝谏的孙楚评价说:“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针对庾亮表奏、温峤笔札,刘勰评鉴道:“靡密以闲畅”,“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王运熙在解析《通变》篇时也指出,“掌握变化、通畅不停滞的作文之理,方能持久”,认为刘勰在继承和革新关系上是秉持着通畅流通的观念的。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曰“持针之道,坚者为宝”,强调针刺时秉针要坚固、刚强有力。与此相应,刘勰认为,刺文在阐发用于讽谏的理义情志时,要不畏强御、独立不惧,正义气势流于墨中,声势威严震于文外,要将作家内在积滞郁结的耿介、愤懑进行刚健有力、正直不惧的宣发。用于谏刺的正直内容,需要“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般刚健威严的文辞,需要用像宝剑那样锋利、剧毒鸩酒那样猛烈的语言来表达。刺文需要用雄健有力、刚强严厉的文辞风格,来保障其劝谏纠恶的说服力、威慑力。既追求文辞表达的委婉雅正,又强调文辞气势的雄健严厉,这种要求看似矛盾,实则正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所秉持的、亦为刘勰所强调的“刚柔并济”之美,是刘勰“唯务折衷”思维方法的典型体现。
在刺文语言表达方面,《文心雕龙》以直为贵。《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曰:“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正指直刺”为针之宝道,能使针刺发挥调节血脉祛病养生的神奇功效。从针刺之道类比而来的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以正直为贵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奏启》曰:“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奏文以直为贵,臣子不能考虑自身安全,上奏帝王时一定要讲正直的话。刘勰对传统的忠直谏刺和“矢言之道”深以为然并自觉发扬,称赞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正直豪率、不畏权势之风,称颂应璩《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对应璩继承建安文学理义正直、文辞委婉、独立不惧的风骨大加赞赏。《文心雕龙》还在《铭箴》“赞曰”部分强调了刺文对于正直的内在要求:“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警乎立履。”要铭记铭箴文的警戒之言,秉持其中正直的勉励,以警戒自己的行为。刘勰详细论述了在文章中树立正直的方法:“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奏启》篇还谈及作家阐发正直理义的内在动力:“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明诗》篇称赞两汉五言冠冕之作“直而不野”,认为它们在内容、品格上是正直而不粗野鄙俗、不浅薄的,肯定诗歌在谏刺方面不虚美、不隐恶,直面问题之所在,发扬先贤圣典忠直劝谏精神,委婉刚健地表达雅正、正直的情理的优秀传统。“直而不野”“辞谲义贞”显示了刘勰“唯务折衷”的理论方法和遵守儒家忠直雅正传统的文学观念。
“确切”是刘勰对刺文所表达的理义情思的要求。《铭箴》篇曰:“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箴文是为纠过防失的,所述理义情思要准确切至。为了做到“确切”,“笔”类刺文在取事用典时必须核实、明辨,即《铭箴》篇所谓“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奏启》篇指出,奏文要“以明允笃诚为本”,理要“切至”。刘勰认为,“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要将实事求是的坚强正直的志意融入文章,通过广博的见识学识讲透道理,要引古论今,通过整理繁杂材料抓住问题关键,更要“使理有典刑”“总法家之裁”“无纵诡随”,即正直刚健地做到理有规范、是非有决断、诡谲欺诈无纵容,从而达到切至的体制要求。刘勰对于《诗经》那样的有韵之“文”,仍然有“确切”的要求,只是这种“确切”与无韵之“笔”的表现不同,要求“情必极貌以写物”,“‘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韵文类刺文的“确切”体现在,极力刻画形貌以表现事物,用切合相似之处来说理,用事物微妙之处来寄托情意,通过周密全面地观察事物,努力寻找差异巨大的事物之间的切合点,模其形拟其神,以小见大,以浅见深,实现“神理共契,政教相参”,达到一种诗意的“切至”。
刘勰认为,用于谏刺、宜于政教、合于雅正的刺文在行文时要深刻严肃。《奏启》言:“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礼》儒墨,既其如此,奏劾严文,孰云能免?”《铭箴》也说:“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于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刺文应该吸收继承“矢言之道”深远宏大的特征。正是以旨意“深刻”为标准,《明诗》篇提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所谓的“深刻”是有限度的,批判、谏刺要深入骨髓,但也不能有失公允、谗言伤人。
刘勰不仅将以针、刺为代表的医事、医理通过类比的方法引入文论中,形成刺文理论,而且将其用于纠治“文”的声律之病。《声律》篇在论及文字声音搭配中出现的音节不和谐、拗口等不符合声韵规律的毛病时,提出解决办法:“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在中医针刺取穴治疗的方法中,有循经远道“反”治法,具体有“左病右治,右病左治”“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中,傍取之”等。如《素问·调经论》:“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素问·缪刺论》:“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灵枢·官针》也说:“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缪刺、巨刺这些方法的治疗功效已为现代中医治疗临床验证。中医针刺治疗这种奇特的“逆”“反”思维模式,神奇地出现在刘勰的文论创建和话语理论系统。
由上可知,《文心雕龙》从为文宗旨、思维方法、语言、声律、修辞、文体风格等多方面为刺文制定了体制要求和写作规范。这种刺文理论的构建增强了写作的政教传道功能,更使谏刺精神、正直传统、心系天下的士子使命在写作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针道(疗人)、文道(辅政)、治道(救世)相互融通
《文心雕龙》中明显存在着文(为文)可以发泄心中郁结烦懑,具有舒展畅通身心僵化阻滞功效的文学治疗思想,同时也对作家的创作原则、创作时的情志心神状态有着相应的规定。刺文创作同样具有发泄心中郁结烦懑、舒展畅通身心之僵化阻滞的功效,刺文也是通过自身和谐从容的内涵、形式感染人、启发人、劝诫人,从而发挥其谏刺、纠恶、防患的政教、社会功用的。文道与针道相通,针刺对医生身心状态的要求和《文心雕龙》对作家创作的身心要求恰相契合互通。《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征四失论》论及医生治疗中存在的身心方面的过失,其中有:“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郁结、阻滞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也是文学创作治疗的对象。这不仅成为众多作家自传式叙述的内容、创作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文论家阐释、论述的理论命题,更成为诸多有社会、政治抱负和责任意识的文人志士拓展引申的话题。其拓展引申大致朝向三个方面:一是以医生诊断疾病的眼光看待社会、自然、政治、文化、风俗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病喻”之。二是自然灾难、社会战乱、政治生活中的挫折失意等“病因”成为文学佳篇诞生的源泉。三是作家、文学将以文辅政、泄导人情、针砭时弊、疗救社会疾病作为崇高使命。
早在先秦时期,文章对社会的谏刺作用已受到重视,如季札观乐以知政、提倡雅乐以利政化民,《诗经》的观风、讽刺功能,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等。从刘勰的刺文论可见,他对文章规劝人生、谏刺社会的功能认识很透彻,并且超出了比喻,直接打通了针刺之理、文学谏刺之道、治世之道。

刘勰刺文论所“刺”的对象包含人、社会、政治、风俗、道德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综合性。刺文论是刘勰文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创造性地以针刺之理譬喻刺文之道,丰富了《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增强了其理论话语的生动形象性,开阔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这一理论对于后世文学“人化”批评模式的形成以及借医理喻论文理批评方法的兴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