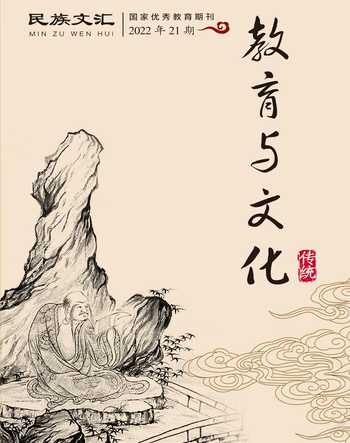笑声的价值
摘 要:一部写实戏剧,尊重生活是第一位的。让舞台和生活保持一致,既不刻意放大也不强行限制,不为了悲伤而悲伤或为了严肃而严肃。如果真的发现哪一处滑稽可笑,那就让观众笑出来;如果此刻需要观众和人物一样面对前所未有的恐惧,那我们就将它极致化,让观众对剧情感同身受;当所有的叙述都清晰有序,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可以将剧作家或二度创作者希望借着人物和事件所表达出来的观点通过某种流畅的不生硬的方式流淌出来或呈现出来。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握总体的规定情境和那些特殊的色彩(包括惊悚或喜剧)所产生的积极和负面的效果。
关键词:悬疑剧、规定情境、喜剧契约、文化自觉、
不少《无人生还》的观众,尤其是在近几年走进剧场观看这部戏的观众,经常会在会员活动或是线上向我们提问——这部戏在首轮演出时就有这么多喜剧效果吗?毕竟这是一部悬疑惊悚题材的作品。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确实引发过我的思考。
笑声的价值
坦白说,在2007年首场《无人生还》演出时观众席里出现的笑声让我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把这部戏给搞砸了。因为最初排练时真的没有想到这部以悬疑、惊悚闻名的戏会被呈现出那么多的喜剧效果。也许因为那时的我缺少经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对舞台场面的判断能力还不够。同时,也是因为当时在舞台上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这种既情况严峻却又能有许多喜剧色彩的戏,即使有一两个色彩人物,也不会出现那么强烈喜剧场面。不过,也要感谢这部戏,在后来执导的那些戏悬疑剧中我深谙此道,自己也没意识到的幽默天性就这样被优秀的剧本挖掘了出来。
在《无人生还》中不但有喜剧场面,甚至还有整场都充斥着尴尬和滑稽氛围的段落,比如在三幕一场停电之后大家点起蜡烛的那一场,仅剩的五个“印第安小瓷人”借着烛光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多动一下,生怕下一个迎接死神的就是自己。然而在这样的规定情境下,神经濒临崩溃一触即发的医生和一直想用满足食欲来缓解紧张的私家侦探,以及提出玩一个名叫“怀疑”的游戏的玩世不恭的上尉,三人组织起来的喜剧关系和场面让观众可以从戏谑讽刺地角度来进入这场戏,这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慧所在。以前我们学习到的,看过的喜剧都是市井生活、家长里短,没有涉及到至少不会去呈现善恶生死这样严肃的内容,所以《无人生还》给观众包括我们都带来了很新鲜的体验。在《无人生还》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这样一类风格的戏。就像后来我导演的艾拉·莱文的惊悚悬疑喜剧《死亡陷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一度,我心目中最好的作品就应该用一个喜剧的外壳去包裹那个严肃的主题,我甚至希望所有我导演的戏都可以如此。不过事实上不是所有优秀的戏剧都那么绝对,也不可能那么单一。但由调侃和戏谑的段落所展现出来的喜剧色彩确实存在于许多并没有被称作喜剧的严肃戏剧中。就像近些年我导的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或同是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它肯定就没发被简单地套在一个喜剧的氛围里,更没有在某种极端规定情境中的戏谑场面。可在这样的悲剧中却有许多台词或人物的行动能非常自然地引出观众的笑声,没有人怀疑它们的悲剧性,但也没有必要在看一出悲剧时就必须一直哭丧着脸,在我看来这来自剧作家的观察,也是某种创作自觉。生活本来如此,既会跟你开天大的玩笑,也会在点滴之中给你面对明天的小光亮,让你知道如果不可能一直哭下去,那就往另一边走——笑出来,即使这些笑或积极或矇昧或苦涩或绝望,这也是形成喜剧的重要内核之一。契诃夫的《海鸥》无疑隐含着巨大的悲寂,但他自己称其为喜剧,他向妻子抱怨,“哭?他们为什么哭?我写的难道不是一部喜剧吗?”在2010年,我第一次去英国看戏,确实就像我们想的一样,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有让观众轻松一笑的地方。甚至有时他们会刻意如此,有的演员、有的角色着意夸张的表演就是為了让观众不要始终沉浸在某一个情绪当中,让观众可以保持清醒。人们来剧院看戏可以得到悲伤和严肃,但他们不是为感受悲伤和严肃而来的。就像生活中有些人就是喜欢逗人开心,哪怕是在很糟糕或严峻的境况下,《无人生还》里的隆巴德上尉就是这一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写实戏剧,别的一些类型,比如荒诞派本身就破除了舞台上的生活,也破除了戏剧性和生活逻辑,那么它本身的无意义带给人们的荒诞可能已经足够幽默了,只看观者如何汲取和感受。
其实,除了没有想到会有人笑,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叫”。剧中的“尸体”被惊雷和闪电照亮的那一瞬间,全场惊叫,叫声远远盖过了舞台上女主角发现尸体时发出的尖叫声。说真的,首演时观众的叫声把我吓了一大跳——他们在叫什么?难道是因为现场的画面?事后想,如果当时我作为观众看到这样的场面可能也会被吓得叫出声来,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看戏被惊吓的经历,所以在创作时自然也预想不到观众会有如此的反应。排练时我们只是跟着规定情境尽可能地将气氛极致化,剧本里提供的是“停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1943年这个戏在伦敦首演时,舞台上有三束聚光灯形成的光柱打在演员身上,但我还是这样的呈现还不够极致。外面是暴风雨,能见度本来就很低,于是在处理这个场面的时候,除了室外雨水的一丁点儿反光之外我们只模拟了三根蜡烛可以提供的照明光亮。当蜡烛被拿下场之后,自然就剩一片漆黑了。我不喜欢演员在舞台上打破假定性去表演,会使观看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于是在一片漆黑中,几位演员在真实的烛光照明下,寻找消失不见的“法官”,于是本段开头所说的那个场面便诞生了。这是一个惊悚场面无疑,但我们当追求的确实是叙事的真实性,没有想过要刻意去吓唬观众。
喜剧的色彩和场面也是一样,具有喜剧感的人物色彩,令人尴尬的欲盖弥彰的行为,陌生人之间的社交障碍,人物在强刺激下的应激反应,尴尬讽刺的场面等等,在剧本提供给我们的优良土壤里,我们做的只是忠实地呈现。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从叙事角度出发去创作的,才会让舞台上没有那些画蛇添足的东西,场面才那么可信,因此不论是可笑还是可怕都那么真实。这也为我之后创作此类场面划定了一个原则,因为有时当经历过某种热烈的观众反应之后,演员乃至导演都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那些效果,进而夸张放大,以至本末倒置,而且有时很难控制,不好察觉。所幸我们有过之前的这种从未知到发现的过程,反而会让我更清醒。无论是调整还是再挖掘,一切遵循剧本叙事的需求,是让一个反复上演十五年的戏不会像重复使用加载多次的软件那样产生垃圾缓存的唯一途径。
在这部戏刚开始演出时,甚至直到这几年都有观众在看完之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喜剧点,认为这样的笑声会让作品变得廉价。也有些表示在看小说时没觉得有什么好笑,没想到话剧竟然“加了”那么多笑料。还有一些更传统的话剧观众或严肃的推理迷们认为那些惊悚的场面会让观众觉得这只是一部寻求刺激的戏而忽略了它对人性的揭示。真的有人问我“难道这部戏的目的就是为了吓人吗?”或者“为什么要把那么严肃一部戏排成一个喜剧?”。
观众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这部戏首演时产生的那些“没想到”让我不禁去思考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戏出现过吗?即使没有完全这样呈现,但这样的文本我相信是被演出过的。可为什么在西方舞台上很普遍的呈现我们的观众却如此陌生?而我们的生活并不见的就比其他别的地方更严肃或更缺乏幽默感。思考之后我发现是我们的打开方式不对,并不完全是哪一种戏横空出世了,也不单单是第一次被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思维定式和惯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曾经把头脑固化得太单一了。过去,在我们的想象中,被界定了某一概念的东西就只能用一种方式去理解。其实即使是生活,在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想象它可能有别的打开方式,而真的发生时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被告知学习就是辛苦的,不可能有那么多快乐,事实上孩子天生有求知欲,原本它就可以是快乐的,取决于怎么看待这件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文本本身就有很多幽默的语言,她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女性,只是那時我们不知道这些可以笑或值得笑,包括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也一样在经历这种再发现,我们在看小说或读剧本的时候,最多就是说这个人物很愚蠢,这个场面很尴尬,但当它没有被称作一部“喜剧”(哪怕是晚会的“小品”)时,很多人就不会笑出声来。但事实上,喜剧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尴尬”,当时机恰到好处时,它很自然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就像生活真的来了,并不会是我们以为的某一个样子一样。但如果在看这个戏的名字时,就已经联系到了某个定式,那么这些效果就有可能都变得意外了,尤其是一些更“了解”戏剧的观众。另外一旦上升到文化审美的范畴,我们便不太被主张在严肃的事情里看到荒诞滑稽的一面。而在西方人们更容易接受讽刺,悲剧深沉喜剧低廉的界限也更早被打破。这无关对错,仅仅是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
就我的实际工作来说,尊重生活是第一位的。让舞台和生活保持一致,既不刻意放大也不强行限制,不为了悲伤而悲伤或为了严肃而严肃。如果真的发现哪一处滑稽可笑,那就让观众笑出来;如果此刻需要观众和人物一样面对前所未有的恐惧,那我们就将它极致化,让观众对剧情感同身受;当所有的叙述都清晰有序,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可以将剧作家或二度创作者希望借着人物和事件所表达出来的观点通过某种流畅的不生硬的方式流淌出来或呈现出来。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握总体的规定情境和那些特殊的色彩(包括惊悚或喜剧)所产生的积极和负面的效果。
不论如何,《无人生还》以及它原著小说都是一部通俗作品,是一部悬疑小说和悬疑剧。无疑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人性洞察敏锐且诚实,但她采取的方式原本就是用一个引人入胜的悬疑故事来作为依托,让读者或观众自己去体察和捕获,我们一定要将它形而上的部分单拎出来或拔高,反而会乏趣无味。其次,每个人对幽默的敏感度不一样,承受刺激的限度也不一样,对问题的思考也完全不一样。我一直主张忠实的说故事,而能够从故事中得到什么这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经历和思维方式。我不介意有的观众是来寻求刺激的,也不介意他们看完之后得出了和我们给出的主张完全不同的想法。剧场和戏剧的功能本就不是单一的,不同类型的戏就更不一样。在我看来,在一部以讲人物,说故事,不完全脱离生活的作品中,那些具有色彩,可以增加作品可看度或更好地吸引观众的场面对于观演不是一件坏事,“笑”或“叫”包括“凝息屏气”和“流泪抽泣”本来就都是观众投入的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它的呈现在这个戏的规定情境和风格内,符合生活,我们就不要去回避它,而要去控制和利用它。如果一个戏仅仅着力去表现某一主张或某一思想,会拦住很多不同需求或不同观点的观众,也会让戏剧丧失光彩。无论是将它看作一部悬疑剧,还是将它看成一部给出更高命题的作品,“雅”或“俗”,原本就应该被更开放地看待。
这可以说是这些“观众席里的笑声”就戏或就《无人生还》本身所产生的价值。而在这部戏之外,它还引发了我另一种思考,那就是关于“观演契约”,更准确来说是关于“喜剧契约”的思考。
喜剧契约
在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开始表演或呈现一场戏之前要和观众签订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在观众开始观看表演时就要生效,有得更早,要从走进剧场时就开始。它的建立有时作用于风格,比如荒诞派的戏剧,经常会用反复使用无意义的台词、不合逻辑的行为,加以演员表演的信念感来向观众证实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确实产生于这个看起来荒唐的舞台情境,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并使之体察这些荒诞行径背后的意义。而在写实戏剧的导表演中它可以表现为向观众明确交代这一场戏的环境,人物前史和当前的状态,在认可这些的情况下,观众就更容易相信演员的表演,同时产生同理和共情。一旦契约被建立,观众就会像遵守约定一般顺利地理解你要表达的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导演和演员对规定情境的重视就是建立这种契约最重要的部分。但还有一种纯表演上的契约,我叫它喜剧契约,它的建立可以独立在规定情境之外,不像惹人悲伤或引人思考这些很大程度来自于文本的给予,它是完全可以依靠演员表演控制的。也就是我想要建立这个契约的时候它就可以被签订,而我不想要的时候它就可以完全不存在。反之,当面对一个喜剧时,如果没建立好喜剧契约,可能会一点喜剧效果都达不到。它是一个导演和演员依靠能力、技巧和生活经验去控制的手段。具体说的话,就是观众要知道现在可以笑,他才会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在参加一个极严肃并且事关重大决策的会议时,忽然有人因为肠胃蠕动,发出了一个不雅的声音,场面无疑是尴尬的,一般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哈哈哈地笑出声来。但如果这时与会的领导笑了出来,那么很有可能大家都会跟着笑起来,原本觉得荒诞但不敢笑出来的人也不用再憋着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喜剧契约”的生活化呈现。
这一点在《无人生还》的某几个人物和某些场面上非常突出,比如阿姆斯特朗和布洛尔这两个角色。布洛尔在和大家介绍自己时一直强调自己姓戴维斯,2007年首轮演员在第一次演的时候就用了非常夸张的表演。当然从人物来说,他为了强调布洛尔想要掩饰自己原本私家侦探的身份,但却达到了我们一开始没有料想到的喜剧效果,由此布洛尔身上的喜剧色彩便被确立了,这完全取决于表演。同时,原本阿姆斯特朗身上最容易让人注意到的是紧张和局促,但由于他在和布洛尔刚碰面时因为布洛尔突然大声介绍自己差点儿紧张地被刚刚送进口中的药呛住,使得这一组人物关系变得非常滑稽,阿姆斯特朗的紧张和局促也变成了他身上容易引人发笑的地方。这其实也是我们发展出来的一段戏,被药呛到这一段剧本里原本并没有,是我们在排练中赋予的,原本是为了强化大夫神经的紧张,但这也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喜剧契约。于是在那之后,他们俩的一言一行都会让观众觉得可笑,就好比生活中大家都认可的那种经常会闹笑话的人。但我们做过实验,如果要求演员演得非常严肃,台词和行动哪怕一摸一样,观众却一丝笑声都不会有。最明显的是隆巴德在三幕一里有一句嘲讽阿姆斯特朗大夫的台词,“直到这个无名氏先生的出现,你才发现金字塔是沙子堆的”,这句话只有在说得像句笑话时观众才会觉得可笑,否则他们即使听懂了意思,也几乎不会笑出来,因为当时大夫正在说自己如何逃过法律的制裁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神经科医生,气氛并不好笑,所以他们需要得到一些暗示。阿加莎的本意也是要让隆巴德打破此刻大夫表现出来的看上去像是承认罪行一样的局面,一是为了凸显他的人物个性,二是强化出剧作者本人对阿姆斯特朗因醉酒致病人死亡这件事的态度,对阿姆斯特朗精神紧张的癫狂状态我们要给的不是同情,而是恶有恶报的讽刺。因此隆巴德这句台词的嘲弄意味就必须被强化出来,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观众笑出来,这里的笑声就是嘲弄的外化,把观众在观演之中的反应纳入表演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它为阿姆斯特朗的气急败坏做了铺垫,以至于会说出“收起你那无聊的玩笑吧,我要杀了你!”这样的台词。试想一下,如果他面无表情地平淡地说出了那句话,那气氛除了尴尬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一个善于冷嘲的人,如果说的不是一个冷笑话而是一个冷场的笑话,那可真是太尴尬了。而且他会显得多么冷酷而无趣,哪怕是小说结局,他也不能是一个无趣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活到最后。所以他必须要真的说一句“笑话”,观众才会真的笑,后续的那一切才可以被完成。
有时喜剧契约能否建立影响还不止是某一个场面或某一个人物,甚至还会整场的叙事结构。还是拿刚才的那一场戏举例子,前一场结尾时连续死了两个人,发电机也停止了工作,气氛剑拔弩张,谁也不愿说话,都谨慎地观察着其他人,观众也随之严肃起来,大气不出。要知道这场戏差不多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观众始终处在一个沉闷紧张的状态中,很快就会疲沓觉得无趣,因为毕竟不是他们处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是在观看别人的困境。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局面,在长时间的紧张或严肃的氛围中,有意识的营造一些喜剧感,所形成的反差会在观演上起到非常积极作用,也就是欲扬先抑。而且就情节本身也是一样,如果某一局面不被打破,那就无法推动剧情。剧本安排的还是隆巴德,因为打破局面来找出暗藏的凶手正是他的内心任务。于是他暗合着当下的局面改编出了一个新版的童谣——“五个印第安小男孩儿,相互张望排排坐,等着上天降灾祸”。但这句话在不同的表演中效果很不一样,此时演员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就是剧本里隆巴德自己随后的那句台词“缓和一下气氛嘛,别那么死气沉沉的”。但如果这句玩笑开得不好,说完之后气氛依然死气沉沉,那角色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我们有过一场演出,演员的表演用力过猛,结果同样抑制了这句话本身会产生的喜剧效果,轻松的调侃本来就是幽默的基础,这依然是一个建立“喜剧契约”的问题,生活中也有很多不会开玩笑的人,尤其是不会嘲讽,所以演员必须了解生活,体会生活,尤其是喜剧。接着局面往下发展,观众得到了一个更严肃的暗示,于是布洛尔因为紧张和饥饿一直想去“吃点东西”,阿姆斯特朗被吓丢了魂草木皆兵,这些都变得不那么容易笑了,我们最终希望欲扬先抑的目标成了泡影,观众在法官中弹的那个大场面中得到的刺激也就不那么大了,就像一根始终绷紧的皮筋最后失去了弹性一样,没有力量。但反之,观众不但能看到隆巴德在行为上非常清晰的目的,我们还能借这样的氛围使观众的神经缓和下来,等他们放松了警惕,再给他们一个猝不及防。但要完成这个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必须更严格地提醒演员注意规定情境,观众可以笑,但他们必须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环境中的心理压强始终要保持,我管这个叫“气压罩”。演员的表演绝不可以轻易地破坏这个“气压罩”,否则这部戏原本要呈现的叙事结构也同样会被打破,这又是就规定情境而产生的“观演契约”。在这样双重契约的保证下,我们才能收放自如。
这就是喜剧契约的重要性,只有在和观众达成了某种幽默或滑稽的共识后,观众才会投入共同完成某个喜剧场面。《演砸了》就是一个和观众强行建立“喜剧契约”的典型例子,尤其是面对含蓄的中国观众,这部戏是说一群九流演员在正式公演的舞台上把一出戏演砸了的故事,除了剧中的“导演”在“开演”前告诉大家他们这个团队是怎么各种“砸锅”的之外,没有任何“戏中戏”的铺垫,各种舞台事故排山倒海地涌来,直接开砸。但观众对于“舞台事故”这个概念还不够熟悉,很容易莫名演员们在演什么。于是我要求剧中饰演“导演”的演员在刚开始的那段话时就要用喜剧的表演方法,利用节奏和人物的尴尬来向观众暗示这群九流演员随时有可能会将这个戏演砸,而其余的演员则被要求非常夸张的表演。于是观众在第一个舞台事故发生时就明白这个戏大概会是什么走向,这就是在和观众建立“喜剧契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观众越来越能接受《糊涂戏班》的第一幕了。我记得很清楚,同样的戏,在十几年前第一次上演时,在第一幕铺垫里观众几乎睡著,更不用说笑了。其实《糊涂戏班》的第一幕非常有趣。我认为这个变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从新版《糊涂戏班》上演的第一场至今,无论是我们的宣传还是看过的观众都在不断地对外宣传这部闹剧有多好笑。于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带着一种要来好好笑一笑的心态走进剧场的,所以他们才能在相对笑点较少的第一幕中得到乐趣,就连新版的海报也比过去更强调和暗示这个戏的戏剧氛围。还有我之前导的《蛛网》,它阿加莎创作的唯一一部正真意义上的喜剧。首先我要破除观众原本的观点,宣传时就强调这是一部喜剧,只字不提它的悬疑性,接着海报的拍摄我们用了非常夸张的慢动作定格,在一个极其混乱的局面中,每个人都处在失控之中。就像我前面说的,宣传必须给出正确的引导,在喜剧中,就是从宣传角度来建立“喜剧契约”。
现在的观众结构中年轻观众占了主体,他们更容易投入,也更反感生拉硬拽的说教。他们更需要生理刺激,无论是笑还是叫。只要创作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不迷失,那就可以通过他们更舒适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年轻的观众有时更愿意思考,而且是用更开放和包容的头脑去思考。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打开方式(进入方式)的问题,他们更愿意自己探索自己抓取,更愿意投入地去感受,继而去思考。从这个角度说,近年在需要进行观点或信息输出的方面,大家都做的越来越好。我们必须要考虑时代带来的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因地制宜。
我在刚排这部戏时甚至忘了自己原本也是个年轻人,注意力几乎都放在这部戏最后是否有罪的“终极审判”上,因为那里从剧本内涵来说应该是观众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刻,也是叙事上最大的逆转。但我仅仅从整部戏的结构和主题出发,忽略了观看者的思路和感受,更没有期待观众会产生什么生理刺激,但事实上他们在获得心理压力之前,应该先有生理上的压强,这样的感受更真实。由于我们对艺术的传统审美和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之前经常认为生理和身体上的刺激要比精神和心理上的感受低廉,是不高雅或浮夸的,因此创作者们往往不齿于逗乐和惊吓。西方一直有拿死亡鬼怪和滑稽行为做为创作基础的习惯,比如惊悚剧和小丑表演,都属于简单的生理刺激,这是文化发展历程不同决定的。其实这种生理刺激在今天的创作中所引申出来的意义自然可以被看作“心理的脆弱”和“从共情出发的讽刺”,也就是“我掌控不了”和“有人比我更惨”,也就是观众从自身出发本能感受到的东西,它们不能说是创作的核心动力,也不是创作的全部,但都会增强观众在主动和被动的投入性。写实戏剧是一个需要依靠观看者的感受来完整呈现的创作过程,我们需要考虑真实有效地感受过程,主动投入远比被动欣赏有效。
不得不说,我们能够有此认识得益于我们迎来一批更年轻也思维更独立的观众。从某个层面来说是的,不止觀众,创作者们的平均年龄也比过去年轻。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的环境,这是一个量变逐渐形成质变的时期,曾经那些有远见的前辈们为我们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多元。现在的话剧早已不是单纯为了创作者表达某一观点或诉求而存在的了。近二十多年,众多话剧人为了让话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努力,甚至在未来不久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可能都不足够,因为现在就连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地被挑战。当科技让生活再一次发生巨变的时候,可能已经成为习惯的某种生活方式立刻就会随之变化,就像现在人们的通讯习惯,消费习惯,接受信息的习惯都是上个世纪甚至十年前不敢想象的。每一门艺术都在更积极地寻找它的立足点。
坦白说,能够处在一个正在发展的环境中对于创作者来说要比处在一个已经发展稳定环境中更幸运。我们在伦敦西区看戏时发现那些在老牌剧场里常演不衰的商业戏剧或新排演的经典剧本吸引的观众年龄层都普遍偏大,我们笑称走进了“银发剧场”。相比我们的观众年龄结构要丰富并且年轻的多。那些走在思想前沿的剧场,诸如杨维克剧院、阿梅达剧院和代表舞台呈现最高水准的英国国家剧院会好很多,那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可能行业覆盖率还是比我们的观众要低。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看戏不是业余时间的唯一选择了,那些拥有优秀戏剧传统,早就把戏剧作为生活方式的国家首先受到了挑战,年轻人们纷纷选择了更为新鲜更为便捷的娱乐方式。从开放的角度来看这些可能都是新的机遇,但就戏剧观演本质和发展而言可能都算不上令人欣喜的事,银发剧场、明星票房、线上播放都是随之产生副产品。而我们的幸运恰恰是舞台事业的上升期和信息时代同时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走进剧场是经过自主选择的,自主选择就具有更多的能动性。
2011年,我们邀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外孙马修·普理查德夫妇来上海观看《无人生还》,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看戏,看完戏之后他非常激动,他为克里斯蒂的戏剧能够在中国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而感到高兴,尤其是看到了那么多年轻的观众。在事后的交流中他问我们是不是因为这部戏的题材才会吸引那么多年轻人来剧场。听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意外,我们表示在我们的剧场里,无论是什么样戏都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来观看,我们的观众主体是就是中青年,来剧场看戏是年轻人业余生活中很普遍的选择。而且我们的从业者也都很年轻,很有热情,这让他既惊讶又欣喜。那次交流让我们陪感荣幸,荣幸处在这样一个可以选择也能够被选择的时代。
拥有选择权和被选择权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调,和过去相比,年轻人行为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再盲从,他们不会像绝大多数他们的父辈一样集体在家看手机,也不需要从已经很饱满但却固化的某种生活模式中跳脱出来。他们处在物质丰富且精神发展的环境中,按需选择成了新的生活方式。选择本身也意味着不僵化,这给了我们机会,并且是持续存在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被轻易舍弃。当然也带来挑战,当我们尽可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之后,我们会经历更严格的被选择。因此我们需要给观众制作更精良,同时内容更丰富,思想更多元的戏。我们既需要顺应观众的需求,同时又要更高质地让观众在剧场得到从别的渠道得不到的享受。立足于剧场观演的本质来给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并借此来引导观众对世界对自身对他人新的观察和思考。这是自新世纪开始乃至未来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戏剧人的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英)劳拉·汤普森 上海译文出版社
《Agatha Christie,A LIFE IN THEATRE》 (英)Julius Green
Harper Collins出版社
作者简介:林奕,女,1982.01.02生人,汉族,福建惠安人,大学本科,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国家二级导演,研究方向:戏剧导演,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