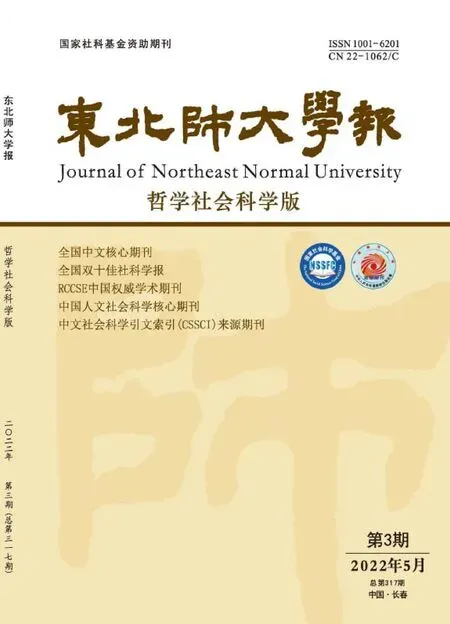一份杂志的历史使命:关于《新小说》基本事实的研究
刘 畅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中国晚清“新小说”的兴起综合了多种社会因素,其中近代文学杂志的兴起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具备近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的小说杂志……《新小说》”(1)郭浩帆:《中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它的创刊与发行在中国现代小说兴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晚清“新小说”的变革与发展,梁启超在文中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新小说”的历史,引发了1902—1911年间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2)根据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从1840年到1911年期间共发表原创小说1 805篇,翻译外国小说1 036篇,其中1902年到1911年共发表原创小说1 595篇,翻译外国小说988篇,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小说在这一阶段的繁荣。。这期间,中国小说的历史地位被首次拔高,小说质地发生重要改变,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重大改变,在数量与质量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最繁荣的时代”(3)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由此可见《新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在中国小说近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新小说》的创刊与发行
晚清小说历经多年的锤炼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标志性事件,即《新小说》杂志的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也是中国第一个推广新小说理念与作品的小说报刊。无论对于中国小说界还是传媒界,《新小说》的创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开辟了中国晚清小说的新局面。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认为:“研究小说的专门杂志,应该了解杂志的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可以说是研究的基本项目之一,不用赘述。”(4)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集稿》,陈薇监译,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207页。对一份杂志出版时间的考古学式研究,一方面可以确定这份杂志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可以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杂志的特色与影响,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实现历史地审视杂志的意义与价值,寄予最为翔实客观的评判。因此,对于《新小说》的研究,首先需要厘清这份杂志的出版日期、印刷地点、发行情况等基本问题。
《新小说》的创刊在事实上基本清楚,它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公元1902年11月14日)的日本横滨,《新小说》创刊号上的编辑兼发行者署名为赵毓林,实则背后的创办者与主持者为梁启超。《新小说》前后共出版24号,其中13号在出版日期上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以往学界较为认可由上海图书馆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书。这是一部记录我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较为权威的工具书,其中清楚地标示了《新小说》每一号的出版日期,但无论是《新小说》杂志标明还是未标明出版日期的刊号,其间的考据显然不足以支撑结论,存在诸多纰漏与问题。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曾在《〈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一文中对《新小说》的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很多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考据依据,但是部分仍然缺乏权威根据。根据中国学者陈大康《〈新小说〉出版时间辨》、姜荣刚《〈新小说〉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考辨》等最新考据,我们基本可以将《新小说》每一期出版时间大致确定如下,虽然在科学性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新小说》创刊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
《新小说》第二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902年12月14日;
《新小说》第三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
《新小说》第四号,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1903年6月10日;
《新小说》第五号,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
《新小说》第六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
《新小说》第七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903年9月6日;
《新小说》第八号,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7月;
《新小说》第九号,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1904年8月6日;
《新小说》第十号,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1904年9月4日;
《新小说》第十一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04年10月23日;
《新小说》第十二号,光绪三十年十月廿五日,1904年12月1日;
《新小说》第十三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
《新小说》第十四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
《新小说》第十五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
《新小说》第十六号,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
《新小说》第十七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期间,1905年12月1日至1906年2月期间;
《新小说》第十八号,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3月;
《新小说》第十九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
《新小说》第二十号,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左右,1906年5月8日左右;
《新小说》二十一号,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1906年6月;
《新小说》二十二号,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7月;
《新小说》二十三号,光绪三十二年六月,1906年8月;
《新小说》二十四号,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
这其中第八号以及第十三号至第二十四号共十三号出版日期存在争议,尤其是从1906年第十八号开始《新小说》干脆不再标示出版时间。对于这一现象,樽本先生认为:“预定的出版日期和实际的相差太远,这个也许就成为《新小说》从第18期以后不再登载出版日期的原因。”(5)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集稿》,第216页。《新小说》在日期上的混乱主要是由于杂志经常性的出版延宕甚至停刊,而为了维护《新小说》的声誉与延续性,于是经常在出版日期上主动造假抑或故意混淆,造成时间上的模糊,令读者无法判断《新小说》是否出现出版问题。
在印刷地点上《新小说》同样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新小说》最初由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社活版部印刷,从“第二卷起迁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6)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5页。。从《新小说》杂志的标示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从《新小说》版权页的印刷所标示来看,一至四号印刷所标示“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活版部”,五至十二号印刷所标示“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民丛报社活版部”,统一标示的定价为“日本各地,日本通用银四角一册;中国各海外各埠,中国通用银四角四分”。等到十三号与十六号《新小说》的版权页被取消,仅仅在杂志封面题“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标示的定价也被简单修改为“每号定价三角半”。从版权页标示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新小说》的印刷确实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社活版部转移到了上海广智书局,但是樽本照雄先生在《〈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一文中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坚持认为《新小说》一直在日本横滨印刷,不存在出版地移师上海一说,上海广智书局只是《新小说》在中国的一个总代售处。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疑。
在期刊发行方面,由于梁启超的原因,《新小说》与《新民丛报》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它们甚至被称为姐妹报刊。《新小说》不仅仅是一份同人报刊,以宣传新思想为主,同时也是一份产业,以营利为目的。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三份报纸——《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都实行股权制。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本着利益一致性原则,《新小说》最初完全借用《新民丛报》的传播渠道。当时《新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邮递渠道,一种是派报渠道,这也是当时晚清报馆的主要传播渠道。而《新小说》从日本横滨邮递到中国上海等地主要依靠的是客邮。客邮是当时中国极为重要的海上邮寄系统,主要被西方列强所控制,因此晚清政府很难干预查禁。
由于《新小说》等报纸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等“悖逆”“异端”学说,一直以来为晚清政府所查禁。梁启超对于清政府的查禁曾回忆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庭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页。。梁启超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清政府的查禁无法限制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更无法遏制新思想的传播。但是随着清政府的查禁活动越来越严,尤其是在1902年至1905年间更是达到“疯狂”程度,当时很多进步报刊遭受一定影响。1902年由于“逮捕新党禁售新报之故”,北京“自六七月后时务新书之销路顿觉阻滞,较之去年退步殊多”(8)《中外近事》,《大公报》1903年1月30日。,1904年导致苏州《新民丛报》等书刊“竟无处可购矣”(9)《新书无售处》,《警钟日报》1904年7月13日。。但是越发严厉的查禁非但没有禁毁新报纸杂志,反而加快了它们的传播速度,清政府的查禁名单恰恰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
无论是《新小说》创刊人梁启超,还是其宣传的启蒙救国的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的思想,都引起清政府的警惕和恐慌,从《新小说》出现伊始便开始了查禁活动。由于《新小说》多采用文白交杂的语言形式,甚至直接刊发白话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其所宣传的新思想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因此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于是引起清政府的格外关注。但是清政府的查禁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对《新小说》,其查禁的结果是“假外人之力以禁《新小说》,而《新小说》如故”(10)《投函》,《警钟日报》1904年5月28日。。虽然清政府的查禁没有直接导致《新小说》停刊,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小说》的出版与发行,成为它延期、停刊的一个原因。
二、《新小说》停刊、复刊及其原因
《新小说》最初创刊规划是“月刊”,计划每月出一号,但是从1902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创刊到1906年9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停刊,其间历时近4年,先后出版2卷24号。办刊期间历经停刊、复刊、延期出版等问题。《新小说》的出版发行几乎成为晚清中国进步报刊的一个缩影,是我们认识晚清文学发展与晚清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新小说》创刊准备工作极为充分,媒体前期宣传造成巨大声势,创刊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学界的翘楚地位以及办刊经验,配之以优良的编辑工作团队,成熟的发行渠道等因素,尤其是《新小说》的办刊主旨符合晚清社会思想启蒙的需求,其倡导的自由平权思想,新世界、新国民的召唤等等,构成了晚清社会基本思想资源,迎合了读者大众的精神需求。因此,《新小说》印出后不到半个月就已销售一空,亟待加印。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是一份高开低走的报刊,在完整出版三期后《新小说》遭遇了第一次停刊。
《新小说》前三号都是每月出一期,1903年1月13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小说》第三号出版后情况急转直下,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新小说》突然停刊,直到五个月以后的1903年6月10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新小说》第四号方才出版。但是复刊的《新小说》第四号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03年1月,在《新小说》第三号出版之后梁启超便离开日本赴美考察,这是他多年的一个夙愿,以期加深对西方现代思想与现代性的了解。这次旅行对于梁启超意义重大,但是对于《新小说》却是一次灾难,梁启超之于《新小说》不仅仅是创刊人、经理人、主编与作者的身份,更是《新小说》的精神领袖。虽然梁启超将《新小说》出版工作委托给朋友罗普,但是群龙无首的《新小说》失去了前三期的办刊风格,其势迅速回落。对此,《新民丛报》曾发表《新小说》告白:
本报自昨年十月开办以来,已出至第三册,今因本报记者饮冰室主人远游美洲,羽衣女士又适患病不能执笔,拟暂停刊数月。本报体例月出一册,准于本年内续出九册,并去年三册,合成十二册,以符一年之数。事出于不得已,以致愆期,无任歉仄,此后当增聘撰述,益加改良,以副购读诸君之雅望。横滨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小说社谨启(11)《新小说告白》,《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1903年3月24日。。
由此证明梁启超的重要性,但是梁启超的远行与罗普的患病这一偶然事件就击垮了《新小说》,致使其停刊数月。从中我们更能看到《新小说》编辑部存在的一个潜在危机:人员不足,可用之人更是紧缺。可以说这是《新小说》的一个致命硬伤,一直未能解决,直到最后停刊亦与此有关。
直到《新小说》第七号出版时梁启超已返回日本横滨,于是再次帮助《新小说》,将自己连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接续到第五回。在梁启超的要求下,雨尘子的《洪水祸》又续刊了两回。至此,两篇小说在未完成状态下无疾而终。同时,梁启超还开辟了《小说丛谈》专栏,将中国小说理论从传统点评式转型到系统评论,实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新小说》第七号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创刊号的文脉,具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势,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七号之后《新小说》再次停刊。这次停刊清政府的查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现在看来应该还有更多尚未知晓的原因隐藏其中,比如编辑部内部管理问题、资金问题、营销问题、股份问题等等,当事人对此事三缄其口并未说明。等到《新小说》第八号于1904年7月(光绪三十年五月)复刊时,梁启超已远在美国,其间如何将《新小说》全权交付于吴趼人更是未尝可知。但是从第八号开始,吴趼人彻底接手《新小说》,梁启超、罗普等人与《新小说》完全脱离关系。吴趼人接手《新小说》后在办刊理念上发生很大变化,期刊开始更为注重商业效益与读者大众,使《新小说》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但是在坚持出完第二卷的12期后,《新小说》最终还是于1906年9月出版完第二十四号后停刊。《新小说》第二十四号内封登载了一则特别广告:
启者:本小说自刊行以来,倏忽数年,屡次愆期,殊深歉仄。今自本号为止,暂停发行,凡报中有未完之稿,则拟陆续付印单行本,俾爱读诸君得窥全豹。此启。新小说社谨启(12)《新小说社特别广告》,《新小说》1906年9月。。
自此《新小说》正式停刊再未复刊,但是该广告并没有明确说明停刊理由,部分研究者分析认为《新小说》的停刊主要原因在于主持者吴趼人和周桂笙被《月月小说》挖走,导致后继无人无奈停刊。从《月月小说》第二号刊登的一则“本社紧要广告,注意!注意!!注意!!!”的启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月月小说》确实挖了《新小说》的墙角,且公开告知读者聘请到著名编辑兼作家吴趼人、周桂笙二人。从这则带有做广告意味的启事中,我们可以确定吴趼人、周桂笙从《月月小说》第三号开始正式入职。二人在当时都极具影响力,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月月小说》的办刊风格,提升了报刊的质量。兴奋难掩的《月月小说》在其第二号、第三号上连续刊登了一则广告:
启者:本社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故特创为此册,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述、总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二君更注全力于本报,其余译述、撰述员均皆通才,分门著述,按期出版。内容之如何,请阅一、二期便知。诸君如欲预订全年者,将来并有临时增刊一册附送。如蒙定阅,报资、寄费赐下后,本社当妥为寄奉也。
这则商业性十足的广告,摆明了卖报纸的姿态,以吴趼人、周桂笙为主要卖点,在充分肯定二人的才华与影响力的同时点明为挖来二人《月月小说》可谓煞费苦心,“商乞再三”方才请来,同时也不无炫耀地首次表明这次挖墙脚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新小说》的停刊。吴趼人、周桂笙之于后期的《新小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离开应该成为《新小说》停刊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从《新小说》第三号后梁启超赴美、罗普生病即导致《新小说》暂时停刊来看,《新小说》的编辑部实力相对薄弱,人才匮乏,无法应对报社的突发性事件。从《新小说》第八号开始吴趼人与周桂笙入主新小说社,他们在《新小说》中的地位相当于当年的梁启超与罗普,二人的突然离职较之于当年梁启超的暂时离开对《新小说》的影响应该更大。
同时,《新小说》的撰稿人一直不够稳定,从《小说丛话》栏目作者来看:

表1
曼殊、平子、定一是主要撰稿人,其他撰稿人相对不稳定,而且每一期参与撰稿的人数不稳定,时多时少,没有稳定的创作团队是一个报刊潜在的危机。
尽管很多研究者利用各类资料对《新小说》停刊原因进行了侧面的佐证推理,但由于《新小说》停刊的复杂性,以及当时负责《新小说》的相关人士并没有明确地将停刊事宜公之于众,事后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缺乏当事人的说明,任何原因的推理证明都只能是一家之谈,难以服众。《新小说》停刊原因究竟为何,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我们也仅能通过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判断与揣摩。
三、《新小说》的栏目设置
晚清报纸杂志开始很少标示栏目。1897年10月上海《求是报》开始连载三乘槎客(陈季同)的翻译作品《卓舒及马格利小说》,且标示为“泰西稗编”栏目,这被认为晚清报刊小说标示栏目的开始。梁启超是中国晚清较早且热心于提倡栏目标示的思想家,他在1898年12月由其本人创刊的《清议报》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自己翻译的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做了“政治小说”的标示,这是我们看到的较早报刊小说的栏目标示,等到《新小说》创刊后栏目标示已成为报刊的一个必要工作,几乎每部作品都有标志以作区分。在梁启超的推动下,《清议报》与《新小说》栏目标示的方式随着报纸杂志影响力的扩大,很快引起其他报刊效法,比如《广益丛报》《苏报》《教育世界》《汉声》《女子世界》等,部分出版社与印书馆也开始为出版书籍注明标示,比如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作新社、文明书局等。自此,小说栏目标示成为报纸杂志的普遍现象,当时共有108种报刊,47家书局、报社等,共1 075篇小说有标示(13)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新小说》杂志先后共标示栏目二十四种。其中以“小说”字样为标示的栏目共13种,主要包括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语怪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札记小说、奇情小说等等。比如,雨尘子的《洪水祸》与罗普的《东欧女豪杰》被标示为“历史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被标示为“政治小说”,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被标示为“哲理小说”,卢藉东翻译的《海底旅行》被标示为“科学小说”,南野烷白子翻译的《二勇少年》与罗普翻译的《离魂病》被标示为“冒险小说”,梁启超翻译的《俄皇宫中之人鬼》被标示为“语怪小说”,等等。很多分类标示今天看来不尽准确,标示名称更是文不对题,存在为了标示而标示的现象,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当时《新小说》如同一面旗帜,它的很多办刊理念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就分类标示而言,它也开创出很多未有之标示名称,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因为杂志名为《新小说》,因此发表小说数量比重相对较高,且种类相对齐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在这些小说当中原创性小说不足,《新中国未来记》《洪水祸》《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算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大部分刊发的小说仍然是翻译小说,以翻译西方小说为主。缺少原创则令《新小说》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毕竟它应该以传播中国的“新小说”为主,而不应该以介绍西方小说为主。
同时,《新小说》还开设多种其他专题栏目,栏目设置带有一定的应时性特征,因为某位作家、理论家,抑或某种文学现象,甚至是编辑的某一偶然想法等,因此这些栏目往往在全部期刊中出现次数较少,且比较凌乱,即时出现即时消失。这类栏目主要包括论说、传奇、广东戏本、杂记、京调西皮、粤东版本、剧本等等,种类杂多不一而足,真可谓包罗万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适宜于晚清复杂多变的文学思想现状。
政治小说与社会小说为《新小说》的主要标示栏目,也是《新小说》的两个分水岭,其中又以《新小说》第八号为分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期。从《新小说》第一号开始到第七号结束,这一时期《新小说》主要以发表政治小说为主,《新小说》创刊号刊登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与玉瑟斋主人《回天绮谈》,在杂志中直接标示为“政治小说”。从《新小说》第八号开始,“政治小说”这一栏目标示再未出现,而“社会小说”的栏目标示则是首次出现于《新小说》第八号,成为《新小说》首创的标示栏目。从第八号开始,社会小说成为《新小说》主要标示栏目,一直延续到《新小说》第二十四号,共占据了17期。《新小说》第八号集中刊发了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和颐琐的《黄绣球》三篇“社会小说”,可见这一小说栏目成为吴研人的《新小说》重点推出栏目。
可以说《新小说》第八号是该报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梁启超彻底离开《新小说》编辑工作,将刊物全权交给了吴趼人,吴趼人改组《新小说》,请来朋友周桂笙,编辑主体彻底发生重大变化。吴趼人开始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改革《新小说》,且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了《新小说》的办刊理念与小说观念,不再突显小说的政治宣传功能,更为关注社会历史等消费性、娱乐性强的小说题材。在《新小说》第八号上刊发了《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也被翻译为《催眠术》)和《新笑史》等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和写情小说,且极力推出“社会小说”。《新小说》第八号起主要标示了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法律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等,政治小说彻底淡出《新小说》。栏目标示从“政治小说”向“社会小说”的转变,恰恰反映了《新小说》开始从关心政治转向世事人情,商业性、通俗性的市民化倾向更为明显。同时,周桂笙开设了专栏“小说丛话”,开始持续讨论小说美学的话题。这也是《新小说》的一个栏目标示首创,推动了晚清文学批评的热潮,吸引了众多作者与作品的出现。
从《新小说》栏目分类标示的出现、发展与变化,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份杂志理念的变化轨迹,是我们了解晚清小说分类以及《新小说》基本特征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