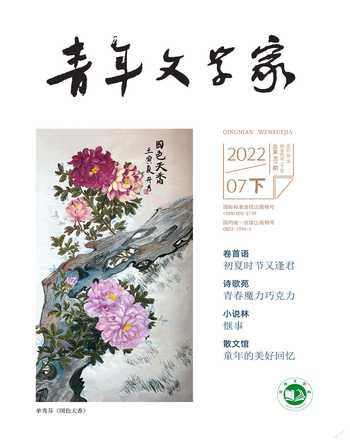看似寻常最奇崛
杨世琪

六年时间弹指一挥,却足够梁遇春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中国的伊利亚”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里,以纯真的性灵观照万物,在反叛性书写中打造了凝视自我与社会的全新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试图从时空观念、矛盾处境与姿态缺陷三个方面对梁遇春的美学思想进行另类解读,并对学界常用的存在主义研究视角进行反思。在梁遇春笔下,崇高被消解与重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形成一种平凡化自由人格的生活艺术,凝练为独特的人生美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读梁遇春的文字,品味其背后的美学思想,不再警惕毫无保留的自尊与怜悯,也最终原谅生命的荒诞与刻奇。
一、空间与时间
(一)空间:广阔社会图景与高远精神疆域
梁遇春在散文创作中不断攀缘常人不能及的边缘,反其人之“文”而行之,突破社会主流观念,阐发“惊世骇俗”之语。他把人生哲思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场域紧密联结,营造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空间状态”,开辟远离主流社会的另类世界,从而达到对平庸现状的颠倒倾覆。这种开放与作者本身打破原有桎梏,拥抱全新自由生活方式的思想构建一脉相承。梁遇春在《救火夫》一文中写道:“救火夫并不是一眼瞧着受难的人类,一眼顾到自己身前身后的那般伟人。”他们是以往文学作品中较少涉及与讴歌的芸芸众生,是不起眼的小人物,无名氏在近代文学浩如烟海的文卷中也只得寥寥几笔,但是“泰然地干着冒火打救的伟业”,与众多伟人相较毫不逊色。在对救火夫的描写中,梁遇春展露出一种强烈的“反英雄”倾向,他指出生命的壮阔在于向残酷的自然反抗,而纵情燃烧莫逆于心的心灵体悟不只被沉醉功名利禄的社会中流砥柱独占。流浪的闲人,高卧的眠者,失掉了悲哀的悲哀,梁遇春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文艺作品的写作对象,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聚焦于笔端。
梁遇春辛勤耕耘散文园地,扩展内容空间,与此同时,他也勾画着高远的精神空间图景,他卓越的反叛意识具有超脱时代的特性。而人类寻求自由之进程,借助主体强烈之本质力量,便构成书写崇高的奋斗路径。梁遇春反对规程化的循规蹈矩,超越世俗的野心隐藏在彬彬有礼的文字之下,究其内核便是独立意识与自由意志的自发反叛与自我发轫。他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阐明新兴思想绑架众人头脑的隐忧,呼吁青年应具有与众不同的灼见;在《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一文,呐喊出众人口中封缄的话语,批判照本宣科漠视知识的社会现象;《吻火》里捕捉肆意放达的快意人生,提倡沉浸式体验生活的喜怒哀乐。这一切均传达出精神解放与人格自由的呼声。
(二)时间:超越线性观念与成功序列突围
梁遇春独特的时间观念也在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梁遇春对时间的思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的流动是否单向且线性的,二是时间流逝对人类生命的影响,即人类是否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采取固定化的举措。《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这篇散文便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蕴含了他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思考。过去在经历的装点下实现了自我的内隐化,未来是无义的,一切取决于内在的感官,在直觉思维中寻找潜藏的价值。时间必然流逝又随着汇入命运的洪流而停滞,当下的存在状态取决于意义之流的回溯。由此,梁遇春对时间的思考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线性观念,而突出“人的存在”给时间附加额外属性。
梁遇春在《破晓》一文中对时间的思考集中在第二个方面,揭示了成功带来的二律背反,否定了以时间限制人为生命的观点。文中描写了人们在追逐理想与趣味的过程中失掉了本真发现志趣的禀赋,在奴役成功时也为成功所俘获,随着时间的推移按部就班地进行固定化的行动,如流水线上的齿轮,兜兜转转丢掉了本能心动。这其中充满了作者对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为探求成功封闭感知,乃至于丧失人性的惋惜。他积极探索成功的各种可能路径,又与当下所流行的“社会逆时钟”同声相应,具有田园牧歌式的慢时间光辉。
(三)崇高来源:怀疑精神与恐慌动因
与《新青年》同仁、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不同,梁遇春悲伤基调下的反叛精神是與鲁迅一脉相承的。在开创“开放空间”和“意义时间”的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出于不安全感的怀疑精神。面对自然社会深感个人渺小的心态深深激发着创作者心中的忧患意识,恐慌的心理动因也成为崇高感的一大重要来源。崇尚自由,在恶的意志指导下僭越规章道德与一切束缚的思想便成为梁遇春散文中一颗亟需引爆的炸弹,他与一根倒刺较量着过完一生,在维持创造性、渴望和平与自由的同时带来未竟的破坏。
二、台前与幕后
(一)台前:失重处境与对峙结构
追求反叛的自由意志与恐惧滋生的忧患观念左右着梁遇春的创作美学,散文呈现出闲情文化与载道文化相冲突的“失重处境”,肯定自我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倡导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读梁遇春的散文,常见的感受便是矛盾与失衡。梁遇春在散文选材时偏向二元对立式的主题,如“泪与笑”“天真与经验”“‘失掉了悲哀的悲哀”“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显性文本中的主体矛盾强化了散文的叙述张力,呼应崇高所包含的冲突对立永恒命题,富有思辨色彩与启示意味。
更有一些文章,在论说之外另有一番天地,矛盾冲突“对峙结构”隐在文本之外。《人死观》与“人生观”遥相呼应,《第二度的青春》与真正的青春年华唱和。表面上看这类文章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题,实际上却在内容上完成了对常见话语体系的冲突与对抗。不仅在文章篇幅内,而且在句的单位中便能体验出作者的矛盾观念。在《这么一回事》中梁遇春从心底发出喟叹:“既然有个终南捷径可以逃出人生,又何妨在人生里鬼混呢!但是……但是……”两个转折的意犹未尽,浑然天成如小林一茶的俳句“我知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言未尽而意无穷,数不清的思绪拉扯在这两个“但是”之中了。
如此,文本之外的矛盾还具有了内涵层面的冲突。在《“春朝”一刻值千金》一文中,忙与闲、快与慢、喧嚣与停滞的矛盾贯穿始终。梁遇春渴望享受生活,细心感受闲趣,将“迟起”视为一门艺术;又偏爱起床后的紧张忙碌与未完的事业,渴望在人生的途中收获丰富的经历。现代性条件下的异化使得梁遇春把创作带入精神危机的领域,挑战自我的同时指向节制与约束,赞美精神解放与人格自由的同时又呼唤理想人格的实现,他用一支笔在人生的两端踽踽独行。
(二)幕后:追求熱力与掩藏疾苦
因这矛盾的存在,梁遇春的文字沦为“带着镣铐的心的枷锁”。他迷恋过去又妄想未来,慕恋着青春的光辉,在时间维度上举棋不定,在空间维度里未能致远。诚然,这与当时新旧思潮下的不确定性心态密切相关。
梁遇春在《春醪集》的序言中写道:“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谈笑风生间,似有“樯橹灰飞烟灭”的少年意气。但作者是否真正不畏惧“张弓拔刀”,仍有待商榷。正如转折时的两个“但是”,纠缠的情感被悉数略去。《救火夫》一文强烈赞颂了救火夫们在席卷一切的大火里奔走,不顾死生,飞蛾扑火,救死扶伤,在人生舞台上燃尽生命的油脂,短暂的一切便是瞬间的永恒。但梁遇春对救火夫这一群体的观照也仅仅止步于此,他与救火夫所存在的真实处境是始终隔一层的。为了生计选择此等危险职业,伤残病痛折磨着的底层人民救火之后面临的现实疾苦,似乎就不再流淌于梁遇春的笔端了。生命的舞场不只有台前还有幕后,救火夫的生命也不止“高光时刻”的光与热,而这隐藏在帘子后疾苦的众生相却被作者有意或无意掩盖了。
(三)崇高背后:姿态缺陷下的悬浮格调
年轻的作者涉世未深,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相去较远,使得散文作品中暗含“悬浮格调”。首先,与现实主义相悖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姿态特有的通病。“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梁遇春在散文中一大重点便是书写闲趣,也将闲愁娓娓道来。潇洒恣意的笔调如高山流水,端坐于书斋中的青年担的便是清白天真之气,与其对应的,他对劳动人民的叙写也具有一定的理想化、天真化色彩。其次,与热烈任性体悟生命的态度不同,作者在创作上采用“隔岸观火”的看客角度叙写人生,以理性洞见品察人生况味。这种抽离感一方面与“对峙结构”一起强化了文本的张力与冲突,加深了文章的客观理性程度;另一方面,如无坚实的土壤,文章也容易落入空中楼阁的窠臼。
三、消解与超越
(一)消解:对抗冲突
悲观与乐观的复调在梁遇春的散文中交错并行,打造了生命存在的二重境遇。他记录难以调和的生之悲哀与死之寂静,用严肃态度与悲剧意识武装头脑。在《救火夫》中,他联想到了古希腊史诗所吟咏的人神之争,人与自然的斗争被划分为宇宙中最为悲壮雄伟的戏剧。他冷峻的思考呈现了世界的本初样貌,面对残酷的自然社会,人们与环境的对抗与冲突难以调和,为解决生存问题,二者进行了长期的博弈。生存的艰难增长了幻灭的苦痛,憎恶、死亡、贪婪、孤独,情感上的荒诞感受佐证着世界的不合理性。大多数人不是沉湎在过去痛苦的旋涡之中无法脱身,就是抓住悲哀的影子,妄想从裂隙中窥见往日幸福的余晖。对理想境界的追逐成为镜花水月,崇高在对抗与冲突的话语体系下渐趋消磨。
(二)超越:内在统一
无独有偶,除《救火夫》外,古希腊神话故事和英雄形象在梁遇春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从《观火》等散文里可见一斑。他援引这些敢于挑战自然的英雄人物,强调死亡的不可避免,倡导直面人生困窘,反对悲观绝望。有学者据此将其思想划归为存在主义范畴,强调其思想中的反抗冲突意识。但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不合理之处。
梁遇春的思想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对生命本身的原生罪孽感,对虚度年华抱有歉疚和悔恨,但比起人与未知冲突的不可回避,他更倾向于荒诞与反抗的内在同一性,于否定之否定中寻找光明。其本质更贴近于以崇高为内核的美学思想。在梁遇春的笔下存在高扬热爱与彷徨踟蹰的矛盾,生命等值与程度比较的矛盾,人生无望与生命无价的矛盾,在广袤的空间与复杂的时间里,一以贯之的始终是终极价值追求的自我认定,人的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才是梁遇春散文中的灵魂与核心。
(三)崇高重构
梁遇春在散文中采取内隐化的崇高叙事,在私人场域中予以观照反思,最终达到超越崇高主体性的重构。与常见类型作品的话语体系不同,梁遇春作品较少涉及自发性的先行与殉道,而是指向内在和谐与圆融。生命的意义与自我的感知紧密相连,当冲突与矛盾出现时,终极手段是在感知的领域里构建自我的意义模式,从而实现精神的绝对领先。在感受与理解中,梁遇春无疑选择了前者。正如其在《黑暗》中所言:“想要知道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个光明的心地。”梁遇春热爱的便是在黑暗中迸发出的信念与见识,在理想人格中建造真理的永无乡。
至此,崇高被消解与重构,奇崛扬厉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形成一种平凡化自由人格的生活艺术,凝练为梁遇春的人生美学。针对生存问题的讨论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博弈。梁遇春指明了两条路径,一个通往人的存在以及自我尊严的获得,另一则是对全体人类的同情与爱。救火夫们因感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毅然投入生命的浪潮,撒播生命的热与力,也是梁遇春心中理想人生的写照。《世说新语》有云:“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利用人类最原始生命强力实现精神突围的同时,自我层面以不断超越建立自尊之情的屏障,社会境域用慈悲同情抵达崇高境界,而这一切都指向生命向往与人生关怀。崇高在中庸拓达的水面下,被情感所孵化,最终进化为个体化、私人化的独特表达。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集体孤独”愈发强烈的时代条件下,梁遇春的散文无疑能带来更多的启迪。他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开放维度构建全新的生活范式,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恐惧时生发的超越精神,在永恒矛盾命题前迸溅的自由意志与思想火花,在对崇高的反叛性书写中的平凡化重构,无一不是在压倒性绝望下以本真热爱为武器的宣战。梁遇春在捍卫人性尊严的同时,致力构建崇高精神图景,其思想在理性之光的烛照下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