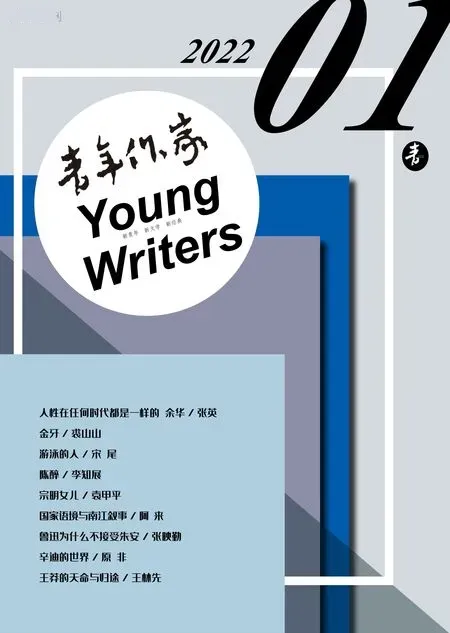番茄里的是是非非
宇 秀
“妈咪,我想吃一碗汤面面!” 囡囡喊着。
她从咿呀学语起,中文“面条”两字,就总是丢了后头的“条”字。 有趣的是,人类语言里不管哪个语种,称呼爸爸妈妈,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是用的叠音,除此之外,英文里就很少有指称事物的名词用叠音的了。比如,tomato,咿呀学语的幼儿也不会说成“to-to”,而中文里虽然番茄或者西红柿也没有叠音的叫法,可妈妈跟小孩子形容起来就会以“酸酸甜甜”这样的叠音。囡囡幼儿时,我每每鼓励她吃番茄说到“酸酸甜甜”,其实心里就比较虚,实在是现在的番茄,酸甜度都很淡了,难怪幼儿时的囡囡拒绝起来就喊:No,It’s not sweet at all (不,一点都不甜)!然而现在叫着要吃汤面面的囡囡,对番茄的态度已经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了。
此刻,炉子上正炖着一锅鸡汤,是专门从唐人街买来的新鲜走地鸡,两只爪子黄黄的,从锅盖里钻出来的蒸汽都是流油的鸡味。我最喜欢她主动要求吃汤面,想象一碗鸡汤到肚子里,小脸就红润了。
“别忘了tomato,Please!” 她中英文混搭着提醒妈妈别忘记加番茄。
这个出生在加拿大的小鬼子,从小不喜欢汤汤水水的中餐,更是莫名其妙地拒绝番茄,就像《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里面的小萝拉,直到某日吃了一碗妈妈煮的番茄鸡汤面,突然变了,连排骨汤、牛腩汤,都要我往里面加番茄。只是暗暗遗憾女儿吃不到我小时候的番茄,那蓄满了夏日骄阳和夜间露水、从肥沃泥土里生出的浓郁酸甜,绝非今日高科技可抵达的纯正,那滋味常常在记忆里折磨我的舌尖,而那些伴随着酸甜滋味的往事,更是夜半独处时的怀旧影片。
四五岁的记忆里,苏州永福里那条弄堂深得像一口井,好婆家就在“井底”。我喜欢坐在门口,看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们,就像看吊桶在井里上上下下。最喜夏天早上,好婆和邻居阿婆说笑着从小菜场回来,她们个个篮子里盛着青翠欲滴的时蔬,如鸡毛菜、毛豆子、香莴笋啦,有的绿叶菜上躺着一两条活鲫鱼,尾巴不时弹跳一下,有的菜面上铺一块红白相间的五花肉,青砖灰瓦的弄堂立刻就像从瞌睡里醒过来似的有了精气神儿。阿婆们坐在各自门口,一边捡菜一边嘹亮地聊天,一天的烟火气就从菜篮子开始了。
好婆篮子里总是搭两三个番茄,好像故意配色似的。她称那种橘红色的为“洋红番茄”,甜味多,可以当水果吃。看我黏在她身边,就先切半个给我生吃,那剩下的半个,好婆就用来做番茄蛋花汤。她先把切成小块的番茄在热油里煸炒一下,再加水、盐,和一小撮榨菜丝,出锅前撒入调均的蛋糊、葱花和味之素,端到台面上再加几滴芝麻香油。
虽然番茄炒蛋几乎是每个中国人家都会做的一道家常菜,但我并不记得好婆做过,也似乎不曾在邻家餐桌上见过。好婆说鸡蛋要凭票买,炒鸡蛋一次就要用掉四五个蛋。再说苏州人家饭桌上不缺鱼肉荤腥,也轮不到番茄炒鸡蛋当主角。番茄作为配角却在各种汤里很出色,除了番茄蛋花汤,还有冬瓜番茄汤,清香中略有酸味,是一道爽口消暑的素汤。不过,好婆是无肉不欢的主,她更多时候喜欢在洋山芋排骨汤里加几块番茄,这汤立刻就少了油腻,平添鲜味。每次看好婆用大汤勺舀一点点汤尝尝咸淡,那汤勺一碰到嘴唇她就立刻拎起两根眉毛啧啧地叫道:“鲜是鲜得来!眉毛脱忒啧!”
至于番茄炒蛋,在父母下乡的“小三线”伏牛山区东麓是一道待客的菜,自家吃的时候叫作“改善生活”。一般人家舍不得平白无故地吃番茄炒蛋,而是将炒好的鸡蛋番茄呼啦啦兑一锅水,勾上厚厚的芡粉打成捞面的卤,配上在臼里新捣的蒜泥,本来一碗鸡蛋炒番茄就被扩大为一锅鸡蛋番茄卤,就够一家几口吃一顿捞面条了,而无需其他菜辅佐,省食材、省工夫。所以当地的主妇们总是比母亲有更多闲暇串门聊八卦,或坐在树底下乘风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政府一声号令,调集全国各地技术骨干投身“三线”建设,一个当地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运煤的小火车就吓晕的山沟沟,旋风似的会聚了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逐鹿中原”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地名——舞阳工区。父母就在工区的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当医生,而我所在的子弟学校,每个班级里的孩子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和炼钢相关的地方,比如武汉、马鞍山、包头、富拉尔基等,来自东北的孩子特别多,我所在的班上,东北口音迅速压倒了其他地方口音,即使当地的河南孩子也成了非主流的“少数族裔”。不过毛头是个例外。
移民,这个如今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其实当年我就随父母一起亲身实践体验了。我们住的家属楼建在一个高坡上,朝南下去一条公路,再穿过一片小树林,便是著名的石漫滩水库。1975 年夏,本地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石漫滩水库正是与驻马店板桥水库先后溃坝的那座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人工水库,据说是苏联专家援建的……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不在此细说,还是让我拐回来继续说说有关番茄的故事。
我家住的楼朝北背靠山峦,从楼房到山脚之间有一片空地。突然某日,各家各户自发圈地开垦,围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菜园。那开荒种地的情景,在我后来听到郭兰英唱《南泥湾》的时候,就总是拿来想象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当初舞钢职工医院的开荒种菜,拿手术刀、挂听诊器的医护人员,总是抵不过刚刚在老家丢下铁锹、锄头的后勤和政工干部及其家属的,他们圈地速度之快,令下了手术台和三班倒的医生们猝不及防。当母亲觉悟到我们可以种一些当地没有的南方老家的蔬菜品种时,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插足之地。等到母亲收到老家用信封寄来的鸡毛菜、草头、丝瓜等种子,我们就只好在朝南的自家窗前开一块袖珍菜地,母亲称之为“豆腐干”。
那时各家菜园必种番茄,母亲也讨来一把番茄秧栽到“豆腐干”里。我们住的家属楼里每两户人家合用一个公共厕所,自从开了小菜园,早上的尿盆就不直接倒厕所去了,母亲命我倒到自家菜园子里。我顿时明白了什么叫“肥水不外流”,比老师写一大黑板词语解释明了和生动太多了。
母亲在菜园里挖了个坑,把树叶和家里馊了的饭菜丢进去,我就把尿盆里的“肥水”倒进去混合。当地人叫“沤粪”,沤过的粪才是有效的肥料。不过我家的豆腐干菜地怎么施肥都没法儿跟毛头家的比。
毛头跟我小学同班,是他家老幺。家里哥哥姐姐加上父母都快一个班了,菜园子的活儿哪轮到他?闲得无聊,他就常常跑到别人家的菜地里祸搅,不是掐了人家的花儿就是踩了人家的苗。可他家的菜园子是最大的,种植品种也最多,就开在家属楼通往山脚的路边,与土坯垒的茅厕离得最近,跨过去几步就贴到土墙上的 “男”“女”了。难怪泥土都黑得流油似的,一眼望去,绿油油的枝叶比周围的深一层。
毛头爸爸是医院食堂的厨子,我对他的印象已经没有五官了,但他光头光膀在菜地里劳作的样子依然清晰。那是夏日傍晚,当太阳像一条巨大无比的金色长裙从天上褪到半山和地面的时候,毛头爸就光着膀子在他家菜地里施肥。一根木头长柄粪勺从大桶里舀一勺,身子一转就甩出180 度半圆,那个半径恰好就以他站立为圆心到篱笆墙,粪勺里的肥料绝不会甩到篱笆外的小路上。毛头爸说,让他甩到路上去他还心疼糟蹋了他家的肥料呢。
虽说不能跟毛头家大田似的菜园子相比,但我和母亲都很敝帚自珍,小心呵护料理着我们的“豆腐干”。我的心里更是在上学以外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种期盼。看着那些秧苗分支开叉,枝叶繁茂,一到花开挂果,自己都站不住了,得在它们身边插一根木棍、竹竿等,用布条将它们一一捆绑于支撑物上,免得倒下。这个时候,各家都格外留神自己的小菜园,特别防备那些平时好惹是生非的捣蛋鬼们。我每天早上去菜园倒尿盆时,就要数一下那些脸色已开始红润的番茄,傍晚浇水时再复核一遍。
一天放学回来,正撞见隔壁邻居大辫儿和她那在医院工资科做会计的妈,俩人扭住毛头,嚷嚷着揪他去见他爹。大辫儿妈虽然个头矮矮的,但脸色黑黑,讲话跟拨算盘珠一样利落干脆。正是食堂要开饭的点儿,端着空碗的单身男女已经一溜儿等在食堂门口了。家属楼、单身宿舍楼和食堂之间自然形成一块类似广场的空间,是医院下班时间最热闹的地方,医院家属们有点什么事儿都会闹腾到这个“广场”来。那天,大辫儿母女俩押着毛头穿过“广场”,跟游街示众差不多。原来是毛头在大辫儿家菜地里偷摘了最红的两颗番茄,被母女俩逮个正着。其实,毛头并不稀罕番茄,那是他无聊的游戏,就是闲得手痒痒。但是,我心里慌了,赶紧奔自家的菜园察看。果不其然,早上清点过的半红半黄的那几颗大个儿番茄,全被摘了,枝头还留着新鲜的岔口。
第二天,医院门诊楼前的空地拉起了银幕,当晚要放的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太阳还火辣辣地晒在水泥地上,各家孩子都已经搬了小板凳去占位置,凳子不够的,先用粉笔画圈占地盘,圈好的地盘上放一颗石子。我也早早摆好了凳子,还帮楼下的邻居晓霞也圈了一片地,但我没像往常一样占中间的位置。其实这个电影也不是第一次看了,当电影里隐藏最深的特务“老狐狸”出现时,我和晓霞借口上厕所悄悄离开,我们一路奔到毛头家的菜地。晓霞放哨,我行动。小刀割在番茄树根上,手直抖,晓霞还不住催我快点快点,割到第三棵赶紧罢手。
第二天傍晚,暴晒了一天的那三棵番茄树,叶子打着卷儿,垂头丧气地全都蔫儿了。我假装上厕所路过观察一下“战果”,看着毛头爸站在他家菜园子皱着眉,喃喃自语:这咋回事咧?嘟囔了一会儿,他突然伸手揪起一棵,发现根没了!接连拔起另两棵,都一个样!毛头爸一屁股坐在菜地里,耷拉着光头。我赶紧躲到厕所里,按住自己怦怦跳的小心脏,毕竟是干坏事啊。不过这次破坏行动,终究没有“破案”。其实是毛头爸并没有去追究,他好像很笃定是谁干的,但肯定没怀疑我。
报复行动成功后,每天吃番茄的时候,就有点忐忑。
盛夏骄阳当头,各家各户的菜园子正硕果累累。丝瓜、西葫芦爬满篱笆,长的圆的果实吊在枝叶间;蒜苗正抽出蒜薹,都能闻到蒜香;最喜人的还是绿叶丛中的番茄,一团一团火似的。男孩子在自家菜地里摘一颗熟透的往胳膊上一捋,就当苹果吃起来。从自家菜地摘回来的番茄,一刀切开立刻冒出一层细密的水珠,像霜一样,吃起来沙沙的甜。父母都是江南人,每顿午餐没有米饭不算吃饭,三菜一汤的正餐,番茄炒蛋在夏日的餐桌上是出场率最高的花旦。毕竟是北方,不像苏州有那么多活鱼活虾。但自家菜地里长出的番茄,那酸甜的浓郁令舌尖都会打激灵。
母亲将番茄和鸡蛋分别单炒,打鸡蛋时加几滴料酒,炒出来的蛋又嫩又暄,喷香扑鼻。然后将炒好的番茄和蛋倒回锅里,添少许水、盐,翻炒一下,让汁色变浓即出锅。这道菜,母亲不放味精,说两样都是鲜物了。我和妹妹都喜欢用番茄鸡蛋里的汤汁拌饭。但母亲规矩大,我连着夹两筷子鸡蛋,就被她一筷子打回去,斥责我吃相难看。那一刻恨恨地下决心等自己上班挣钱了,每顿都吃一大碗番茄炒蛋!以后大了,慢慢理解母亲,若不是她定规矩,三个孩子的筷子和匙羹非在番茄炒鸡蛋的碗里打架不可。
有一天,母亲的病号送来一篮子番茄,加上自家种的,一下子吃不完了。母亲就把这些番茄洗净切块加盐和糖煮沸,装进消毒后控干的盐水瓶里,然后把装得满满的盐水瓶放在高压锅里煮沸,只听到瓶子在沸水里砰砰相碰的声音。取出后令其自然冷却存在阴凉处,便是一瓶瓶可存到冬天的番茄酱。母亲尽量不把番茄剁碎,只要能塞进瓶口即可。等倒出来食用时,块状的番茄依然保留了新鲜的美味。那时没有大棚蔬菜,没有反季蔬果,记得春节期间母亲在家宴客,端出番茄炒鸡蛋,客人们都惊叹母亲会变魔术。番茄的酸甜,在窗外飘雪的日子里,更加浓郁美味。那样真那样浓的酸甜,是泥土与阳光亲密合作的结果,有着土地的深情和夏日的烈性,绝不是当今通过高科技合成的味道。
“妈咪,我的汤面面呢?“ 囡囡叫道。
“ 哦,今天没有番茄,妈咪做不出你喜欢的汤面面了。要不,我用Ketchup 给你做Pasta,配一碗鸡汤?”
“ No,一定要有real tomato 才好吃!”小鬼子很固执。
唉,即使超市里买来的番茄,也不real 了!我不由暗叹。不过,我没有跟囡囡说,我不想破坏了孩子对于她所认为的 real tomato的好感,但忍不住还是遗憾囡囡完全不知道真正的番茄在母亲这代人的记忆里是什么味道。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在工艺美术品商店看到的工艺品水果,一串葡萄、几个苹果、香蕉、梨子什么的,为了看上去逼真,工匠们特意在它们身上做点瑕疵,比如一个结节、一个疤痕什么的,这样放在桌面上,可以乱真。然而想不到,现在人们吃到肚子里的水果在店里货架上摆着的样子都比那些工艺品完美得多了,个头大小都像是仪仗队员一样经过严格筛选过。想起曾在微信群里看到关于番茄的热议,其中印象特深的有这样一段:
纽约一位文友说,他回北京碰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以前是京郊农民。文友就跟司机聊天说起现在的番茄看上去很棒,却完全没有小时候能当水果吃的感觉了。那位司机回答:还想吃过去咱们自己的番茄?别做梦了,我家就是种番茄的。现在的种子都让日本公司垄断了,开始时种子很便宜甚至免费赠送,种出来又漂亮又有卖相,还不生虫害,很好赚钱,大家就都扔掉自己家传统的品种了。后来发现,这些外国新品种不仅不好吃,连番茄味儿都没有,种子价格还连年上涨,尤其坑人的是你用了他的种子,就必须按阶段买他的肥料和农药,只要你没按他的要求施放日本种子公司的肥料和农药,那些番茄就不结果,或者长不大,或者不红不成熟。说到这儿,司机咬牙切齿地骂说把他们坑苦了,当明白过来永远都得花钱给那些公司时,已经找不回来过去自己的老品种了。
出租司机说的西红柿,就是番茄了,中国北方地区多称番茄为西红柿,其实这个名字更符合番茄的来源,它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一带。我不敢肯定文友转述的司机的话是不是今天的番茄没有番茄味道的确切原因,但司机的说法还是让我不由心里一惊:原来我们不经意间就丢失了自己的种子!再一想,如今的世界,丢失种子的,又岂止是中国人?又想到,当年在自家“豆腐干”里种番茄和自制番茄酱的母亲,是不会像我这样在番茄的记忆里感伤的,不知该为她庆幸还是悲伤?如今躺在老人院里靠别人翻身、喂食的母亲,早已失语、失忆,那原味的酸酸甜甜,她都还给了往昔的岁月,却独独留下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反复咀嚼回味,并思索着那些有没有答案都无济于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