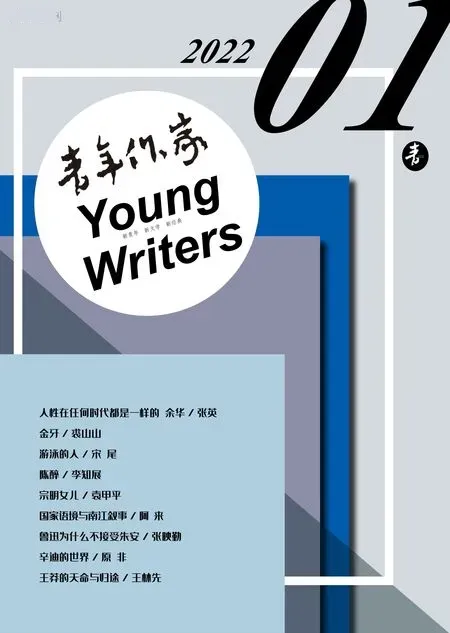飞蛾之死
杨 道
星期三是蓝蛾最喜欢的日子。她选择在这一天的凌晨三点从31 层高的楼顶跳下,是经过近半年的精心设计和计算的。落地的点她早已选好,楼下圆形花坛里的花一直开得甚艳,姹紫嫣红的,茉莉、七彩铁、千里香、月季……她喜欢花,她希望她的身体被花托着进入天堂。
这个城市的凌晨三点,雾气在半空悬着,蓝蛾的身体以飞蛾扑火的姿势匍匐在楼下花坛的中央,脸埋在一丛黄玫瑰中,仿佛她耗尽了半生活着的福气,终于捕到了那一点火光。
她的追思会,她的家人选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举行。从殡仪馆的入口就铺展着白色的菊花,来的人垂着头,合着手,手里握一支白菊。四月的早晨,有一些微凉的风,像飞蛾扇动翅膀的褶子。来的人随着褶子的皱依序进入馆内。蓝蛾像一个天使,静静地在椭圆形的花丛中躺着。这椭圆形花丛,类似于小说里美满的坟墓,献花的人从门口进来,绕着蓝蛾一圈,把手里的花插在离蓝蛾最理想的一个位置,仿佛就表达了最美满的悲哀。她的朋友做着哀痛的陈述:
“……蓝蛾是一个稀有的美好的女孩子……她在美丽的浔阳出生,她有着和陶渊明一样淡泊的心志,她九岁来到海南岛,22 岁毕业于楚地名校,50岁逝于抑郁症。……她爱读书、爱音乐、爱插花、爱吟诗、爱品茶、爱看画展、爱美、爱静、爱女儿、爱父母……无尽的爱,无尽的惋惜……她趋雅向美,冰雪聪明……她是沉睡在花梗上的天使。”
的确,她一直把自己置于一个冠着风雅名号的玻璃器皿中。她美丽、安静,穿着旗袍,轻声细语地说话,隔一些时间办一场读书沙龙,在种着绿植的露台煮茶,水汽噗噗地从陶制的茶壶中冒出来。围坐在露台品茶的,都是风雅之人,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蓝蛾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被富养的女孩子天然地有一股娇憨之气。蓝蛾还长着一张娃娃似的圆脸,年轻时可谓面若银盘,眉不画而翠,眼含一汪盈盈秋水,看人时充满一种深邃的智慧与哲思。
在一众朋友中她算不得最美,但她嘴角隐隐的笑让她获得了好人缘。她的丈夫耳丁是她大学的校友。大一时耳丁对她一见钟情,大学一毕业,两人就结了婚。婚后第三年,女儿出生。蓝蛾对于新出生的女儿并没有特别亲近,面对孩子时,她甚至生出一种烦躁和恐惧来。对于蓝蛾的情况,耳丁有些担忧,带她去医院,医生言之凿凿:这是产后抑郁症,要及早治。
蓝蛾对医生的话嗤之以鼻,她认为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她从单位请了假,产假和年假,加起来足足一年。
蓝蛾本来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自从生了孩子,得了这样一个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意识渐渐地膨胀起来。下腹一道剖腹产后留下的疤痕,像一条恣肆爬行的死去的蜈蚣,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背靠着背,拴在一起,沉沉地往下坠。
她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开始疼痛。她害怕医院里冰冷的仪器。她到处收罗可以通过按摩来减轻甚至治愈身体痛苦的民间偏方。她遇见了很多神医,在神医供职的各类国医馆办了卡,卡里的金额十分充足,把卡撑得满满的,仿佛这样就能把她身体里的病毒驱除出去。
她找每一个认识的人说话,一说就说上两个小时,话题都宽泛,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盘古到如今的当红女作家贾贾。后来认识的人见了她就避。避之不及,就假装不认识,与她擦肩而过时目不斜视,仿佛要前往的是一条通向罗马的金光大道。
蓝蛾并不是没有眼色之人。在认识的人都昂着头从她面前走过之后,她发奋地写作,写诗歌、写散文,有时候,觉得精力还足够充沛,就写小说。以她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极有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她想通过小说来创造自己的存在。她给自己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清泉”。
2015 年6 月,她以清泉的名字从电子邮箱开始进入我的生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学副刊编辑,我告诉她,我们不刊载小说,她的下一封邮件就换成了七篇散文。她的散文里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断地积累着日常琐事,记录下她头脑中的一切想法。她的每一篇散文都很长,内容包罗万象,仿佛她的世界里有着广阔的森林。她的行文散漫,如同在跟隔壁的邻居聊天。温着炭火,火苗一簇一簇地跳跃,林间小路上是斑驳的树影,空地上人影交错,忽隐忽现。她逮着文章里的每个人说话,话题也散漫,无法汇集成一个整体。但小说里的人不会避了她,她于是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她的存在之中。
为了同更多的人说话,她加入了教会和各种协会。她的一个教会姐妹告诉她,她的丈夫耳丁出轨了,出轨的对象是他的合作者叶银。他们在蓝蛾生下孩子没多久的时候就认识了。耳丁在初见时就爱上了叶银,中间因为叶银劈腿了另一个男人,把耳丁甩了。但耳丁一直对叶银痴情守望。在叶银甩了另一个男人的时候,耳丁迅速补上。此时的叶银离了婚,有一个乖巧的女儿。离了婚的叶银显然更加迷人,即使耳丁在电视台里见过无数美女,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她牵肠挂肚。
知道耳丁出轨的那个早晨,蓝蛾正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剪枝、插花。这是她难得不想说话的时光。她嫁给耳丁有十五年了。耳丁性情温和,喜欢热闹,经常无缘无故地放声歌唱。但他们之间缺乏理解,一个喜静,一个好动,这样的两个人配成一对,并不十分和谐——然而,她还是喜欢他并不十分温暖的拥抱。她在他抱着她的时候,可以多说十多分钟的话,他脸上也不显出十分的厌烦。——为了这十多分钟,她就老老实实地爱着他了。
茶几上摆着一瓶玫瑰,她手中的剪刀在她愣神的时候无知觉地剪去了几片卷曲的花瓣,发出干枯嘶哑的响声。她急切地想说话。她把身上的蕾丝花边睡衣拢紧,往黑暗的卧室走去。她伸出胳膊,摸到床头的位置,在床边躺了下来。她的已经出轨的丈夫就躺在一边。她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看着头顶上洁白的墙,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疼痛。
月光透过藏绿色的百叶窗,一道一道横切屋里的黑暗。他背朝她躺着,她看见他一脑门的青光,在月光中有些分外的白。她想把他摇醒,她储着一肚子的愤怒和恐惧需要发泄。她的手伸出去,在对着他鼻尖的空中晃了晃,又缓缓地放下。她生来就软弱,从身体到个性。她给每一个遇见的人以温柔的微笑,说话语调也是软的。大家说起她来,就都异口同声地感慨:咳,这真是一个好女人。
她被“好女人”的圈箍着。在发现丈夫出轨之后,她没有像普通女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把自己蜷缩进一个角落里。她在黑夜中听着男人震耳欲聋的呼噜声,感觉心里有什么在坍塌。她想象自己是古代的浣衣女,在最繁忙最满足的时候放下手中的衣服。丈夫一周换下来的衣服、床单和睡衣,在她的手中粉身碎骨。她想用语言去声明这一点,但除了她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休息,不受任何打扰。头顶的三盏莲花形灯也悄无声息,仿佛所有的一切都身处旷野之中,目之所及,一望无垠,萧瑟的冬没有繁殖绿的能力。一切都是静止的。
她的意识越来越清醒。她发现了莲花灯上匍匐着的那只飞蛾。飞蛾其实在做展翅欲飞状。像野鸟掠过高耸的群山,继续充满野性力量地飞行。
南边的窗户被风吹开了,一些风带着潮气进入她的身体。她感觉胸腔里有一些火开始滋生,渐渐地熊熊燃烧起来。那火苗仿佛落满灰尘的光,虚弱无力却又倔强地想要逃脱耀眼的阳光带来的尴尬压力。
她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把耳丁叫醒。他们是那天民政局开门后的第一对顾客。民政局的人都沉默,他们见惯了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丑态,已经没有欲望去探究结婚证上的这对男友曾经经历过些什么。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离婚证就办好了,蓝蛾和耳丁各持一本。没有什么财产分割,为了不让女儿察觉,两人决定离婚不离家,依旧在一个院子里居住,生活照常。只是女儿不在家时,就可各自找寻幸福,谁也管不着谁。
从民政局出来,蓝蛾提议走路回家。回去的路程很长,一路上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耳丁后来拐了道,把蓝蛾带到一家名为“意外”的小酒馆。酒馆里外的装饰都有一种文艺腔调,是蓝蛾喜欢的。
那晚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蓝蛾从耳丁的眼睛里看到愧疚,做了十五年的夫妻,对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通过缓慢的符号传达给他有关的信息。
酒醒后的耳丁搬离了他们共同的卧室。蓝蛾静静地坐在床上,守着几本旧影集。影集的一页掉出来一张,是她大学时站在樱花树下朝耳丁羞涩地微笑的照片。后来他们结了婚。再后来他们开始吵架,记不清每一次吵架的具体内容,但这期间她对于生活渐渐地恐惧起来,脑子里成了一团乱麻。她感觉浑身都疼,各种幻觉有条有理地互联起来。她完全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她到处找名师按摩身体,她急切地想把胸腔里淤堵的这些气尽快地排出去。对于和人类之间的语言上的交流,她已经彻底感到绝望。她急需一个出口,一个能容下她所有秘密的树洞。她想到了匍匐在莲花灯上的飞蛾。飞蛾窄窄的双翼如同一片枯草,翼梢如流苏,点缀着同双翼一样的枯草色。她不知道这飞蛾是不是曾经来过的那只,它一直用同一个姿势在亲近莲花灯。它在灯影中来回穿行,让她不由得生出一丝爱怜。这个夜里,她发现生命的快乐在飞蛾身上体现得十分完满,宏大宽阔而又千姿百态。飞蛾的生命过于短暂,但它却尽情地享受着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快乐。
蓝蛾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她连着几天几夜和飞蛾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夜里的飞蛾充满热情,生机勃勃地从领地的一角飞到另一角,尔后,继续飞向第三个、第四个角落。她注视着它,喋喋不休。没有人会对她喊停,她说得神采飞扬,仿佛整个世界巨大的能量化作一根细丝,注入她柔弱而骄傲的身体中。每当它在灯影里扇动翅膀,她便设想着有一丝生命之光亮起,群山壮阔,天空浩瀚,炊烟辽远。
离婚一年后,她在一次读书会上遇见了新的爱情。她像一只瘦小羸弱的飞蛾,在黑暗中寻着那一丝光,寻着了,便以简单直接的形式从敞开的窗户扑过去,不管窗外是悬崖还是深渊。她的奋不顾身在我和其他人脑中那逼仄复杂的盘廊中冲击而过,令人担心和唏嘘。
她的新男友是个有妇之夫,这使得这份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对等。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见过这位神秘的新男友,他像是她出于必要的局限臆造出来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中。所有的故事情节由创作者本人来证实,其真实性完全属于作者的想象。但这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作者本人。她开始变得活跃,感觉这花花世界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华服、精装本大菜单上的珍肴、最文艺范儿的房间,里面空无所有,除了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她在大玻璃窗下铺设暖调的地毯,地毯上随兴散落几个五颜六色的软垫。——后来我在一个夜晚陪她回家时,发现这个文艺房间也许也是她臆造出来的。她的家里,是暗沉的中式家具,沙发扶手上的雕花都有着分外的讲究。家里的饰品和茶具堆得满满当当,两三本书翻开在某一页,偶有风来,在沙发上沙沙作响。
她的睡眠一直很差。不管多累,与意识分离的痛苦都会引起她无法言说的反感。她发现即使天天诅咒睡眠之神也并无任何改善,这是一个凶残的黑脸刽子手。对此,她毫无防卫之术。她与人类的交集本来不多,因而,每一个夜里同飞蛾的交谈,就成了她唯一能依赖的微弱光亮。她在彻底的黑暗中会感觉头晕,如同灵魂会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样。
她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新调来的上司与原来的上司矛盾不可调和,又不能直接开撕,两人都选择在夜深人静时找她吐槽。她谁也不能得罪,就打哈哈吧。后来打哈哈也不行了,无论如何也得说出个子丑寅卯。她于是闭着眼睛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她感觉自己正处在一场大病之中,每天白昼黑夜都在感受着痛苦。她的痛苦比跳天鹅舞的演员弯曲低垂的苍白胳膊更接近艺术真实。
她给自己放了一个多月的假。回到我们身边时,岁月的刻针把她的圆脸刻成了轮廓分明的瓜子脸。脸庞变小了,眼睛里有一种迷茫的亲近。她的话变得更多了,仿佛喷壶嘴,琐碎繁杂,絮聒叨叨。但她说话的语速很慢,语调听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仿佛她的嘴悬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慢慢地往下沉。
新的春天来时,她的新爱情夭折了。
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她自己。
她的病也越来越不耐烦。她整日整夜地在床上躺着。有几次她想撑着爬起来,也许撑着撑着就过去了。
耳丁带着她去了几次医院。医生们的诊断分毫不差:患的是抑郁症。夜里,耳丁搬回他们曾经同床共枕的卧室,在蓝蛾的床边支起一张军用旅行床。耳丁按照医生的要求,天天给蓝蛾按摩。每逢他的手轻轻地按到她胸肋上,微凉的手指的碰触,让蓝蛾忍不住战栗。她知道自己这病根在于这双手,她以为可以执一生的手,却去触碰了别的女人。
从蓝蛾的少女时代起,世人就能在她眼中看到“爱情似乎是永恒的可能”。爱耳丁几乎成了她人生的信仰。直到他们离婚,这爱情依然“存在”,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一直在寻求永恒。她像个误坠人间的天使,对于世间转瞬即逝的事物毫无概念,无数的苦难和烦恼困扰着她。她用欢乐和悲伤给她的爱情幻象织就了一个温暖的茧。镜花水月转瞬成空,她心头枯败的爱情,却在遇见缝隙里的一丝光就能明亮而持久地燃烧。
我去看她的时候是黄昏。她躺在客厅的绒布沙发上,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客厅里的灯晕黄着,和窗外的夕照一样,有一种沉沉老去的暮气。她的圆脸愈发地尖了,卷发蓬散着,看起来像一株枯败的海棠,凋是凋谢了,花的底子形状还在的,薄薄的一片,风一吹,却也就落了下去,总要打几个转的,依依复依依。
她一天一天地瘦了下去。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她的肉体就从我指底溜走了。病了半年,她成了骨痨。她吃不下任何东西,偶尔吃进去一点,就在胃里梗着,身体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就整张脸都得憋着,人都憋得变了形。
她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了耳丁面对她时的不耐烦。她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个拖累。
她的爱情已经彻底地死了。在她的肉身枯朽之前。
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在与莲花灯上的飞蛾进行对话。她所要的死是诗意的,可以让人长久铭记的死。可是对于病人,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他们可以陪着电视剧里的林黛玉流泪,但不会对身边的肺痨病人有一丝亲近的想法。人们总是更易于接受戏剧化的悲哀、虚假的悲哀。
可是有时候蓝蛾也有一些乐观。逢到好天气,小鸟在窗外啁啾,也能暂时冲淡死亡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影。把厚重的帘布拉开,枕头在太阳里晒过,也能留一些香气。窗外的天,到底与过去是不一样了。想起刚和耳丁结婚时,每天夜里,他抱着她,一起站在窗前看星星。有流星划过,耳丁就大声嚷嚷:快,快许愿……她其实比他更早发现那颗流星,早早地在心里许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但走着走着,这样美好的两个人,终究还是走散了。
有那么一阵子,以前的生活就像一幕幕戏剧在蓝蛾眼前浮现。到了夜里,这些场景被灯盏笼罩,更显出异样的剪影。蓝蛾心里的感受会疾速膨胀,如同被注入空气的气球。当这美丽的幻象膨胀到最饱满紧张的时候,一根针刺了下去,它轰然坍塌。
这个星期三其实很平静,太阳沉下去后,黑夜和往常一样迅速蔓延。蓝蛾把植着兰花和海棠的瓷盆从客厅搬到卧室,一一摆放在淡青色的窗台上。她清楚地知道,当她从楼顶下坠的时候,会经过这个窗台,她会带着它们惊诧的目光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她把卧室里的书都收到书柜里,给自己换上一袭真丝白底青绿绣花旗袍,披上她最喜欢的绣着大红玫瑰的流苏披肩,然后安安静静坐在窗台边的藤椅上,看莲花灯上新来的一只飞蛾。这只飞蛾弓背凸肚,粉雕玉琢,踽踽独行,仿佛知道这是一个特殊时刻,每一步都充满极致的慎重与庄严。
飞蛾绕着莲花灯飞了一圈又一圈,进行一场一演员一观众的落寞的独舞。片刻后,它显然是舞累了,停在了灯影里的窗格上。蓝蛾看着它,面带凄凉的笑。似乎为回应蓝蛾的殷切,飞蛾尝试着重新起舞,但因为过于疲累,它的身子十分僵硬笨拙。它在窗格间拍打着翅膀挣扎着想要飞起来,但每一次都失败了。大约在第九次尝试过后,它从窗格上滑了下来,扑腾着翅膀,仰面倒在了窗台上。仰躺着的飞蛾奄奄一息,但它的细腿还在努力地挣扎。然而此时,死神如期降临了。它的身体松懈下来,随即变得僵直。它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死亡。
蓝蛾安安静静地目睹了这只飞蛾短暂的一生。她走过去,摆正飞蛾的身体,让它安详高贵地躺在那里。而后,她把窗户打开,双脚并拢,双臂张开,纵身一跃……如同飞蛾独舞,片刻之后,夜空里空空如也,路过的车灯照在一楼院里树篱上的一朵红玫瑰上,越来越细弱,直至变成一片黑暗。